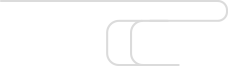
傷寒論註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傷寒論註卷之一 |
||
|
傷寒總論 |
||
|
病有發熱惡寒者,發於陽也,無熱惡寒者,發於陰也。 |
||
|
「無熱」,指初得病時,不是到底無熱發。「陰」指陽証之陰,非指直中於陰。「陰陽」指寒熱,勿鑿分營衛經絡。按本論云「太陽病,或未發熱,或已發熱」,「已發熱」,即是發熱惡寒,「未發熱」,即是無熱惡寒。斯時頭項強痛已見,第陽氣閉鬱,倘未宣發。其惡寒,體痛,嘔逆,脈緊,純是陰寒爲病,故稱「發於陰」,此太陽病發於陰也。又《陽明篇》云「病得之一日,不發熱而惡寒」,斯時寒邪凝斂,身熱惡熱,全然未露,但不頭項強痛,是知陽明之病發於陰也。推此則少陽往來寒熱,但惡寒而脈弦細者,亦病發於陰。而三陰之反發熱者,便是發於陽矣。 |
「無熱」,指的是得病之初沒有發熱,不是從頭到尾都不發熱。「陰」指的是陽證之陰,不是指邪氣直中三陰。「陰陽」指的是寒熱之證,千萬不要執著去區分營衛經絡。根據《傷寒論》所載「太陽病,或已發熱,或未發熱」,「已發熱」就是指發熱惡寒,「未發熱」,就是指不發熱但惡寒。此時已經出現了頭項強痛,只是陽氣閉鬱,尚未得到宣發。至於惡寒、體痛、嘔逆、脈緊等,單純只是陰寒所致之病,所以說「發於陰」,這是太陽病發於陰之病證。另外,在《陽明病篇》中說「病得之一日,不發熱而惡寒」,此時寒邪凝斂,身熱、惡熱完全沒有顯露出來,只是沒有頭項強痛,因此知道這是陽明病發於陰之病證。由此推論,少陽病之寒熱往來,只有惡寒而脈弦細者,亦是病發於陰。而三陰病中反而有發熱之證,就是病發於陽了。 |
|
|
發於陽者七日愈,發於陰者六日愈,以陽數七,陰數六故也。 |
||
|
寒熱者,水火之本體。水火者,陰陽之徵兆。七日合火之成數1,六日合水之成數,至此則陰陽自和,故愈。盖陰陽互爲其根,陽中無陰,謂之孤陽;陰中無陽,便是死陰。若是直中之陰,無一陽之生氣,安得合六成之數而愈耶?《內經》曰「其死多以六七日之間,其愈皆以十日以上」,使死期亦合陰陽之數,而愈期不合者,皆治者不如法耳。 |
寒熱所代表的是水火之本體,水火則是陰陽外在之反映。七日是火之成數,六日是水之成數,到了成數之日陰陽就會自和,所以病就痊愈了。陰陽互爲對方之根基,陽中無陰就被稱爲孤陽,陰中無陽便是沒有生機之陰。如果是寒邪直中三陰之陰,沒有一陽之生氣,怎麼能與水之成數相合而六日即病愈呢?《內經》說,「其死多以六七日之間,其愈皆以十日以上」,如果死期亦與陰陽之數相合,而病愈之期卻沒有與陰陽之數相合,這都是因爲醫者治不如法所致。 |
|
|
1 成數:根據《河圖》所示: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;地二生火,天七成之;天三生木,地八成之;地四生金,天九成之;天五生土,地十成之。五行各有生數與成數,即唐·孔穎達《周易正義》所說:「天一生水,地二生火,天三生木,地四生金,天五生土,此其生數也。地六成水,天七成火,地八成木,天九成金,地十成土。於是陰陽各有匹配,而物得成焉,故謂之成數也。」 |
||
|
問曰:凡病欲知何時得?何時愈?答曰:假令夜半得病者,明日日中愈。日中得病者,夜半愈。何以言之?日中得病,夜半愈者,以陽得陰則解。夜半得病,明日日中愈者,以陰得陽則解也。 |
||
|
上文論日期,合陰陽之數而愈。此論愈時於陰陽反盛時解,何也?陰盛極而陽生,陽盛極而陰生。陰陽之相生,正陰陽之相得,即陰陽之自和也。然此指病在一二日愈者言耳。如六七日愈者,則六經各以主時2解,是又陽主晝而陰主夜矣。 |
上文論及病愈之日期,是與陰陽之數相合而病愈。這裏論及了疾病會在陰陽氣反而盛極之時得解,爲什麼呢?陰氣盛極則陽氣生,陽氣盛極則陰氣生。陰陽氣之相生,正好是陰陽氣之相得,這就是陰陽自和。但是,這是指得病在一兩天之內而痊愈的病人。如果得病在六七天而痊愈者,則應該從六經病各自欲解所主之時辰來認識,這又反映了白晝屬陽而夜晚屬陰。 |
|
|
2 六經各以主時:即《傷寒論》所說的六經病欲解時,如「太陽病欲解時,從巳至未上」。 |
||
|
問曰:脈有陰陽,何謂也?答曰:凡脈浮大滑動數,此名陽也。脈沈弱濇弦微遲,此名陰也。 |
||
|
脈有十種,陰陽兩分,即具五法。浮沈是脈體,大弱是脈勢,滑濇是脈氣,動弦是脈形,遲數是脈息,總是病脈而非平脈也。脈有對看法、有正看法、有反看法、有平看法、有互看法、有徹底看法。如有浮即有沈,有大即有弱,有滑即有濇,有數即有遲。合之於病,則浮爲在表,沈爲在裏,大爲有餘,弱爲不足,滑爲血多,濇爲氣少,動爲博陽,弦爲博陰,數爲在府,遲爲在藏,此對看法也。如浮、大、滑、動、數,脈氣之有餘者,名陽,當知其中有陽勝陰病之機。沈、弱、濇、弦、遲,脈氣之不足者,名陰,當知其中有陰勝陽病之机,此正看法也。夫陰陽之在天地間也,有餘而往,不足隨之,不足而往,有餘從之。知從知隨,氣可與期。故其始,爲浮、爲大、爲滑、爲動、爲數。其繼也,反沈、反弱、反濇、反弦、反遲者,是陽消陰長之機,其病爲進。其始也,爲沈、爲弱、爲濇、爲弦、爲遲。其繼也,微浮、微大、微滑、微動、微數者,是陽進陰退之机,其病爲欲愈,此反看法也。浮爲陽,如更兼大、動、滑、數之陽脈,是爲重陽,必陽盛陰虛之病矣。沈爲陰,而更兼弱、濇、弦、遲之陰脈,是爲重陰,必陰盛陽虛之病矣,此爲平看法。如浮而弱、浮而濇、浮而弦、浮而遲者,此陽中有陰,其人陽虛,而陰氣早伏於陽脈中也,將有亡陽之變,當以扶陽爲急務矣。如沈而大、沈而滑、沈而動、沈而數者,此陰中有陽,其人陰虛,而陽邪下陷於陰脈中也,將有陰竭之患,當以存陰爲深慮矣,此爲互看法。如浮、大、滑、動、數之脈體雖不變,然始爲有力之強陽,終爲無力之微陽,知陽將絕矣。沈、弱、濇、弦、遲之脈,雖喜變而爲陽,如忽然暴見浮、大、滑、動、數之狀,是陰極似陽,知反照之不長,餘燼之易滅也,是謂徹底看法。更有真陰真陽之看法,所謂陽者,胃脘之陽也。脈有胃氣,是知不死。所謂陰者,真藏之脈也,脈見真藏者死。然邪氣之來也,緊而疾;穀氣之來也,徐而和,此又不得以遲數定陰陽矣。 |
脈有十種,分爲陰陽兩類,因此就具備了五分法。浮沉是脈體,大弱是脈勢,滑澀是脈氣,動弦是脈形,遲數是脈息,總之是屬於病脈而不是正常之脈。辨脈時有對看法、有正看法、有反看法、有平看法、有互看法、有徹底看法。比如脈象有浮就有沉,有大就有弱,有滑就有濇,有數就有遲。將其與疾病相應,就是浮爲病在表,沉爲病在裏,大爲邪氣有餘,弱爲正氣不足,滑爲血多,澀爲氣少,動爲邪氣搏於陽分,弦爲邪氣搏於陰分,數爲邪氣在腑,遲爲邪氣在臟,這就是「對看法」。比如浮、大、滑、動、數,屬於脈氣有餘,就爲陽,由此應該知道其中有陽勝陰病之病機。沉、弱、澀、弦、遲,屬於脈氣不足,就爲陰,由此應該知道其中有陰勝陽病之病機,這就是「正看法」。陰陽在天地之間,具有開始有餘,隨後就有不足;開始不足,隨後就會有餘之特點。知道陰陽氣這樣的特點,那麼對於陰陽氣之有餘或不足就可以有預期。所以,開始時脈象爲浮、爲大、爲滑、爲動、爲數,隨後分別爲反沉、反弱、反澀、反弦、反遲,這就是陽消陰長之變化,表明病情在進一步發展。開始時脈象分別爲沉、爲弱、爲濇、爲弦、爲遲,隨後分別爲微浮、微大、微滑、微動、微數,這就是陽進陰退之變化,表明疾病將要痊愈,這就是「反看法」。脈浮爲陽,如果又見到大、動、滑、數之陽脈,這就是重陽,一定屬於陽盛陰虛之病。脈沉爲陰,如果有見到弱、濇、弦、遲之陰脈,這就是重陰,一定屬於陰盛陽虛之病,這就是「平看法」。比如脈象浮而弱、浮而澀、浮而弦、浮而遲,這屬於陽中有陰,病人原本陽虛,但陰氣早就潛伏於陽脈之中,將會出現亡陽之變化,就應該把扶陽作爲當務之急。比如脈象沉而大、沉而滑、沉而動、沉而數,這屬於陰中有陽,病人原本陰虛,但陽邪已經下陷於陰脈之中,將會出現陰竭之憂患,就應該好好考慮如何保存陰氣,這就是「互看法」。比如浮、大、滑、動、數之脈體雖然不變,但是開始時是陽氣有餘之有力脈象,最後成爲陽氣微弱之無力脈象,就知道陽氣將絕。沉、弱、澀、弦、遲之脈象,雖然願意其變爲陽脈,但如果忽然出現浮、大、滑、動、數之脈象,這卻是陰極似陽,由此可知回光反照不會長久,餘灰是很容易熄滅的,這就是「徹底看法」。還有「真陰真陽之看法」,所謂「陽」是指胃脘之陽。脈象有胃氣就知道病人不會死。所謂「陰」,是指真臟脈,出現真臟脈,病人就會死。但是,邪氣侵入之時,往往脈來緊而疾數;當胃氣回復時,脈象就會變得緩慢而和緩,這時候又不可以簡單地用脈象之遲數來定其陰陽屬性。 |
|
|
寸口脈浮爲有表,沈爲在裏,數爲在府,遲爲在藏。 |
||
|
寸口,兼两手六部而言,不專指右寸也。上古以三部九候決死生,是徧求法。以人迎、寸口、趺陽辨吉凶,是扼要法。自《難經》獨取寸口,并人迎、趺陽不參矣。然氣口成寸,爲脈之大會,死生吉凶繫焉。則內外藏府之診,全賴浮、沈、遲、數爲大綱耳。浮沈是審起伏,遲數是察至數。浮沈之間,遲數寓焉。凡脈之不浮不沈而在中,不遲不數而五至者,謂之平脈,是有胃氣。可以神求,不可以象求也。若一見浮、沈、遲、數之象,斯爲病脈矣。浮象在表,應病亦爲在表。浮脈雖有裡証,主表其大綱也。沈象在裡,應病亦爲在裡。沈脈雖或有表証,主裡其大綱也。數爲陽,陽主熱,而數有浮、沈,浮數應表熱,沈數應裡熱。雖數脈亦有病在藏者,然六府爲陽,陽脈營其府,則主府其大綱也。遲爲陰,陰主寒,而遲有浮、沈,浮遲應表寒,沈遲應裡寒。雖遲脈多有病在府者,然五藏爲陰,而陰脈營其藏,則主藏其大綱也。脈狀種種,總該括於浮、沈、遲、數。然四者之中,又以獨浮、獨沈、獨遲、獨數爲準則。而獨見何部,即以何部深求其表裡藏府之所在,病無遁情矣。 |
寸口脈,是包括兩手寸關尺六部而言,不是專指右手之寸部脈。上古時期根據三部九候來定生死,這是遍求法。而根據人迎、寸口、趺陽之脈來辨別吉凶,這是扼要法。從《難經》提出診脈獨取寸口之後,人迎、趺陽之脈就不再參見了。然而氣口作爲寸脈,是脈氣之大會,關係到死生吉凶。如此,則內外臟腑之脈診,全都以寸口脈之浮、沉、遲、數爲大綱。浮沉是用來審察脈氣之起伏,遲數是用來審察脈氣之至數,浮沉之間亦都有遲數。凡是脈不浮不沉而在中,不遲不數而五至的話,就被稱爲平脈,反映脈有胃氣。這可以意會但不能完全依憑脈象。如果一看到浮、沉、遲、數之脈象,這就是病脈了。脈浮之象在表,主病亦在表。雖然浮脈亦可見裏證,但主表是其大綱。脈沉之象在裏,主病亦在裏。雖然沉脈有時亦可見表證,但主裏是其大綱。數爲陽,陽主熱,而數脈又有浮沉。浮數對應表熱,沈數對應裏熱。雖然數脈亦主有病在臟,然而六腑爲陽,陽脈主要佈散於六腑,那麼數脈主病在腑就是其大綱。遲爲陰,陰主寒,而遲脈又有浮沉。浮遲應表寒,沉遲應裏寒。雖然遲脈亦經常反映有病在腑,然而五臟爲陰,而陰脈主要佈散於五臟,那麼遲脈主病在臟就是其大綱。種種脈象,總的來說都應該包括浮、沉、遲、數。然而在這四者之中,又以脈象獨浮、獨沉、獨遲、獨數爲準則。而獨見在哪個脈位,就從那個脈位深求其表裏臟腑病變之所在,如此病情就無所遁形。 |
|
|
凡陰病見陽脈者生,陽病見陰脈者死。 |
||
|
起口用「凡」字,是開講法,不是承接法。此與上文陰陽脈文同而義則異也。陽脈指「胃氣」言,所謂「二十五陽」3者是也。五藏之陽和發見,故生。陰脈指「真藏」4,言胃脘之陽不至於手太陰。五藏之真陰發見,故死。要知上文沈、濇、弱、弦、遲是病脈,不是死脈,其見於陽病最多。若真藏脈5至,如肝脈中外急,心脈堅而搏,肺脈大而浮,腎脈之如彈石,脾脈之如喙距,反見有餘之象,豈可以陽脈名之?若以胃脈爲遲,真陰爲數,能不悞人耶? |
句子開始時用「凡」字,這是開始論述之方法,不是承前啟後之方法。這與上文所說的陰陽脈內容相同,但意義就不同了。陽脈指「胃氣」而言,即所謂「二十五陽」。五臟之陽表現爲調和,所以主生。陰脈指「真臟脈」而言,指胃脘之陽不能到達手太陰。五臟之真陰已經展露,所以主死。要知道上文所說的沉、澀、弱、弦、遲是主病之脈,而不是主死之脈,經常見於陽病之中。如果出現真臟脈,比如說肝脈之中外急,心脈之搏而堅,肺脈之大而浮,腎脈之如彈石,脾脈之如喙啄,反而見到了脈氣之有餘,怎麼可以稱之爲陽脈呢?如果把遲脈看成有胃氣之脈,把數脈看成真臟脈,怎麼會不誤人呢? |
|
|
3 二十五陽:《素問·陰陽別論》:「脉有陰陽,知陽者知陰,知陰者知陽。凡陽有五,五五二十五陽。所謂陰者,真藏也。」 |
||
|
4 真藏:見註3。 |
||
|
5 真藏脈:《素問·玉機真藏論》:「真肝脉至,中外急,如循刀刃責責然,如按琴瑟弦,色青白不澤,毛折乃死。真心脉至,堅而搏,如循薏苡子累累然,色赤黑不澤,毛折乃死。真肺脉至,大而虛,如以毛羽中人膚,色白赤不澤,毛折乃死。真腎脉至,搏而絕,如指彈石辟僻然,色黑黃不澤,毛折乃死。真脾脉至,弱而乍疏,色黃青不澤,毛折乃死。諸真藏脉見者,皆死不治也。」 |
||
| 寸脈下不至關6,爲陽絕。尺脈上不至關,爲陰絕。此皆不治,決死也。若計餘命生死之期,期以月節7剋之8也。 | ||
|
6 關:《脈經》:「寸後尺前名曰關,陽出陰入,以關爲界。……陽生於尺動於寸,陰生於寸動於尺。」 |
||
|
7 月節:本意指每月之節氣。《素問·六節藏象論》謂「五日謂之候,三候謂之氣,六氣謂之時,四時謂之歲」,故一月之中有二個節氣。由「月節」引申至四時之中有六氣之不同,各與五臟相應。風寒暑濕燥火,天之三陰三陽。木火土金水火,地之三陰三陽。故六氣應五行,五行應五臟。 |
||
|
8 剋之:指以五行相克之理推斷。 |
||
|
陰陽升降,以關爲界。陽生於尺而動於寸,陰生於寸而動於尺,陰陽互根之義也。寸脈居上而治陽,尺脈生下而治陰,上下分司之義也。寸脈不至關,則陽不生陰,是爲孤陽,陽亦將絕矣。尺不至關,則陰不生陽,是爲孤陰,陰亦將絕矣。要知不至關,非脈竟不至,是將絕之兆,而非竟絕也,正示人以可續之機。「此皆不治」,言皆因前此失治以至此,非言不可治也,正欲人急治之意,是先一著看法。夫上部有脈,下部無脈,尚有吐法。上部無脈,下部有脈,尚爲有根,即脈絕不至,尚有灸法。豈以不至關便爲死脈哉?看「餘命生死」句,則知治之而有餘命,不爲「月節」所剋者多耳,此又深一層看法。脈以應月,每月有節。節者,月之關也。失時不治,則寸脈不至関者,遇「月建」 之屬陰,必剋陽而死。尺脈不至關者,遇「月建」之陽支,則剋陰而死,此是決死期之法。若治之得宜,則陰得陽而解,陽得陰而解,陰陽自和而愈矣。 |
陰陽氣之升降,以關部爲界。陽氣生於尺脈而動於寸脈,陰氣生於寸脈而動於尺脈,這就是陰陽互根之意。寸脈居於上而關乎陽氣,尺脈生於下而關乎陰氣,說明寸尺分治上下陰陽之氣。寸脈之氣不能達於關脈,就是陽不生陰,是孤陽,反映了陽氣將絕。尺脈之氣不能達於關位,就是陰不生陽,是孤陰,反映了陰氣亦將消亡。要知道脈氣不能到達關脈,不是脈象竟然不出現,而是脈氣將絕之徵兆,而非已經斷絕,正是警示醫者有延續脈氣之機。「此皆不治」,是說都是因爲此前失治以至於此,不是說不可醫治,正是希望醫者迅速救治,這是先人一手之看法。如果上部有脈,下部無脈,還可以採用吐法。而上部無脈,下部有脈,說明脈氣還有根,即使脈氣絕而不來,還有灸法可用,怎麼能以爲脈氣不到達關部便是死脈呢?看「餘命死生」這一句,就知道加以治療是可以有餘命的,不爲「月節」所克的情況也有很多,這又是屬於深一層的看法。脈象與月相應,每月有節氣。節氣,是每個月之關口。失去治療時機,則寸脈之氣不能到達關脈者,遇到「月建」屬陰之時,陰氣一定會克陽而死。尺脈之氣不能到達關脈者,遇到「月建」屬陽之時,陽氣一定會克陰而死,這是判斷病者死期之方法。如果採用合適的方法進行治療,那麼就會陰病得陽而解,陽病得陰而解,陰陽氣自和而病愈。 |
|
|
問曰:脈欲知病愈未愈者,何以別之?曰:寸口、関上、尺中三處,大小、浮沈、遲數同等,雖有寒熱不解者,此脈陰陽爲和平,雖劇當愈。 |
||
|
陰陽和平,不是陰陽自和,不過是純陰純陽無駁雜之謂耳。究竟是病脈,是未愈時寒熱不解之脈。「雖劇當愈」,非言不治自愈,正使人知此爲陰陽偏勝之病脈。陽劇者當治陽,陰劇者當治陰。必調其陰陽,使其和平。失此不治,反加劇矣。] |
陰陽和平,並不是指陰陽自然調和,只不過是純陰純陽沒有夾雜而已。最終還是有病之脈,是疾病未愈時寒熱之邪未解之脈象。「雖劇當愈」,不是說不治療就會自愈,正是讓人知道這是陰陽偏勝之病脈。對於陽熱邪氣盛之病人應該治其陽熱之邪,對於陰寒邪氣盛之病人應該治其陰寒之邪。一定要調其陰陽,使陰陽達至和平。失於這樣的認識就不能治愈,反而會使病情加劇。 |
|
|
傷寒一日,太陽受之。脈若靜者,爲不傳。頗欲吐,若躁煩,脈數急者,爲傳也。 |
||
|
太陽主表,故寒邪傷人,即太陽先受。太陽脈浮,若見太陽之浮,不兼傷寒之緊,即所謂「靜」也。脈靜証亦靜,無嘔逆、煩躁可知。今又有發熱惡寒,頭項強痛,不須七日衰,一日自止者,正此「不傳」之謂也。若受寒之日,頗有吐意,嘔逆之機見矣。若見煩躁,陽氣重可知矣。脈急數,陰陽俱緊之互文。「傳」者,即《內經》「人傷於寒而傳爲熱」 之「傳」,乃太陽之氣生熱而傳於表,即「發於陽」者。「七日」之謂,非太陽與陽明、少陽經絡相傳之謂也。「欲」字「若」字,是審其將然。脈之數急,是診其已然。此因脈定証之法也。 |
太陽之氣主表,所以寒邪傷人,即是太陽先感受到邪氣。太陽病浮脈,如果見到太陽病之脈浮,而不同時出現太陽傷寒之緊脈,也就是所謂的「靜」。脈象未發生變化則證候亦不會發生變化,由此可知不會有嘔逆、煩躁之證候。如今又出現發熱惡寒、頭項強痛,不需要等到七日病情就會好轉,病證一天就能自然消散,正是這裏所說的「不傳」。如果受寒當日,病人就很想嘔吐,這是已經出現胃氣上逆之機。如果見到煩躁,由此可知陽氣鬱閉嚴重。脈象變得急數,與「脈陰陽俱緊」互文同意。「傳」,也就是《內經》「人傷於寒而傳爲熱」中所說的「傳」,是太陽之氣生熱而傳於表,這就是「發於陽」者。這裏所說的「七日」,不是太陽與陽明、少陽經絡相互傳變之意。「欲」字與「苦」字,是審視以後將會發生之事。脈象數急,是診斷現在已經發生之事。這就是根據脈象來確定證候之方法。 |
|
|
傷寒二三日,陽明、少陽證不見者,爲不傳也。 |
||
|
傷寒一日太陽,二日陽明,三日少陽者,是言見症之期,非傳經之日也。岐伯曰:「邪中於靣,則下陽明。中於項,則下太陽。中於頰,則下少陽。其中膺背兩脇,亦中其經。」 蓋太陽經部位最高,故一日發。陽明經位次之,故二日發。少陽經位又次之,故三日發。是「氣有高下,病有遠近,適其至所爲故也」 。夫三陽各受寒邪,不必自太陽始。諸家言二陽必自太陽傳來者,未審斯義耳。若傷寒二日,當陽明病,若不見陽明表証,是陽明之熱不傳於表也。三日少陽當病,不見少陽表証,是少陽之熱不傳於表也。 |
傷寒病第一日爲太陽病,第二日爲陽明病,第三日爲少陽病,這是說證候出現的日期,而不是傳經之日期。岐伯說:「邪氣入侵到面部,就會傳入到陽明經。入侵到項部,則會傳入到太陽經。入侵到面頰,就會傳入到少陽經。如果侵入到胸、背、兩脅,亦會傳入到相應的陽明經、太陽經和少陽經。」這是因爲太陽經部位最高,所以第一日就發病。陽明經的位置次之,所以兩日後發病。少陽經的位置又次之,所以三日後發病。這就是《內經》所說「氣有高下,病有遠近,適其至所爲故」。三陽各自都能受到寒邪入侵,不是必須從太陽經開始。很多注家都說陽明病、少陽病一定從太陽病傳來,是因爲沒能領會《內經》之意。如果患傷寒兩日,應該出現陽明病證,但如果沒有出現陽明病表證,是因爲陽明之熱沒有傳於表。第三日應該出現少陽病證,而沒有出現少陽病表證,是因爲少陽之熱沒有傳於表。 |
|
|
傷寒三日,三陽爲盡,三陰當受邪。其人反能食而不嘔,此爲三陰不受邪也。 |
||
|
受寒三日,不見三陽表症,是其人陽氣沖和,不與寒爭,寒邪亦不得入,故三陽盡,不受邪也。若陰虛而不能支,則三陰受邪氣。岐伯曰:「中於陰者,從臂胻始。」9故三陰各自受寒邪,不必陽經傳授。所謂太陰四日,少陰五日,厥陰六日者,亦以陰經之高下,爲見症之期,非六經部位以次相傳之日也。三陰受邪,病爲在裡。故邪入太陰,則腹滿而吐,食不下。邪入少陰,欲吐不吐。邪入厥陰,飢而不欲食,食即吐蚘。所以然者,邪自陰經入藏,藏氣實而不能容,則流於府。府者胃也,入胃則無所復傳。故三陰受病,已入於府者,可下也。若胃陽有餘,則能食不嘔,可預知三陰之不受邪矣。蓋三陽皆看陽明之轉旋。三陰之不受邪者,藉胃之蔽其外也。則胃不特爲六經出路,而寔10爲三陰外蔽矣。胃陽盛,則寒邪自解。胃陽虛,則寒邪深入陰經而爲患。胃陽亡,則水漿不入而死。要知三陰受邪,関係不在太陽而全在陽明。 |
受寒三日後,沒有見到三陽病表證,這是因爲病人陽氣沖和,不與寒邪相爭,寒邪亦不得侵入三陽,所以邪氣在三陽經結束而不再受邪。如果三陰經虛而不能對抗寒邪,那麼三陰經就會受到邪氣侵入。岐伯說:「邪氣中於三陰經,從手臂和足脛開始」。所以三陰經能各自遭受到寒邪侵襲,不必由三陽經傳入。所謂第四日是太陰發病,第五日是少陰發病,第六日是厥陰發病,亦是因爲三陰經位置高下不同,是出現病證之日期,而非六經不同部位按次序相傳之日期。三陰受邪之後,病位在裏。所以邪氣侵入太陰,就會出現腹滿而嘔吐,不能食。邪氣侵入少陰,則想吐又吐不出來。邪氣侵入厥陰,則饑而不欲食,如果進食就吐蛔蟲。之所以會這樣,是因爲邪氣從陰經進入五臟,五臟之氣充實而不能容忍邪氣,邪氣就會從臟流向腑。腑就是指胃而言,邪氣進入胃就不會再傳變下去。所以三陰經受邪而已經入於胃腑者,可以用攻下法治療。如果胃陽有餘,則病人能食而不嘔,由此可以預見三陰不會受到邪氣入侵。因爲三陽病都會根據陽明之氣的變化而變化。三陰之所以不會受到邪氣入侵,全靠胃氣能作爲其屏障而在外保護。如此,胃氣不只是六經祛邪外出之出路,實際上亦能作爲屏障而保護三陰不受邪氣侵襲。胃陽旺盛,則寒邪自然就會解除。胃陽虛弱,則寒邪就會深入三陰經而發病。胃陽亡絕,則病人水漿不入而死。要知道三陰經是否受邪,關鍵不在太陽而全在陽明。 |
|
|
9 語出《靈樞·邪氣藏府病形》:「中於陰者,常從臂胻始。夫臂與胻,其陰皮薄,其肉淖澤,故俱受於風,獨傷其陰。」 |
||
|
10 寔:同「實」,異體字。 |
||
|
傷寒六七日,無大熱,其人躁煩者,此爲陽去入陰故也。 |
||
|
上文論各經自受寒邪,此條是論陽邪自表入裡症也。凡傷寒發至六七日,熱退身涼爲愈。此無大熱,則微熱尚存。若內無煩躁,亦可云表解而不了了矣。傷寒一日即見煩躁,是陽氣外發之机。六七日乃陰陽自和之際,反見煩躁,是陽邪內陷之兆。「陰」者,指裡而言,非指三陰也。或入太陽之本而熱結旁光,或入陽明之本而胃中乾燥,或入少陽之本而脇下硬滿,或入太陰而暴煩下利,或入少陰而口燥舌乾,或入厥陰而心中疼熱,皆「入陰」之謂。 |
上文論及各經都能自受寒邪,而此條文字則是討論陽邪自表入裏之證候。凡傷寒病發病六七日以後,熱退身涼就表示病人痊愈。這裏說沒有高熱,則還有微熱。如果沒有煩躁,亦可以說是表證已解但尚未完全結束。傷寒一日就出現煩躁,反映了陽氣向外宣發。六七日原本是陰陽自和之時機,反而出現煩躁,這是陽邪內陷之徵兆。所謂「陰」,指的是裏,不是指三陰。陽邪內陷,或者入於太陽之腑則熱結膀胱,或者入於陽明之腑則胃中乾燥,或者入於少陽之腑則脅下硬滿,或者入於太陰則暴煩下利,或者入於少陰則口乾舌燥,或者入於厥陰則心中疼熱,這些都是所謂的「入陰」。 |
|
|
太陽病,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,以行其經盡故也。若欲再作經者,鍼足陽明,使經不傳則愈。 |
||
|
舊說傷寒日傳一經,六日至厥陰,七日再傳太陽,八日再傳陽明,謂之「再經」。自此說行,而仲景之堂無門可入矣。夫仲景未嘗有「日傳一經」之說,亦未有傳至三陰而尚頭痛者。曰「頭痛」者,是未離太陽可知。曰「行」,則與「傳」不同。曰「其經」,是指本經而非他經矣。「發於陽者七日愈」,是七日乃太陽一經行盡之期,不是六經傳變之日。岐伯曰「七日太陽病衰,頭痛少愈」,有明證也,故不曰傳足陽明。而曰「欲再作經」,是太陽過經不解,復病陽明而爲併病也。鍼足陽明之交,截其傳路,使邪氣不得入陽明之經,則太陽之餘邪亦散。非歸併陽明,使不犯少陽之謂也。本論「傳經」之說,惟見於此。蓋陽明經起於鼻額旁,納太陽之脈,故有傳經之義。目疼鼻乾,是其症也。若腳攣急,便非太陽傳經矣。陽明經出大指端內側,太陽經出小指端外側,絡不相連接。十二經脈,足傳手,手傳足;陽傳陰,陰傳陽。與傷寒之六經先陽後陰,先太後少之次第迥別。不知太陽傳六經,陽明傳少陽之說何據乎?細審仲景「轉屬」、「轉係」、「併病」、「合病」諸條,傳經之妄,不辨自明矣。 |
之前的說法是,傷寒病是每日傳一經,第六日就傳到厥陰經,第七日又再傳到太陽經,第八日再傳到陽明經,這被稱爲「再經」。自從有此說法之後,再想進入仲景之堂就無門可入了。仲景從來沒有「日傳一經」之說法,也沒有說邪氣傳到三陰還會有頭痛。說「頭痛」,可以知道邪氣尚未離開太陽經。說「行」,與「傳」是不同的。說「其經」,指的是太陽本經而不是其他經。「發於陽者七日愈」,是指七日是太陽經邪氣行盡之日期,不是六經傳變之日期。岐伯說過「七日太陽病衰,頭痛少愈」,這是有明確依據的,所以不說「傳足陽明」。而說「欲再作經」,是指太陽病過經後不解,又使陽明發病而成爲太陽陽明併病。針刺與足陽明交會之處,截斷邪氣傳變之路,使邪氣不得傳入陽明經,那麼太陽經之餘邪亦會消散。不是邪氣併於陽明之後,使其不再傳入少陽經之意。《傷寒論》「傳經」之說只見於此。因爲陽明經起於鼻額旁,與太陽經相合,所以才有傳經之理。目疼鼻乾,就是其證候。如果腳痙攣,就不屬於太陽傳經。陽明經出於大拇指指端內側,太陽經出小指指端外側,經絡不相互連接。十二經脈,足傳手,手傳足;陽經傳陰經,陰經傳陽經。與傷寒病之六經病先三陽病後三陰病,以及先太陽病後少陰病的順序差別很大。不知道太陽之邪傳六經,陽明之邪傳少陽的說法有何依據?仔細考察仲景有關「轉屬」、「轉系」、「併病」、「合病」各條條文,「傳經」說之謬誤,可以不辨自明了。 |
|
|
風家11,表解而不了了者,十二日愈。 |
||
|
11 常受風邪所犯之人。 |
||
|
「不了了」者,餘邪未除也。七日表解後復過一候12,而五藏元氣始充,故十二日精神慧爽而愈。此雖舉「風家」,傷寒槩之矣。如「太陽七日病衰,頭痛少愈」,曰「衰」曰「少」,皆「表解而不了了」之謂也。六經部位有高下,故發病有遲早之不同。如陽明二日發,八日衰;厥陰至六日發,十二日衰。則六經皆自七日解,而十二日愈。夫若誤治,又不在此例。 |
所謂「不了了」,是因爲餘邪尚未消除。在第七日表證解除後又過一候,五臟元氣才開始充盈,所以十二日後病人才精神慧爽而病愈。這裏雖然以「風家」爲例,但概括了所有傷寒病。比如說「七日太陽病衰,頭痛少愈」,用「衰」字,用「少」字,都是所謂的「解表而不了了」。六經部位有高下之分,所以發病會有遲早之不同。比如陽明病在第二日發病,到第八日開始緩解;厥陰病在第六日發病,到第十二日開始緩解。可見六經病都是到第七日開始緩解的,而到第十二日痊愈。如果被誤治的話,則不在此例中。 |
|
|
12 一候:依據《素問·熱論》,三陽三陰發病後,都以六日爲循環周期。這裏「一候」,就是指六日的循環周期。 |
||
|
仲景分別六經,各經俱有中風、傷寒脈症治法。叔和時《太陽篇》存者多而失者少,他經存者少而失者多。《陽明篇》尚有中風脈症二條,少陽經只症一條而不及脈,三陰俱有中風欲愈脈,俱無中風脈症。以《傷寒論》爲全書,不亦疏乎? |
仲景分別論述六經病,各經都有中風與傷寒之脈證與治法。王叔和在世時《太陽病篇》所保存的條文多而丟失的較少,其他經病所保存的條文少而丟失的較多。在《陽明病篇》中尚有兩條關於中風的脈證,少陽經只有一條有證候但沒有涉及脈象,三陰病都有中風欲愈之脈象,但都沒有中風之脈證。把《傷寒論》當成是一部完整的書,難道不覺得有疏忽嗎? |
|
|
右論13傷寒診病大畧。 |
上面所討論的是診察傷寒病之大概情況。 |
|
|
13 右論:古書排版爲豎排,右先左後。今改爲橫排,所以「右」爲上而「左」爲下。 |
|
原文 |
|
翻譯 |
|
傷寒論註卷之二 |
||
|
麻黃湯證上 |
||
|
太陽病,頭痛發熱,身疼腰痛,骨節疼痛,惡風,無汗而喘者,麻黃湯主之。 |
||
|
太陽主一身之表,風寒外束,陽氣不伸,故一身盡疼。太陽脈抵腰中,故腰痛。太陽主筋所生病,諸筋者,皆屬於節,故骨節疼痛。從風寒得,故惡風。風寒客于人則皮毛閉,故無汗。太陽為諸陽主氣,陽氣鬱于內,故喘。太陽為開,立麻黃湯以開之,諸症悉除矣。麻黃八症,頭痛、發熱、惡風,同桂枝症。無汗、身疼,同大青龍症。本症重在發熱、身疼、無汗而喘。 |
太陽主持全身之表氣,風寒邪氣從外入侵體表,陽氣因而鬱閉而不伸,所以全身疼痛。足太陽脈抵於腰中,所以腰痛。太陽主筋脈所生之病,而筋脈都與關節相連,所以骨節疼痛。由於病從風寒而得,所以病人惡風。風寒傷人則皮毛閉塞,所以無汗。太陽統領諸陽之氣,而陽氣鬱閉於內,所以氣喘。太陽之氣主開,所以確立麻黃湯以開太陽之氣,各種證候就會隨之消除。麻黃湯所治有八證:頭痛、發熱、惡風,與桂枝湯證一樣。無汗,身體疼痛,與大青龍湯證一樣。本方所治之證重在發熱、身體疼痛及無汗而喘。 |
|
|
脉浮者,病在表,可發汗,麻黃湯。脉浮而數者,可發汗,宜麻黃湯。 |
||
|
前條論症,此條論脉。言浮而不言遲弱者,是浮而有力也。然必審其熱在表,乃可用。若浮而大,有熱屬藏者,當攻之,不令發汗矣。若浮數而痛偏一處者,身雖疼,不可發汗。 |
前條討論的是證候,本條討論的是脈象。說脈浮卻不說脈遲弱,反映脈象浮而有力。然而一定要判斷其熱屬表證,才適用這一點。如果脈浮而大,屬於熱在臟腑,則應該攻下,不能用汗法。如果脈浮數而痛處偏向一處,身體即使疼痛,都不可以發汗。 |
|
|
脉浮而數,浮為風,數為虛。風為熱,虛為寒。風虛相搏,則酒淅惡寒也。 |
||
|
脉浮為在表者,何?以表有風邪故也。邪之所湊,其氣必虛。數本為熱,而從浮見,則數為虛矣。風為陽邪,陽浮則熱自發。數為陽虛,陽虛則畏寒。凡中風寒,必發熱惡寒者,風虛相搏而然也。 |
脈浮反映病在表,為什麼?這是因為有風邪在表。凡是邪氣所湊之處,該處之正氣一定虛弱。數脈原本反映熱,但是隨著浮脈而出現,那麼數脈就代表虛了。風原本為陽邪,陽氣外浮則自然發熱。而脈數反映陽虛,陽虛則畏寒。凡是受風寒邪氣所傷,之所以一定會發熱惡寒,這正是風邪傷於正虛之人的結果。 |
|
|
諸脉浮數,當發熱而洒淅惡寒。若有痛處,飲食如常者,畜積有膿也。 |
||
|
浮數之脉,而見發熱惡寒之症,不獨風寒相同,而癰瘍亦有然者,此浮為表而非風,數為實熱而非虛矣。發熱為陽浮,而惡寒非陽虛矣。若欲知其不是風寒,當以內外症辨之。外感則頭項痛、身痛、骨節痛、腰脊痛,非痛偏一處也。外感則嘔逆或乾嘔,不得飲食如常。如此審之,有畜積而成癰膿者,庶不致誤作風寒治,則舉瘡家一症例之。治傷寒者,見脉症之相同,皆當留意也。 |
脈浮數而見發熱惡寒之證,不僅中風傷寒是一樣的,而且癰瘍也會有這種情況,此時之浮脈反映病位在表而非風邪在表,脈數表示實熱而非虛弱。發熱是因為陽氣外浮,但惡寒就不代表陽虛了。如果想要知道病人所得的是不是風寒,應該根據內外證候進行分辨。外感則見頭頸痛、身痛、骨節痛、腰脊痛,而且疼痛並非偏向一處。外感則見嘔逆或乾嘔,不能正常飲食。這樣來判斷,有熱邪積聚所致之癰膿,可能就不會誤作風寒表證來治療,這是就瘡家為例說明不同疾病可能出現相似證候。治療傷寒病,凡是有相同之脈證,都應當留意這一點。 |
|
|
瘡家,身雖疼,不可發汗,汗出則痙。 |
||
|
瘡家病與外感不同,故治法與風寒亦異。若以風寒之法治之,其變亦不可不知也。瘡雖痛偏一處,而血氣壅遏,亦有遍身疼者,然與風寒有別。汗之則津液越出,筋脉血虛,攣急而為痙矣。諸脉症之當審,正此故耳。 |
瘡家之病和外感不同,所以治法與風寒也不同。如果用治療風寒的方法治療瘡家,可能出現之變化亦不可不知。瘡痛雖然是偏於一處,但血氣壅遏也會出現全身疼痛,只是與風寒所致之疼痛是不同的。發汗則使津液外出,筋脈血虛而失養,就會導致痙攣成痙證。各種脈證都應該加以辨別,正是因為這樣的緣故。 |
|
|
脉浮數者,法當汗出而愈。若身重心悸者,不可發汗,當自汗出乃觧。所以然者,尺中脉微,此裡虛,須表裡實,津液自和,便汗出愈。 |
||
|
脉浮數者,于脉法當汗。而尺中微,則不敢輕汗,以麻黃為重劑故也。此「表」指身,「裡」指心。有指營衛而反遺心悸者,非也。身重是表熱,心悸是裡虛。然悸有因心下水氣者,亦當發汗,故必審其尺脉。尺中脉微為裡虛。裡虛者,必須實裡。欲津液和,須用生津液。若坐而待之,則表邪愈盛,心液愈虛,焉能自汗?此「表」是帶言,只重在「裡」,至于自汗出,則裡實而表和矣。 |
脈浮數者,根據脈法應該用汗法。但尺中微,就不敢輕易發汗,因為麻黃湯是發汗之重劑。此處「表」,指的是身體,「裏」,指的是心。有人以為是指營衛而卻引發心悸,這是不對的。身重是因為表熱,心悸是因為裏虛。然而心悸也有因為心下有水氣所引發,也應當發汗,所以一定要審查尺脈。尺中脈微表示裏虛,裏虛就需要補裏氣。想要津液調和,必須採用生津液之法。如若只是等待,則表邪就會越來越盛,心液越來越虛,病人怎麼能自然汗出呢?此處之「表」字,只是順帶提及的,重點在「裏」,到了病人能自然汗出,就表明裏氣實而表氣和了。 |
|
|
寸口脉浮而緊,浮則為風,緊則為寒。風則傷衛,寒則傷營。營衛俱病,骨肉煩疼,當發其汗也。 |
||
|
風寒本自相因,必風先開腠理,寒得入于經絡。營衛俱傷,則一身內外之陽不得越,故骨肉煩疼,脉亦應其象而變見於寸口也。緊為陰寒,而從浮見,陰盛陽虛,汗之則愈矣。 緊者急也,即數也。緊以形象言,數以至數言。緊則為寒,指傷寒也;數則為熱,指發熱也。辭異而義則同,故脉浮數、浮緊者,皆是麻黃症。 脉法以浮為風,緊為寒,故提綱以「脉陰陽俱緊」者名「傷寒」。大青龍脉亦以浮中見緊,故名「中風」。則脉但浮者,正為風脈,宜麻黃湯,是麻黃湯固主中風脉症矣。麻黃湯症,發熱,骨節疼,便是骨肉煩疼,即是風寒兩傷,營衛俱病。先輩何故以大青龍治營衛兩傷?麻黃湯治寒傷營而不傷衛,桂枝湯治風傷衛而不傷營,曷不以桂枝症之惡寒,麻黃症之惡風,一反勘耶?要之冬月風寒,本同一體。故中風、傷寒,皆惡風、惡寒。營病衛必病。中風之重者,便是傷寒。傷寒之淺者,便是中風。不必在風寒上細分,須當在有汗、無汗上着眼耳。 |
風和寒本來就是相互影響,必然是風邪先打開腠理,寒邪才得以進入經絡,營衛都被風寒所傷,則全身內外之陽氣不能外達,因此會有骨肉劇痛,脈氣隨之也在寸口反映出來。脈緊代表陰寒,而與浮脈同見,反映陰盛陽虛,用汗法就可以了。 「緊」就是「急」,即是「數」。緊是從脈之形象而言,數是以脈之次數而言。「緊則為寒」,指的是傷寒;「數則為熱」,指的是發熱。用詞不同而意思卻一樣,所以脈浮數、脈浮緊都是麻黃湯證。 根據脈法,浮脈代表風邪,緊脈代表寒邪,所以提綱證將「脈陰陽俱緊」者稱為「傷寒」。大青龍湯證脈也是因為浮中見緊,所以命名為「中風」。所以只要見脈浮,正是風脈,應該用麻黃湯,是麻黃湯固然用來主治中風之脈證。麻黃湯證,發熱、骨節疼,就是骨肉劇痛,代表風寒兩傷,營衛俱病。前輩為甚麼只用大青龍湯治療營衛兩傷?如果麻黃湯是治療寒傷營卻不傷衛,桂枝湯是治療風傷衛卻不傷營,怎麼不根據桂枝湯證之惡寒,麻黃湯證之惡風,一一將其勘正過來呢?關鍵在於,冬月所遇到之風與寒本來是同一件事。所以無論中風或傷寒,都會出現惡風、惡寒。營氣受病則衛氣一定也會病。中風之重證,就是傷寒。傷寒之輕證,就是中風。無需在風或寒上仔細區分,而必須要在有汗或無汗上著眼。 |
|
|
太陽病,脉浮緊,無汗,發熱,身疼痛,八九日不解,表症仍在,此當發其汗,麻黃湯主之。服藥已微除,其人發煩目瞑,劇者必衂,衂乃解。所以然者,陽氣重故也。 |
||
|
脉症同大青龍而異者,外不惡寒,內不煩躁耳。「發於陽者,七日愈」,八九日不觧,其人陽氣重可知。然脉緊無汗,發熱身疼,是麻黃症未罷,仍與麻黃。只「微除」,在表之風寒而不觧,內擾之陽氣,其人發煩目瞑,見不堪之狀可知。陽絡受傷,必逼血上行而衂矣。血之與汗,異名同類。不得汗,必得血。不從汗解,而從衂解。此與「熱結膀胱,血自下」者,同一局也。 太陽脉從自目內眥,絡陽明脉于鼻。鼻者,陽也。目者,陰也。血雖陰類,從陽氣而升,則從陽竅而出,故陽盛則衂。陽盛則陰虛,陰虛則目瞑也。 解後復煩,煩見于內,此餘邪未盡,故用桂枝更汗。微除發煩,是煩于外見,此大邪已解,故不可更汗。仲景每有「倒句法」,前輩隨文衍義,謂當再用麻黃以散餘邪,不知「得衂乃觧」句何處着落? |
麻黃湯之脈證與大青龍湯證不同是,在外不惡寒,在內不煩躁。「發於陽者,七日愈」,而八九日都不解,就可知病人陽氣鬱閉之嚴重。但是脈緊無汗,發熱身疼痛,這是麻黃湯證尚未消退,所以仍然要讓病人服用麻黃湯。服藥後病證只是「微除」,是在表之風寒仍未得解,而陽氣內擾,則使病人煩躁而目暝,就可知病者不欲視物之狀態。陽絡受傷,就一定會逼血上行而鼻血。血與汗,雖然名稱不同但卻屬於同類。服藥後,不得出汗就一定會出血。病邪不能通過發汗而解,就會通過鼻血而解,這與「熱結膀胱,血自下」之局面是一樣的。 太陽脈從目內眥而出,在鼻側與陽明脈交接。鼻屬陽,目屬陰。血雖然屬於陰,但隨陽氣而升,因此從陽竅而出,所以陽盛則見鼻血。陽盛則陰虛,陰虛則目暝。 表解後又見煩躁,這是源自於內之煩躁,餘邪未被盡除,所以再用桂枝湯發汗。表邪微除而煩躁,是源自於外之煩躁,在表之病邪已基本被祛除,所以不可以再發汗。張仲景經常會採用「倒句法」,前輩們隨文衍義,說應該再用麻黃湯來祛散餘邪,如果這樣,不知道「得衄乃解」這一句應該如何理解呢? |
|
|
傷寒脉浮緊者,麻黃湯主之。不發汗,因致衂。 |
||
|
脉緊無汗者,當用麻黃湯發汗,則陽氣得泄,陰血不傷,所謂「奪汗者無血」也。不發汗,陽氣內擾,陽絡傷則衂血,是「奪血者無汗」也。若用麻黃湯再汗,液脫則斃矣。言「不發汗,因致衂」,豈有因致衂更發汗之理乎?觀少陰病無汗而強發之,則血從口鼻而出,或從目出,能不懼哉?愚故亟為校正,死誤人者多耳。 |
脈緊無汗,應該用麻黃湯發汗,則陽氣得以外泄,陰血就不受損傷,所謂「奪汗者無血」。如若不發汗,陽氣內擾,而陽絡受傷則出現鼻血,這就是所謂「奪血者無汗」。此時如果再用麻黃湯發汗,就會導致陰液盡脫死。說「不發汗,因致衄」,豈有因為鼻血而再發汗之理?看看少陰病無汗卻強行發汗,則會導致口鼻出血,或目中出血,能不感到害怕嗎?所以我認為必須盡快糾正此等錯誤,否則,因此而誤治致死者就太多了。 |
|
|
太陽病,脉浮緊,發熱,身無汗,自衂者愈。 |
||
|
汗者,心之液,是血之變,見于皮毛者也。寒邪堅斂於外,腠理不能開發,陽氣大擾于內,不能出玄府而為汗,故逼血妄行,而假道于肺竅也。今稱「紅汗」,得其旨哉。 |
汗就是心之液,是血之變化而見於於皮毛上。當寒邪凝於體表而使腠理不能宣透,被鬱閉之陽氣不能外出於玄府而為汗,則內擾而陽逼血妄行,借道於肺之竅而出。如今稱其為「紅汗」,是明白其中之理了。 |
|
|
衂家,不可發汗,汗出必額上陷,脉緊急,目直視,不能眴,不得眠。 |
||
|
太陽之脉,起自目內眥,上額。已脫血而復汗之,津液枯竭,故脉緊急,而目直視也,亦心腎俱絕矣。目不轉,故不能眴。目不合,故不得眠。 |
太陽之脈,從目內眥起始,循行上額。衄家已脫血,若再發汗,津液枯竭,故脈緊急而目睛直視,亦反映了心腎之氣已絕。目睛直視則目不轉,所以不能眴。眼睛不合,所以不得眠。 |
|
|
脉浮緊者,法當身疼痛,宜以汗解之。假令尺中遲者,不可發汗,以營氣不足,血少故也。 |
||
|
脉浮緊者,以脉法論,當身疼痛,宜發其汗。然寸脈雖浮緊,而尺中遲,則不得據此法矣。尺主血,血少則營氣不足。雖發汗,決不能作汗。正氣反虛,不特身疼不除,而亡血、亡津液之變起矣。「假令」是設辭,是深一層看法,此與「脉浮數而尺中微」者同義。陽盛者不妨發汗,變症惟衂,衂乃解矣。陰虛者不可發汗,亡陽之變,恐難為力。 |
根據脈法,脈浮緊時應該會身體疼痛,適宜用發汗之法。然而寸脈雖然浮緊,但是卻尺中脈遲,那就不能據此為法了。尺脈主血,血少則營氣不足。雖然用了汗法,決不能令人有汗。一旦汗出,正氣反虛,不但身體疼痛不會消除,而亡血、亡津液等變化隨之而起。「假令」,這種措辭是假設之意,作為深一層之看法,與「脈浮數而尺中微」之意相同。陽氣盛者不妨發汗,其變化只不過是鼻出血,之後反而病解。而陰虛者則不可發汗,出現亡陽之變化,恐怕就無能為力了。 |
|
|
太陽與陽明合病,喘而胸滿者,不可下,麻黃湯主之。 |
||
|
三陽俱受氣于胸中,而部位則屬陽明。若喘屬太陽,嘔屬少陽,故胸滿而喘者,尚未離乎太陽。雖有陽明可下之症,而不可下。如嘔多,雖有陽明可攻之症,而不可攻,亦以未離乎少陽也。 |
三陽都是在胸中受氣,而受氣之部位則屬於陽明。如果喘屬太陽病,嘔屬少陽病,則胸滿而喘,尚未脫離太陽病。雖然有陽明病可下之證,但不可用下法。如果多嘔吐,雖然有陽明病可攻之證,但不可攻之,因為病情仍未脫離少陽病。 |
|
|
陽明病,脉浮,無汗而喘者,發汗則愈,宜麻黃湯。 |
||
|
太陽有麻黃症,陽明亦有麻黃症,則麻黃湯不獨為太陽設也。見麻黃症即用麻黃湯,是仲景大法。 |
太陽病有麻黃湯證,陽明病也有麻黃湯證,那麼麻黃湯就不是專門為太陽病而設。見有麻黃湯證就用麻黃湯,這是仲景之大法。 |
|
|
右論麻黃湯脉症。 |
上面所論是麻黃湯之脈證。 |
|
|
太陽病,十日已去,脉浮細而嗜卧者,外已解也。設胸滿脇痛者,與小柴胡湯。脉但浮者,與麻黃湯。 |
||
|
脉微細,但欲寐,少陰症也。浮細而嗜卧,無少陰症者,雖十日後,尚屬太陽,此「表解而不了了」之謂。設見胸滿嗜卧,亦太陽之餘邪未散。兼脇痛,是太陽少陽合病矣,以少陽脉弦細也。少陽為樞,樞机不利,一陽之氣不升,故胸滿脇痛而嗜卧,與小柴胡和之。若脉浮而不細,是浮而有力也。無胸脇痛,則不屬少陽。但浮而不大,則不涉陽明,是仍在太陽也。太陽為開,開病反閤,故嗜卧。與麻黃湯以開之,使衛氣行陽,太陽仍得主外而喜寤矣。與太陽初病用以發汗不同,當小其制而少與之。 |
脈微細,只是想睡覺,這是少陰證。脈浮細而嗜臥,沒有少陰證者,即使病發十天後,還屬於太陽病,這就是所說的「表解而不了了」。假如證見胸滿嗜臥,亦是太陽病之餘邪沒有被驅散。兼見脅痛,這就是太陽少陽合病了,因為少陽病之脈是弦細。少陽為樞,樞機不利則一陽氣不升,所以有胸滿脅痛而嗜臥之證,用小柴胡湯和解少陽。如果脈浮而不細,就是浮而有力。沒有胸脅痛,那就不屬於少陽病。若脈象只浮而不大,就不涉及陽明病,仍然是太陽病。太陽為開,主「開」之病反而出現「合」的狀態,所以出現嗜臥。用麻黃湯來開發陽氣,使衛氣能行於陽分,太陽之氣仍得以主外,就會醒寤了。這與最初得太陽病時用發汗之法不同,劑量應該小一些,而且服用劑量也要少一些。 |
|
|
右論麻黃湯、柴胡湯相關脉症。 |
上面所論是麻黃湯、柴胡湯之相關脈證。 |
|
|
麻黃湯 麻黃二兩,去節 桂枝二兩 甘草一兩,炙 杏仁七十個,去尖 水九升,先煮麻黃減一升,去沬,內諸藥,煮二升半,溫服八合,覆取微似汗。不須啜粥,餘如桂枝法。 |
麻黃湯 麻黃二兩,去節 桂枝二兩 甘草一兩,炙 杏仁七十個,去尖 用九升水,先煮麻黃至八升水,撇去浮沫,再加入其餘藥物,煮到剩下二升半,每次溫服八合,蓋上被子取微微汗出。服藥後無須喝熱稀粥,但其餘的服藥及調息方法與桂枝湯方後注一樣。 |
|
|
麻黃色青入肝,中空外直,宛如毛竅骨節狀,故能旁通骨節,除身疼,直達皮毛,為衛分驅風散寒第一品藥。然必藉桂枝入心通血脉,出營中汗,而衛分之邪,乃得盡去而不留。故桂枝湯不必用麻黃,而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。杏為心果,溫能散寒,苦能下氣,故為驅邪定喘之第一品藥。桂枝湯發營中汗,須啜稀熱粥者,以營行脉中,食入于胃,濁氣歸心,淫精于脈故耳。麻黃湯發衛中汗,不須啜稀熱粥者,此汗是太陽寒水之氣,在皮膚間,腠理開而汗自出,不須假穀氣以生汗也。 |
麻黃之色青而入肝,中空外直,好似毛竅、關節一般,所以能旁通骨節而除身體疼痛,又能直達皮毛,是衛分驅除風寒之首選藥。但必須借助桂枝之入心而通血脈,能從營分中發汗,而衛分之病邪才能被全部驅除。所以桂枝湯中不必用麻黃,而麻黃湯中卻不可以沒有桂枝。杏仁為心之果,性溫能散寒,味苦能下氣,所以是驅邪定喘之首選藥。桂枝湯能從營分中發汗,服藥後必須喝熱稀粥,這是因為營氣行於脈中,水穀進入胃中後,其濃濁之氣歸於心,則精氣能佈散於脈中之緣故。麻黃湯從衛分中發汗,服藥後之所以不須喝熱稀粥,是因為衛中之汗來自於太陽寒水之氣,是在皮膚之間,只要腠理開而汗自然就會出,所以不需要借助穀氣來生成汗液。 |
|
|
服汗者,停後服,汗多亡陽,遂虛,惡風,煩躁不得眠也。汗多者,溫粉撲之。 |
||
|
此麻黃湯禁也。麻黃湯為發汗重劑,故慎重如此。其用桂枝湯,若不汗更服,若病重更作服,若不出汗,可服至二三劑。又,刺後,可復汗;汗後,可復汗;下後,可復汗。此麻黃湯但云「溫服八合」,不言「再服」,則一服汗者,停後服。「汗出多者,溫粉撲之」,自當列此後。大青龍煩躁,在未汗先,是為陽盛。此煩躁在發汗後,是為陰虛。陰虛則陽無所附,宜白虎加人參湯。若用桂附以囘陽,其不殺人者,鮮矣。 |
這是麻黃湯服藥後之禁忌。麻黃湯是發汗重劑,所以才會如此慎重。而服用桂枝湯後,如果不汗出就再服,如果病情嚴重則再服,如果一直不出汗,可以服至二三劑。再者,針刺後,可以再發汗;發汗後,可以再發汗;攻下後,也可以再發汗。這裏說麻黃湯只是「溫服八合」,沒有說「再服」,就是說在服用一次藥後有汗出,就要停服餘下之藥。「汗出多者,溫粉撲之」一句,自然應當列在麻黃湯之後。大青龍湯證之煩躁,發生在沒有發汗之前,是陽盛所致。這裏所說之煩躁是在發汗後出現,屬於陰虛。陰虛則陽無所依附,應該用白虎加人參湯。如果用桂枝、附子等藥來回陽,而不會導致死亡的情況發生,是很少見的。 |
|
傷寒論註卷之三 南陽 張機 仲景原文 慈谿 柯琴 韻伯編註 崑山 馬中驊驤北較訂 |
|
|
陽明脉證上 |
|
|
陽明之為病,胃家實也。 |
|
|
陽明為傳化之府,當更實更虛。食入胃實而腸虛,食下腸實而胃虛。若但實不虛,斯為陽明之病根矣。胃實不是陽明病,而陽明之為病,悉從胃實上得來,故以「胃家實」為陽明一經之總綱也。然致實之由,最宜詳審。有實于未病之先者,有實于得病之後者。有風寒外束,熱不得越而實者,有妄汗吐下,重亡津液而實者。有從本經熱盛而實者,有從他經轉屬而實者。此只舉其病根在實,而勿得以胃實即為可下之症。按:陽明提綱,與《內經·熱論》不同。《熱論》重在經絡,病為在表。此以裡証為主,裡不和,即是陽明病。他條或有表証,仲景意不在表。或兼經病,仲景意不在經。陽明為闔。凡裡証不和者,又以闔病為主。不大便固闔也,不小便亦闔也。不能食、食難用飽、初欲食,反不能食,皆闔也。自汗出、盜汗出,表開而裡闔也。反無汗,內外皆闔也。種種闔病,或然或否,故提綱獨以胃實為正。胃實不是竟指燥屎堅鞕,只對下利言。下利是胃家不實矣。故汗出觧後,胃中不和而下利者,便不稱「陽明病」。如胃中虛而不下利者,便屬陽明。即初鞕後溏者,總不失為「胃家實」也。所以然者,陽明太陰同處中州,而所司各別。胃司納,故以陽明主實;脾司輸,故以太陰主利。同一胃府而分治如此,是二經所由分也。 |
陽明為傳化之府,其特點是實與虛更替。進食後則胃實而腸虛,食物下行則腸實而胃虛。如果只有實而不虛,這就是陽明病之根源。胃實不是陽明病,而陽明病都是從胃實而來的,所以把「胃家實」作為陽明病之總綱。然而導致「胃家實」之緣由,最應該詳細審察。有的是在未病之前就已有,有的是在得病之後才有。有的是風寒外束,熱邪不得發越而成,有的是誤用汗、吐、下過度傷津液而成。有的是從本經病熱盛而成,有的是從他經之病傳變而成。這裡只指出其病根在「胃家實」,但不能將「胃家實」看作可攻下之證。按:陽明病之提綱與《內經‧熱論》不同。《熱論》重在經絡,討論的是病邪在表。此以裏證為主,裏氣不和,就是陽明病。其他條文或者有表證,但仲景只意不在表證或兼經表之病,仲景之意不在經脈。陽明為闔。凡裏證不和,又以闔病為主。不大便為闔,不小便亦為闔。不能食、或不能飽食、初欲食,反而不能食,這都闔。自汗出、盜汗出,為表開而裏闔。反無汗,則內外皆闔。種種闔病,或有或無,所以提綱證只以「胃家實」為方向。「胃家實」不全都指大便燥結堅硬,只是相對下利而言。下利就是胃家不實了。所以汗出解之後,胃中不和而下利,便不再稱為「陽明病」。如果胃中虛而不下利者,便屬於陽明病。即使是大便初硬後軟,總的來說亦不失為「胃家實」。之所以這樣,陽明與太陰氣同處中焦,而其功能各有不同。胃主受納,所以陽明病以實為主;脾主運化轉輸,所以太陰病以下利為主。同一胃腑而有如此之分治,這就是陽明、太陰二經所主之不同。 |
|
問曰:陽明病外証云何?答曰:身熱,汗自出,不惡寒,反惡熱也。 |
|
|
陽明主裡,而亦有外証者,有諸中而形諸外,非另有外証也。胃實之外見者,其身則蒸蒸然,裡熱熾而達于外,與大陽表邪發熱者不同。其汗則濈濈然,從內溢而無止息,與太陽風邪為汗者不同。表寒已散,故不惡寒。裡熱閉結,故反惡熱。只因有「胃家實」之病根,即見身熱、自汗之外証,不惡寒反惡熱之病情。然此但言病機發現,非即可下之証也,宜輕劑以和之。必譫語、潮熱、煩躁、脹滿,諸証兼見,纔為可下。 四証是陽明外証之提綱,故「胃中虛冷」,亦得稱「陽明病」者,因其外証如此也。 |
陽明病以裏證為主,然而亦有外證,這是有諸內而形諸外,不是另外又有外證。「胃家實」之外證,其身體有蒸蒸然之發熱,是裏熱熾盛而透達於外,與大陽病表邪發熱不同。其汗出是持續性的,從內往外溢而無休止,與太陽病風邪致汗不同。表寒已散,所以不惡寒。裏熱閉結,所以反惡熱。只因為有「胃家實」之病根,就會出現身熱、自汗之外證,與不惡寒反惡熱之病情。然而這裏只是說病機是什麼,而不是說即時可攻下之證,此宜用輕劑調和。必須等到有譫語、潮熱、煩躁、脹滿等各種證候,才可攻下。 此四證是陽明病外證之提綱,所以即使是「胃中虛冷」,亦可以稱為「陽明病」,是因為其外證就是這樣。 |
|
陽明病,脉浮而緊者,必潮熱,發作有時,但浮者,必盜汗出。 |
|
|
陽明脉証與太陽脉証不同。太陽脉浮緊者,必身疼痛、無汗、惡寒發熱不休。此則潮熱有時,是惡寒將自罷,將發潮熱時之脉也。此「緊反入裡」之謂,不可拘「緊則為寒」之說矣。太陽脉但浮者,必無汗。今盜汗出,是因于內熱,且與本經初病「但浮,無汗而喘」者不同,又不可拘「浮為在表」之法矣。脉浮緊,但浮而不合麻黃証,身熱、汗出而不是桂枝証。麻桂下嚥,陽盛則斃耳。此脉從經異,非脉從病反。要知仲景分經辨脉,勿專據脉談証。 |
陽明病治脈證與太陽病治脈證不同。太陽病脈浮緊,必然會身疼痛、無汗、惡寒發熱不休止。本條則是時有潮熱,這是惡寒即將消失,快要發潮熱時之脈證。這就是「緊反入裏」之意,不可拘泥於「緊脈為寒」之說。太陽病而只是脈浮,必然無汗。如今盜汗出,是由於有內熱,而且與本經初病時「脈浮,無汗而喘」不同,又不可拘泥於「脈浮為表」之法。脈浮緊,如果只是脈浮便不符合麻黃湯證,身熱、出汗而不是桂枝湯證。兩方一旦服用,因為陽盛則會斃命。這是在不同疾病中出現不同脈證,不是脈證與疾病相反。要明白仲景是根據不同經脈之病而論脈證,不是專門根據脈象來論證。 |
|
傷寒三日,陽明脉大。 |
|
|
脉大者,兩陽合明,內外皆陽之象也。陽明受病之初,病為在表,脉但浮而未大,與太陽同,故亦有麻黃、桂枝証。至二日惡寒自止,而反惡熱。三日來,熱勢太盛,故脉亦應其人而洪大也。此為「胃家實」之正脉。若小而不大,便屬少陽矣。 《內經》云「陽明之至,短而濇」,此指秋金司令之時脉。又曰「陽明脉象,大浮也」,此指兩陽合明之病脉。 |
脈大,是兩陽合明,內外均充斥熱邪之象。陽明受病之初,病邪在表,只是脈浮而卻未見脈大,與太陽病相同,所以亦有麻黃湯證、桂枝湯證。等到第二日惡寒自然消失,反而惡熱。三日以後,熱勢極盛,所以脈象亦與病人之熱勢而變洪大。這是「胃家實」之正脈。如果脈小而不大,便屬於少陽病。 《內經》說「陽明之至,短而澀」,這是指的是秋金當令之時脈。又說「陽明脈象,大浮」,這是指兩陽合明之病脈。 |
|
脉浮而大,心下反鞕。有熱屬藏者,攻之不令發汗。屬府者,不令溲數,溲數則大便鞕。汗多則熱愈,汗少則便難。脉遲尚未可攻。 |
|
|
此治陽明之大法也。陽明主津液所生病,津液乾,則胃家實矣。津液致乾之道有二:汗多則傷上焦之液,溺多則傷下焦之液。一有所傷,則大便鞕而難出,故禁汗與溲。夫脉之浮而緊、浮而緩、浮而數、浮而遲者,皆不可攻而可汗。此浮而大,反不可汗而可攻者,以為此陽明三日之脉,當知「大為病進」,不可拘「浮為在表」也。心下者,胃口也。心下鞕,已見胃實之一班。以表脉不當見裡証,故曰「反鞕」耳。「有熱屬藏」,是指心肺有熱,不是竟指胃實。「攻之」是攻其熱,非攻其實,即「與黃芩湯徹其熱」之義也。「不令」者,禁止之辭,便見瀉心之意,「上焦得通,津液自下,胃氣因和」耳。「屬府」,指膀胱,亦不指胃。膀胱熱,故溲數,「不令」處亦見當滋陰之義矣。「屬府」是陪說,本條重在「藏熱汗多」句,直接「發汗」句來。蓋汗為心液,汗出是「有熱屬藏」之徵也。所以「不令發汗」者何?蓋汗出多,津液亡而火就燥,則愈熱而大便難。即汗出少,亦未免便鞕而難出,故利于急攻耳。仲景治陽明,不患在胃家實而患在藏有熱,故急于攻熱而緩以下。其實禁汗與溲,所以存其津,正以和其實耳。然証有虛實,脉有真假。「假令脉遲」,便非藏實,是浮大皆為虛脉矣。仲景特出此句,正發明心下鞕一証有無熱屬藏者,為妄攻其熱者禁也。其慎密如此。 |
這是治療陽明病的基本原則。陽明主津液所生病,津液乾燥,則胃家成實。導致津液乾燥之原因有兩種:發汗多則傷上焦之津液,小便過多則傷下焦之津液。津液一有所傷,則大便硬而難出,所以陽明病禁用發汗與利小便。出現脈浮而緊、浮而緩、浮而數、浮而遲的話,都不可攻下而可以發汗。現在脈浮而大,反而不可發汗而可以攻下,是因為這陽明病第三日之脈,應該知道「大則病進」,而不可拘泥「浮脈為表」。心下,就是胃口。心下硬,已經是胃實之證。表證之脈不應該出現裏證,所以說「反硬」。「有熱屬臟」,是指心肺有熱,不是簡單地指胃實。「攻之」,是治其熱,不是攻逐實邪之意,亦就是「與黃芩湯撤其熱」之意。「不令」,是禁止之辭,由此便可見瀉心之意,如此可以達到「上焦得通,津液自下,胃氣因和」之效果。「屬腑」,指的是膀胱,亦不是指胃。膀胱有熱,所以小便數,從「不令溲數」可以知道應該要滋陰。「屬府」是襯托之文,本條重點在於「臟熱汗多」這句話,直接上承「發汗」一句。因為汗是為心液,汗出是「有熱屬臟」之反映。為甚麼要「不令發汗」呢?因為汗出多,則津液亡而導致火愈盛津液愈燥,熱愈盛則大便困難。就算出汗少亦難以避免大便硬而難出,所以需要迅速攻下。仲景治陽明病,不擔心胃家成實而擔心臟有熱,所以急於攻熱而緩於攻下。其實,禁發汗與利小便是為了保存津液,正是為了緩和實邪。然而,證有虛實,脈有真假。「假令脈遲」,便不是臟腑有實邪,凡浮大都是虛脈。仲景特意說出這一句,正是為了說明心下硬一證有「無熱屬藏」者,防止醫者誤用攻下。仲景就是如此審慎周。 |
|
陽明病,心下鞕滿者,不可攻之。攻之,利遂不止者死,利止者愈。 |
|
|
陽明証具而心下鞕,有可攻之理矣。然鞕而尚未滿,是熱邪散漫,胃中尚未乾也。妄攻其熱,熱去寒起,移寒于脾,實反成虛,故利遂不止也。若利能自止,是其人之胃不虛而脾家實,腐穢去盡而邪不留,故愈。上條熱既屬藏,利于急攻,所以存津液也。此條熱邪初熾,禁其妄攻,所以保中氣也。要知腹滿已是太陰一班,陽明太陰相配偶,胃實則太陰轉屬于陽明,胃虛則陽明轉屬于太陰矣。此仲景大有分寸處,診者大宜著眼。 |
陽明證已具而心下硬,便有可以攻下之理。但是雖然心下硬還未有腹滿,只是熱邪散漫,胃中津液尚未乾燥。如果妄攻其熱,熱邪去則寒邪起,寒邪傳至於脾,實證反而變成虛證,所以就下利不止。如果下利能自止,是因為病人之胃氣不虛而脾氣開始恢復,腐穢之邪去盡責病邪不留,所以就愈。上條所說既然熱邪屬臟,便應該迅速攻下,是為了保存津液。本條所說的是熱邪初起,嚴禁誤用攻下,是為了保護中氣。要知道腹滿已經是太陰病之證,陽明太陰互為表裏,胃氣實則太陰病傳回陽明病,胃氣虛則陽明病傳變至太陰病。仲景對此心中大有分寸,醫者應該著眼於此。 |
|
傷寒嘔多,雖有陽明証,不可攻之。 |
|
|
嘔多是水氣在上焦,雖有胃實証,只宜小柴胡以通液,攻之恐有「利遂不止」之禍。要知陽明病,津液未亡者,慎不可攻。蓋腹滿、嘔吐,是太陰陽明相關証。胃實胃虛,是陽明太陽分別處。胃家實,雖變証百出,不失為生陽。下利不止,參附不能挽回,便是死陰矣。 |
嘔吐多是因為水氣在上焦,雖然有胃實之證,只適宜用小柴胡湯來通行津液,攻下恐怕會出現「利遂不止」的禍。要明白陽明病時,如果津液未亡,就要慎重餓不可攻下。因為腹滿、嘔吐,是太陰病與陽明病均可見之證。胃實或胃虛,是區分陽明病和太陽病之要點。胃家實,雖然變證百出,仍然是生命之陽氣。如果下利不止,用人參、附子亦不能挽救,這便屬於死證。 |
|
陽明病,自汗出。若發汗,小便自利,此為津液內竭。大便雖鞕,不可攻之。當須自欲大便,宜蜜煎導而通之。若土瓜根及與大豬膽汁,皆可為導。 |
|
|
本自汗,便發汗,則上焦之液已外竭。小便自利,則下焦之液又內竭。胃中津液兩竭,大便之鞕可知,雖鞕而小便自利,是內實而非內熱矣。蓋陽明之實,不患在燥而患在熱。此內既無熱,只須外潤其燥耳。連用三「自」字,見胃實而無變証者,當任其自然而不可妄治。更當探苦欲之病情,于欲大便時,因其勢而利導之。不欲便者,宜靜以俟之矣。此何以故?蓋「胃家實」固是病根,亦是其人命根。禁攻其實者,先慮其虛耳。 |
本身是自汗,又進行發汗,則上焦之津液已經外竭。小便自利,則下焦之津液又內竭。胃中津液上下兩竭,可知大便必然會硬,雖然大便硬而小便卻自利,這只是內實而不是內熱。因為陽明之實證不擔心燥而擔心熱。現在既然無內熱,則只需要外潤其燥。連用三個「自」字,可見胃實如果沒有其他變證,應當順其自然而不可妄治。更應該探究一下病者之所苦與所欲,在想要大便時,因其勢而利導之。而不想大便的話,則應該靜靜地等到想大便時。這是為什麼呢?因為「胃家實」固然是陽明病治病根,亦是病人生命之根。禁止攻逐實邪,是已經考慮到病者之虛了。 |
|
陽明病,本自汗出,醫更重發汗。病已差,尚微煩不了了者,此必大便鞕故也。以亡津液,胃中乾燥,故令大便鞕。當問其小便日幾行。若本小便日三四行,今日再行,故知大便不久出。今為小便數少,以津液當還入胃中,故知不久必大便也。 |
|
|
治病必求其本。胃者,津液之本也。汗與溲皆本于津液。本自汗出,本小便利,其人胃家津液本多,仲景提出「亡津液」句,為世之不惜津液者告也。「病差」,指身熱、汗出言。「煩」,即惡熱之謂。煩而微,知惡熱將自罷。以「尚不了」,故大便鞕耳。「數少」,即「再行」之謂。大便鞕,小便少,皆因胃亡津液所致,不是陽盛于裡也。因胃中乾燥,則「飲入于胃」,不能「上輸于肺,通調水道,下輸膀胱」,故小便反少。而「遊溢之氣」,尚能「輸精于脾」,津液相成,還歸于胃,胃氣因和,則大便自出,更無用導法矣。以此見津液素盛者,雖亡津液而津液終自還。正以見胃家實者,每躊躇顧慮,示人以勿妄下與勿妄汗也。歷舉治法,「脉遲不可攻」,「心下滿不可攻」,「嘔多不可攻」,「小便自利與小便數少不可攻」。總見「胃家實」,不是可攻証。 |
治病必求其本。胃是津液之本。汗與小便都來自於津液,原本就自汗出,原本就小便利,說明病人胃家之津液素來旺盛,而仲景提出「亡津液」這句話,是對世醫不懂珍惜津液者提出告誡。「病差」,是指身熱、汗出而言。「煩」,就是「惡熱」之意。雖然煩但卻微,可知惡熱即將自然消退。因為「尚不了了」,所以大便硬。「數少」,即「再行」之意。大便硬,小便少,都是因為胃中沒有津液,不是陽熱盛於裏引致。由於胃中乾燥,所以當「飲入於胃」時,不能「上輸於肺,通調水道,下輸膀胱」,所以小便反而少了。而「遊溢之氣」尚能「輸精於脾」,所以就能產生津液,還歸於胃中,胃氣因此而調和,則大便就自然被排出,更無需用導法。由此可見,津液素盛之人,雖然曾亡津液而津液最終會自還。這正是為什麼見到胃家實,仲景往往都躊躇顧慮而告誡醫者不要妄用攻下與發汗。前面所列舉之治法,有「脈遲不可攻」,「心下滿不可攻」,「嘔多不可攻」,「小便自利與小便數少不可攻」。總之是說,「胃家實」並不是可攻下之證。 |
|
蜜煎方 蜜七分 右一味,于銅器內煎,凝如飴狀,攪之,勿令焦著。欲可丸,併手捻作挺,令頭銳,大如指,長二寸許。當熱時急作,冷則硬。以內穀道中,欲大便時乃去之。 |
蜜煎方 七分蜜 上一味,在銅器內煎熬,使之凝固如飴糖,不停攪拌,使其不要燒焦。然後快速弄成丸狀,並用雙手搓成條狀,使頭部成尖狀,整條像手指一樣大,長約二寸多。要趁熱時製作,冷欲後則會變硬。將其放入肛門中,在想大便才去掉它。 |
|
猪膽汁方 大猪膽一枚,瀉汁,加醋少許,灌穀道中,如一食頃,當大便出宿食滯惡物,甚效。 |
豬膽汁方 一枚大豬膽,擠出膽汁,加一些醋,灌入肛門中,大約吃一頓飯之功夫,大便應當排出宿食及留滯之惡物,很有功效。 |
|
問曰:病有得之一日,不發熱而惡寒者,何也?答曰:雖得之一日,惡寒將自罷,即自汗出而惡熱也。 |
|
|
陽明受病,當二三日發。上條是指其已發熱言,此追究一日前未發熱時也。初受風寒之日,尚在陽明之表,與太陽初受時同,故陽明亦有麻黃、桂枝証。二日來,表邪自罷,故不惡寒。寒止熱熾,故汗自出而反惡熱,「兩陽合明」之象見矣。陽明病,多從他經轉屬,此因本經自受寒邪,胃陽中發,寒邪即退,反從熱化故耳。若因亡津液而轉屬,必在六七日來,不在一二日間。本經受病之初,其惡寒雖與太陽同,而無頭項強痛為可辨。即發熱、汗出,亦同太陽桂枝証,但不惡寒、反惡熱之病情,是陽明一經之樞紐。本經受邪,有中面、中膺之別。中面則有目疼、鼻乾,邪氣居高,即熱反勝寒,寒邪未能一日遽止。此中于膺部,位近于胃,故退寒最捷。 |
陽明受邪,應該在二三天發病。上條是針對病人已經發熱而言,本條則追究一日前尚未發熱之時的情況。最初受風寒之日,病邪尚在陽明之表,與太陽最初受邪時相同,所以陽明病亦有麻黃湯證、桂枝湯證。二天日,陽明之表邪自然消退,所以就不惡寒了。表寒止而裏熱熾盛,所以有自出汗而反惡熱,出現了「兩陽合明」之象。陽明病大多從他經轉屬而成,而本條則是因為本經自受寒邪,胃陽從中而發動,寒邪即退,反而從陽化熱。如果因為亡津液而轉屬為陽明病,一定是在六七日之后,而不在一二日之內。陽明本經受邪之初,惡寒雖然與太陽病相同,但卻沒有頭頸強痛而可以辯證。一二日之後隨即發熱、汗出,亦跟太陽病之桂枝湯證相同,但不惡寒、反惡熱之病情則是陽明一經之樞紐。陽明本經受病,有中於面和中於膺之分別。中於面則有目疼、鼻乾之證,邪氣居於高位,即使熱反能勝寒,寒邪亦不能一天就消退。這是邪氣中於膺部,位置靠近胃,所以退寒最快捷。 |
|
問曰:惡寒何故自罷?答曰:陽明居中,土也,萬物所歸,無所復傳。始雖惡寒,二日自止,此為陽明病也。 |
|
|
太陽病八九日,尚有惡寒証。若少陽寒熱往來,三陰惡寒轉甚,非發汗、溫中,何能自罷?惟陽明惡寒,未經表散,即能自止,與他經不同。「始雖惡寒」二句,語意在「陽明居中」句上。夫知陽明之惡寒易止,便知陽明為病之本矣。胃為戊土,位處中州,表裡寒熱之邪,無所不歸,無所不化,皆從燥化而為實。實則無所復傳,此「胃家實」所以為陽明之病根也。 |
太陽病八九日,尚有惡寒之證。如果是少陽病之寒熱往來,三陰病中惡寒變得更嚴重,如果不用發汗與溫中治法,惡寒怎麼會自然消失呢?只有陽明病之惡寒,未經發散表邪,惡寒便自然消散,與其他經之病不同。「始雖惡寒」這二句話,其意落在「陽明居中」之句上。知道陽明病之惡寒容易消散,就可知這是陽明病了。胃屬戊土,位於中焦,表裡寒熱之邪,沒有不歸屬於土,亦沒有不會被土所化,都會從陽明之燥化而變成胃實。胃實之後就不會再傳變,這就是為什麼「胃家實」成為陽明病之病根。 |
|
○右論胃實証。 |
○上面所論是胃實證。 |
|
問曰:太陽緣何而得陽明病?答曰:太陽病,若發汗,若下,若利小便,亡津液,胃中乾燥,因轉屬陽明。胃實大便難,此名陽明也。 |
|
|
此明太陽轉屬陽明之病,因有此亡津液之病機,成此「胃家實」之病根也。按:仲景陽明病機,其原本《經脉篇》「主津液所生病」句來,故雖有《熱論》中身熱、鼻乾等症,總歸重在津液上。如中風之口苦、咽乾、鼻乾、不得汗、身目黃、小便難,皆津液不足所致。如腹滿、小便不利、水穀不別等症,亦津液不化使然。故仲景諄諄以亡津液為治陽明者告也。 |
本條表明太陽病轉屬為陽明病,是由於有亡津液之病機而形成了「胃家實」之病根。按:仲景對陽明病病機之認識,是源自於《素問‧經脈》中「主津液所生病」這句話,所以雖然《素問‧熱論》有發熱、鼻乾等證,都將重點都放在津液上。例如中風證之口苦、咽乾、鼻乾、不得出、身目發黃、小便難等,都由津液不足所導致。又如腹滿、小便不利、水穀不別等證,亦是津液不化所導致。所以仲景不停告誡醫者,治陽明病時不要招致亡津液。 |
|
陽脉微而汗出少者,為自和也。汗出多者,為太過。陽脉實,因發其汗,出多者亦為太過。太過為陽實于裡,亡津液,大便因鞕也。 |
|
|
陽明主津液所生病者也。因妄汗而傷津液,致胃家實耳。桂枝証本自汗,自汗多則亡津。麻黃証本無汗,發汗多亦亡津。此雖指太陽轉屬,然陽明表証亦有之。 |
陽明「主津液所生病」。因為誤用汗法而傷津液,導致胃家實。桂枝湯證本有自汗出,自汗出多責亡津液。麻黃湯證本無汗,發汗過多亦會亡津液。這雖然是指太陽病轉屬陽明病而言,但陽明病表證亦會有同樣之變化。 |
|
本太陽病,初得時,發其汗,汗先出不徹,因轉屬陽明也。 |
|
|
「徹」,止也,即「汗出多」之互辭。 |
「徹」,就是停止之意,即「汗出多」之互辭。 |
|
傷寒轉屬陽明者,其人濈然微汗出也。 |
|
|
此亦「汗出不止」之互辭,概言傷寒,不是專指太陽矣。 |
這亦是「汗出不止」之互辭,泛泛地說傷寒病,而不是專指太陽病。 |
|
傷寒發熱,無汗,嘔不能食,而反汗出濈濈然者,是轉屬陽明也。 |
|
|
胃實之病机,在汗出多,病情在不能食。初因寒邪外束,故無汗。繼而胃陽遽發,故反汗多。即嘔不能食時,可知其人胃家素實,與乾嘔不同。而反汗出,則非太陽之中風,陽明之病實矣。 |
胃實之病機在於汗出多,病情上則在於不能食。病初時由於寒邪外犯於表,所以無汗。接著便胃陽發動,所以反汗多。即使在嘔而不能食之時,都可知病者胃家之氣素來旺實,與乾嘔不同。反而汗出,則不是太陽病之中風證,而是陽明病之胃實。 |
|
太陽病,寸緩、關浮、尺弱,其人發熱汗出,復惡寒不嘔,但心下痞者,此以醫下之也。如不下者,病人不惡寒而渴者,此轉屬陽明也。小便數者,大便必鞕。不大便十日,無所苦也。渴欲飲水者,少少與之。但以法救之,宜五苓散。 |
|
|
此病机在渴,以桂枝脉証而兼渴,其人津液素虧可知。小便數,則非消渴矣。以此知大便雖鞕,是津液不足,不是胃家有餘。即十日不便,而無痞滿硬痛之苦,不得為承氣証。飲水,利水,是胃家實而脉弱之正治也。不用豬苓湯,用五苓散者,以表熱未除故耳。此為太陽陽明之併病,餘義見五苓証中。 |
此病機在於口渴,因為桂枝湯脈證而兼有口渴,可知病人津液素虧。此時小便數,並不是消渴。由此可知大便雖然硬,是因為津液不足,不是胃家之氣有餘。即使十天不大便,但沒有痞滿硬痛之證,就不可認為是承氣湯證。渴而欲飲而利於飲水,是胃家實而脈弱之正治。不用豬苓湯而用五苓散,是因為表熱未除。這是太陽陽明併病,其他需要理解之文意將在後面五苓證中討論。 |
|
傷寒脉浮緩,手足自溫者,繫在太陰。太陰者,身當發黃。若小便自利者,不能發黃。至七八日大便鞕者,為陽明病也。 |
|
|
太陰受病,轉屬陽明者,以陽明為燥土,故非經絡表裡相關所致,總因亡津液而致也。此病機在小便,小便不利,是津液不行,故濕土自病,病在肌肉。小便自利,是津液越出,故燥土受病,病在胃也。 客曰:病在太陰,同是小便自利,至七八日暴煩下利者,仍為太陰病。大便鞕者,轉為陽明病。其始則同,其終則異,何也?曰:陰陽異位,陽道實,陰道虛。故脾家實,則腐穢自去,而從太陰之開。胃家實,則地道不通,而成陽明之闔。此其別也。 |
太陰受邪而病,之所以轉屬而為陽明病,是由於陽明屬燥土,與太陰、陽明在經絡上相互絡屬而為表裏無關,總是因為亡津液而導致。此處病機在小便,小便不利,反映津液無以運化,所以脾之濕土自病,病變在肌肉。小便自利,表示津液有所出,所以胃明燥土受病,病位在胃。 有客問曰:太陰病,同樣是小便通利,病至七八日而突然煩躁而下利,仍然是太陰病。如果大便硬,則轉成陽明病。其病初始相同,最後則不一樣,為甚麼呢?回答說:這與陰陽異位有關,即所謂「陽道實,陰道虛」。因為脾家之氣充實,腐穢之邪自然能除去,而與「太陰為開」相應。但如果胃家氣實,則地道不通,而形成陽明之闔病。這就是兩者之分別。 |
|
右論他經轉屬証。 |
上面所論是從他經轉屬之陽明證。 |
|
問曰:脉有陽結、陰結,何以別之?答曰:其脉浮而數,能食,不大便者,此為實,名曰陽結也,期十七日當劇。其脉沉而遲,不能食,身體重,大便反鞕,名曰陰結也,期十四日當劇。 |
|
|
脉以浮為陽,為在表;數為熱,為在府。沉為陰,為在裡;遲為寒,為在藏。証以能食者為陽,為內熱;不能食者為陰,為中寒。身輕者為陽,重者為陰。不大便者為陽,自下利者為陰。此「陽道實,陰道虛」之定局也。然陽証亦有自下利者,故陰証亦有大便鞕者。實中有虛,虛中有實,又陰陽更盛更虛之義。故胃實因于陽邪者,為「陽結」。有因于陰邪者,名「陰結」耳。然陽結能食而不大便,陰結不能食而能大便,何以故?人身腰以上為陽,腰以下為陰。陽結則陰病,故不大便。陰結則陽病,故不能食。此「陽勝陰病,陰勝陽病」之義也。凡三「候」為半月,半月為一「節」。凡病之不及太過,斯皆見矣。能食、不大便者,是但納不輸為太過。十七日劇者,「陽主進」,又合乎陽數之奇也。不能食而硬便仍去者,是但輸不納為不足。十四日劇者,「陰主退」,亦合乎陰數之偶也。《脉法》曰:「計其餘命生死之期,期以月節剋之。」《內經》曰「能食者過期,不能食者不及期」,此之謂也。 此條本為陰結發論,陽結即是胃實,為陰結作伴耳。陰結無表証,當屬之少陰,不可以身重、不能食為陽明應有之証,沉遲為陽明當見之脉,大便鞕為胃家實,而不敢用溫補之劑也。且陰結與固瘕、穀疸有別,彼溏而不便,是虛中有實;此鞕而有便,是實中有虛,急須用參附以回陽,勿淹留期至而不救。 |
就脈象而言,浮為陽,病在表;數為熱,病在腑。沉為陰,病在裏;遲為寒,病在臟。就證候而言,能食為陽,為內熱;不能食為陰,為中寒。身輕為陽,身重為陰。不大便為陽,自下利為陰。這就是所謂「陽道實,陰道虛」之定局。但是陽證亦有自下利,所以陰證亦有大便硬。實中有虛,虛中有實,又是陰陽虛實不斷更變之義。所以胃實因為陽邪所致者就是陽結。而胃實因為陰邪所致者就是陰結。但是陽結者能食而不大便,陰結者不能食而能大便,這是為什麼呢?人身腰部以上屬陽,腰部以下屬陰。陽結則陰病,所以不大便。陰結則陽病,所以不能食。這就是「陽勝陰病,陰勝陽病」之意。凡是三「候」為半個月,半月是一「節」。凡病情之太過或不及,都可以根據日子來判斷其變化。能食而不大便者,是因為水穀只被受納而不能被傳導,這屬於太過。十七日病情加重者,是因為「陽主進」,這亦符合陽數為奇數之特點。不能食而硬便仍被排出者,是因為水穀只被傳導而沒有被收納,就屬於不足。十四天病情加重者,是因為「陰主退」,亦符合陰數為偶數之特點。《平脈法》說:「計其餘命生死之期,期以月節數剋之。」《內經》說「能食者過期,不食者則不及期」,說的即是此意。 本條本來是為了討論陰結,陽結就是胃實,只不過是作為陰結之陪襯。陰結無表證,應當屬於少陰病,不可以把身重、不能食作為陽明病應有之證,脈沉遲是陽明病應有之脈,大便硬就是胃家實,因而不敢用溫補之方。而且陰結與固瘕證、穀疸證有所區別,固瘕或穀疸是便溏且又不大便,是虛中有實;此則大便硬而仍能大便,是實中有虛,需要迅速用人參、附子來回陽,不要拖延時間,以免失去救治之機會。 |
|
○右論陰陽結証。 |
○前面所論是陰陽結之證候。 |
|
陽明病,脉遲,汗出多,微惡寒者,表未觧也。可發汗,宜桂枝湯。陽明病,脉浮,無汗而喘者,發汗則愈,宜麻黃湯。 |
|
|
此陽明之表証、表脉也。二証全同太陽,而屬之陽明者,不頭項強痛故也。要知二方專為表邪而設,不為太陽而設。見麻黃証,即用麻黃湯;見桂枝証,即用桂枝湯,不必問其為太陽、陽明也。若惡寒一罷,則二方所必禁矣。 |
這是陽明病之表證、表脈。二證與太陽病完全相同,而之所以屬於陽明病,是因為沒有頭項強痛之證。要明白此兩方專為表邪而設,不是專門為太陽病而設。出現麻黃湯證,就用麻黃湯;出現桂枝湯證,就用桂枝湯,不必問其是太陽病還是陽明病。如果惡寒一旦消失,就不能再用此二方了。 |
|
陽明病,脉浮而緊者,必潮熱發作有時。但浮者,必盜汗出。 |
|
|
上條脉証與太陽相同,此條脉証與太陽相殊。此陽明半表半裡之脉証,麻桂下嚥,陽盛則斃耳。故善診者,必據証辨脉,勿據脉談証。全註觧見本篇之前。 |
上條脈證與太陽病相同,本條脈證則與太陽病不同。這是陽明病半表半裏之脈證,服麻黃湯、桂枝湯後,如果病人陽邪旺盛則會因此而斃命。所以善於診病之醫者,必須根據證候而論脈象,不應根據脈象而解釋證候。本條完整之註解已在本篇之前談及。 |
|
脉浮而遲,面熱赤而戰惕者,六七日當汗出而觧。遲為無陽,不能作汗,其身必癢也。 |
|
|
此陽明之虛証、虛脉也。邪中于面,而陽明之陽上奉之,故面熱而色赤。陽併于上而不足于外衛,寒邪切膚,故戰惕耳。此脉此証,欲其惡寒自止,于二日間,不可得矣。必六七日胃陽來復,始得汗出溱溱而觧。所以然者,汗為陽氣,遲為陰脉。無陽不能作汗,更可以身癢驗之,此又當助陽發汗者也。 |
這是陽明病之虛證、虛脈。邪氣侵犯面部,而陽明之陽氣抗邪於上,所以面熱而發紅。陽氣抗邪於上則無以衛外,寒邪犯人之肌膚,所以戰惕。此等脈證,要想惡寒在二日內自然消散,是不可能的。必須等到六七日後胃陽恢復,才能得汗出而解。之所以這樣,因為汗為陽氣所化,脈遲為陰脈。無陽氣則不能化為汗,醫者又可以根據身癢對此加以判斷,這應該輔助陽氣以發汗。 |
|
陽明病,法多汗,反無汗,其身如蟲行皮膚中,此久虛故也。 |
|
|
陽明氣血俱多,故多汗。其人久虛,故反無汗。此又當益津液,和營衛,使陰陽自和而汗出也。 |
陽明氣血俱多,所以陽明病時汗出多。病人如果久虛,所以反而無汗。此時又應該補益津液,調和營衛,使陰陽調和則自然汗出。 |
|
陽明病,反無汗而小便利,二三日嘔而欬,手足厥者,必苦頭痛。若不欬不嘔,手足不厥者,頭不痛。 |
|
|
小便利,則裡無瘀熱可知。二三日無身熱、汗出、惡熱之表,而即見嘔、欬之裡,似乎熱發乎陰。更手足厥冷,又似病在三陰矣。若頭痛,又似太陽之陰証。然頭痛必因欬、嘔、厥逆,則頭痛不屬太陽。欬、嘔、厥逆,則必苦頭痛,是厥逆不屬三陰,斷乎為陽明半表半裡之虛証也。此胃陽不敷布于四肢,故厥;不上升于額顱,故痛。緣邪中于膺,結在胸中,致嘔、欬而傷陽也。當用瓜蒂散吐之,嘔、欬止,厥、痛自除矣。兩「者」字作「時」字看更醒。 |
小便利,則知裏無瘀熱。二三日時,沒有發熱、汗出、惡熱等表證,卻出現嘔吐、咳嗽等裏證,看似熱發於陰。更見手足厥冷,又好像病在三陰。如見頭痛,又好像是太陽病之陰證。但是頭痛必然是由於咳嗽、嘔吐、厥逆而作,則頭痛不屬於太陽病。咳嗽、嘔吐、厥逆,必然有頭痛之苦,則此厥逆不屬於三陰病,因而可以斷定為此為陽明病半表半裏之虛證。胃陽不能布散於四肢,所以厥冷;不能上升至額頭,所以頭痛。由於邪氣侵犯胸中而導致咳嗽、嘔吐,因而傷及陽氣。應該用瓜蒂散催吐,咳嗽、嘔吐停止後,厥冷、頭痛自然就會消除了。條文中兩個「者」字應該按「時」字解,則更清楚。 |
|
陽明病,但頭眩,不惡寒,故能食而欬,其人必咽痛。若不欬者,咽不痛。 |
|
|
不惡寒、頭不痛但眩,是陽明之表已罷。能食而不嘔、不厥但欬,乃是欬為病本也。咽痛因于欬,頭眩亦因于欬,此邪結胸中而胃家未實也,當從小柴胡加減法。 |
不惡寒、頭不痛而只是眩暈,這是陽明之表證已解。能食而不嘔吐、不厥冷,只見咳嗽,可知咳嗽是此病之根本。咽痛是由於咳嗽,頭暈亦是由於咳嗽,這表示病邪結聚於胸中而胃家未實,應該用小柴胡湯加減進行治療。 |
|
陽明病,口燥,但欲漱水不欲嚥者,此必衂。 脉浮,發熱,口乾,鼻燥,能食者則衂。 |
|
|
此邪中于面,而病在經絡矣。液之與血,異名而同類。津液竭,血脉因之而亦傷,故陽明主津液所生病,亦主血所生病。陽明經起于鼻,繫于口齒。陽明病則津液不足,口鼻乾燥。陽盛則陽絡傷,故血上溢而為衂也。口鼻之津枯涸,故欲漱水。不欲嚥者,熱在口鼻,未入乎內也。能食者,胃氣強也。以脉浮、發熱之証,而見口乾、鼻燥之病機。如病在陽明,更審其能食、不欲嚥水之病情,知熱不在氣分而在血分矣。此問而知之也。 |
這是邪氣侵犯面中,而病位則在經絡。津液與血,名稱不同但卻都屬於同一類。津液枯竭,血脈亦因此而損傷,所以陽明不僅主津液所生病,亦主血所生病。陽明經起於鼻,與口齒相連。陽明病則津液不足,故口鼻乾燥。陽邪盛則陽絡受損,所以血上溢而流鼻血。口鼻之津液枯涸,所以想漱口。但卻不欲下咽,是因為熱邪在口鼻而尚未入於內。能食,表示胃氣強。根據脈浮、發熱之證,就可見口乾、鼻燥之病機。如果病至陽明,更要審察其能食、不欲飲水之病情,就可知其熱邪不在氣分而在血分了。這是通過問診而知之。 |
|
按:太陽、陽明皆多血之經,故皆有血証。太陽脉當上行,營氣逆不循其道,反循巔而下至目內眥,假道于陽明自鼻額而出鼻孔,故先目瞑、頭痛。陽明脉當下行,營氣逆而不下,反循齒環唇而上循鼻外至鼻額而入鼻,故先口燥、鼻乾。異源而同流者,以陽明經脉起于鼻之交頞中,旁納太陽之脉故也。 二條但言病機,不及脉法主治,宜桃仁承氣、犀角地黃輩。 |
按:太陽與陽明都是多血之經脈,所以都可以出現血證。太陽脈本應向上循行,但營氣逆行而不循常道,反而從巔而下行至目內眦,借道於陽明之脈而從鼻額而出到鼻孔,所以先有眩暈、頭痛。陽明脈本應下行,營氣逆而不下行,反而沿齒環唇而上循鼻外至鼻額而後進入鼻子中,所以先口燥、鼻乾。這種異原而同流之象,是因為陽明經脈始起於鼻之交頞中,又與旁邊之太陽脈相交。 此二條條文只說到了病機,沒有提及脈證與主治方法,可以用桃仁承氣湯、犀角地黃湯之類。 |
|
○右論陽明在表脉証。 |
○前面所論為陽明病在表之脈證。 |
|
傷寒四五日,脉沉而喘滿。沉為在裡,而反發其汗,津液越出,大便為難。表虛裡實,久則讝語。 |
|
|
喘而胸滿者,為麻黃証,然必脉浮者,病在表,可發汗。今脉沉,為在裡,則喘滿屬于裡矣。反攻其表則表虛,故津液大泄。喘而滿者,滿而實矣,因轉屬陽明,此譫語所由來也,宜少與調胃。汗出為表虛,然是陪話,歸重只在裡實。 |
喘而胸滿是麻黃湯證,但必須見脈浮而病在表,才可以發汗。如今脈沉,表示病在裏,則喘而胸滿屬於裏證。反而發汗解表就會導致表虛,所以津液大泄。喘而胸滿,滿則為實,因而轉屬陽明,這就出現譫語之原因,可以服用少量調胃承氣湯。汗出為表虛,只是作為陪襯之,本條重點只在裏實。 |
|
發汗多,若重發汗者,亡其陽,讝語,脉短者死,脉自和者不死。 |
|
|
上條論譫語之由,此條論譫語之脉。「亡陽」,即「津液越出」之互辭。心之液為陽之汗,脉者血之府也。心主血脉,汗多則津液脫,營血虛,故脉短是營衛不行,藏府不通,則死矣。此譫語而脉自和者,雖津液妄泄,而不甚脫,一惟胃實。而營衛通調,是脉有胃氣,故不死。此下歷言譫語不因于胃者。 |
上條討論了譫語之原因,本條則討論譫語之脈象。「亡陽」,與「津液越出」是互辭。汗為心之液,脈為血之府。心主血脈,汗多則津液受損,營血虧虛,所以脈短反映營衛運行失常,臟府氣血不通,這是死證。這裏所說譫語而脈調和者,雖然發汗而使津液被泄,但未至於嚴重受損,只不過是導致胃實。而營衛通暢,反映脈有胃氣,所以不屬死證。以下所涉及之譫語都與胃無關。 |
|
讝語,直視,喘滿者,死。下利者,亦死。 |
|
|
上條言死脉,此條言死証。蓋譫語本胃實,而不是死証。若譫語而一見虛脉、虛証,則是死証,而非胃家實矣。藏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,目不轉睛,不識人,藏府之氣絕矣。喘滿見于未汗之前,為裡實;見于譫語之時,是肺氣已敗。呼吸不利,故喘而不休,脾家大虛,不能為胃行其津液,故滿而不運。若下利不止,是倉廩不藏,門戶不要也。與大便難而譫語者,天淵矣。 |
上條所說是死脈,本條所說是死證。因為譫語原本由於胃實,而不是死證。如果譫語而一見虛脈、虛證,這才是死證,而不是胃家實。五臟六腑之精氣都上注於目,目不能轉睛而又不識人,則臟府之氣已絕。喘滿出現在未汗出之前,屬於裏實;而在譫語時又有喘滿,表示肺氣已經敗壞。呼吸不利,所以氣喘不休,這是脾氣大虛而不能為胃行其津液,所以滿而氣不運行。如果下利不止,反映脾胃不能如倉廩般守護其門戶。這與大便難而譫語屬於胃實是完全不一樣的。 |
|
夫實則讝語,虛則鄭聲。鄭聲,重語也。 |
|
|
同一譫語,而有虛實之分。「邪氣盛則實」,言雖妄誕,與發狂不同,有莊嚴狀,名曰「讝語」。「正氣奪則虛」,必目見鬼神,故鄭重其語,有求生求救之狀,名曰「鄭聲」。此即從讝語中分出,以明讝語有不因胃實而發者,更釋以「重語」二字,見鄭重之謂,而非鄭重之音也。若造字出于喉中,與語多重復叮嚀者不休等義,誰不知其虛,仲景烏庸辨? |
同一譫語,而有虛實之分。「邪氣盛則實」,言語雖然狂妄放肆,但與發狂不同,有莊嚴之狀,稱為「讝語」。「正氣奪則虛」,必然目見鬼神,所以鄭重地說話,有求生求救之狀,稱為「鄭聲」。這是從讝語中分出來的,以表明讝語有可能不因胃實而引發,仲景更以「重語」來解釋「鄭聲」,以見鄭重之意,而不是鄭重之聲音。發聲本出於喉中,如果「鄭聲」與說語多重復而叮嚀不休之意思相同的話,誰不知道這是虛證,仲景哪裏需要再去分辨? |
|
陽明病,下血譫語者,此為熱入血室。但頭汗出者,刺期門,其隨實而瀉之,濈然汗出則愈。 |
|
|
血室者,肝也。肝為藏血之藏,故稱「血室」。女以血用事,故下血之病最多,若男子非損傷,則無下血之病。惟陽明「主血所生病」,其經多血多氣,行身之前,鄰于衝任。陽明熱盛,侵及血室,血室不藏,溢出前陰,故男女俱有是証。血病則魂無所歸,心神無主,譫語必發。要知此非胃實,因熱入血室而肝實也。肝熱,心亦熱。熱傷心氣,既不能主血,亦不能作汗,但頭有汗,而不能遍身,此非汗吐下法可愈矣。必刺肝之募,引血上歸經絡,推陳致新,使熱有所洩,則肝得所藏,心得所主,魂有所歸,神有所依,自然汗出週身,血不妄行,譫語自止矣。按:畜血、便膿血,總是熱入血室,入于腸胃,從肛門而下者,謂之便血、膿血。蓋女子經血出子戶,與溺道不同門。男子精、血、溺三物,內異道而外同門。精道由腎,血道由肝,水道由膀胱,其源各別,而皆出自前陰。 |
血室,就是肝。肝為藏血之臟,所以稱為「血室」。女人以血為本,所以下血之病最多。男人如果不是外傷,就沒有下血之病。只有陽明「主血所生病」,其經脈多血多氣,循行在身體正前方,與衝任之脈相鄰。陽明熱盛而侵入血室,血室之血不藏,於前陰溢出,所以男女都有這種病證。血病就導致魂無所歸,心神無主,必然出現譫語。要明白這不是胃實,是因為熱入血室而導致肝實證。肝熱,心亦熱。熱邪傷及心氣,既不能主血,也不能使汗出,因此只見頭上有汗而不能遍及全身,這不是發汗、涌吐、攻下之法所能治。必須針刺肝經之募穴,引血上歸於經絡,推陳致新,使熱邪泄出,肝能恢復藏血功能,心能主神明,魂有所歸,神有所依,自然遍身汗出,血不妄行,譫語自然就停止了。按:蓄血與大便膿血,都是熱入血室而熱邪入於腸胃,從肛門而下血,稱為便血、膿血。因為女子經血從子宮而出,與尿道屬於不同之出口。而男子之精、血、小便三物,在內雖然不同通道,但在外則同一出口而出。精道出自於腎,血道出自於肝,小便出自於膀胱,其源頭各有區別,而都出自前陰。 |
|
期門,肝之募也,又足太陰、厥陰、陰維之會。太陰陽明為表裡,厥陰少陽為表裡。陽病治陰,故陽明、少陽血病,皆得刺之。 |
期門,是肝經之募穴,又是足太陰、足厥陰、陰維脈之交會穴。太陰與陽明相表裏,厥陰與少陽亦相表裏。陽病而治陰,所以陽明病與少陽病之血病,都可以刺期門。 |
|
婦人中風,發熱惡寒,經水適來。得之七八日,熱除而脉遲、身涼、胸脅下滿如結胸狀、譫語者,此為熱入血室也。當刺期門,隨其實而瀉之。 |
|
|
人之十二經脉,應地之十二水,故稱血為「經水」。女子屬陰而多血。脉者,血之府也。脉以應月,故女子一月經水溢出,應時而下,故人稱之為「月事」也。此言婦人適于經水來時,中于風邪,發熱惡寒,此時未慮及月事矣。病從外來,先觧其外可知。至七八日熱除、身涼、脉遲為愈。乃反見胸脅苦滿,而非結胸,反發詀語而非胃實,何也?脉遲故也。遲為在藏,必其經水適來時,風寒外來,內熱乘肝,月事未盡之餘,其血必結。當刺其募以瀉其結熱,滿自消,而詀語自止,此「通因塞用」法也。 |
人之十二經脈,與地之十二水相應,所以稱血為「經水」。女子屬陰而多血。脈為血之府。脈氣與月相應,所以女子每月都會有經水溢出,所以稱之為「月事」。這裏說的是婦人正值月經時,風邪犯人而發熱惡寒,此時尚未影響月事。病從外而來,可知需要先解表。等到七八日而熱除、身涼、脈遲時,則其病當愈。但卻反見胸脅苦滿,又不是結胸證,反而出現譫語,但又不是胃實,為甚麼呢?這是由於脈遲。脈遲表示病邪在臟,必然是正值月事,風寒外來,內熱乘機犯肝,而月經又未盡,經血必然結聚。此時應當針刺肝之募穴以瀉結聚之熱,胸脅滿自然消除,而譫語亦自然停止,這是「通因塞用」之治法。 |
|
婦人傷寒發熱,經水適來,晝則明瞭,暮則譫語,如見鬼狀,此為熱入血室。無犯胃氣及上下焦,必自愈。 |
|
|
前言中風,此言傷寒者,見婦人傷寒中風,皆有熱入血室証也。然此三條,皆因譫語而發,不重在熱入血室,更不重在傷寒中風。要知詀語多有不因于胃者,不可以詀語為胃實而犯其胃氣也。發熱不惡寒,是陽明病。申酉詀語,疑為胃實。若是經水適來,固知熱入血室矣。此經水未斷,與上條「血結」不同。是肝虛魂不安而妄見,本無實可瀉,固不得妄下以傷胃氣,亦不得刺之令汗,以傷上焦之陽。刺之出血,以傷下焦之陰也。俟其經盡,則詀語自除,而身熱自退矣,當以不治治之。 熱入血室,寒熱如瘧而不譫語者,入柴胡証。 |
前面說的是中風,這裏說的是傷寒,由此可見婦人傷寒或中風,都可以出現熱入血室證。但是這三條都是針對譫語而言,重點不在熱入血室,更不是重在傷寒中風。要知道有很多譫語不屬於胃實證,不可以認為譫語就是胃實證而用攻下法傷及胃氣。發熱不惡寒,是陽明病。申酉之時譫語,可以懷疑是胃實證。如果恰好月經來潮,可知這是熱入血室。此時月經未斷,與上條「血結」不同。這是因為肝虛,魂不安而出現幻覺,本來就沒有實證可以攻逐,當然亦不能誤用攻下而損傷胃氣,也不能以針刺使病人出汗而傷及上焦陽氣。針刺出血,則會傷及下焦之陰氣。等到病人月經結束,譫語自然就會消失,而身熱亦自然就消退了,應該採用不治之法來治療此病證。 熱入血室,若出現寒熱像瘧疾般,卻沒有譫語的話,應歸入柴胡湯證之治療。 |
|
○右論陽明譫語脉証。 |
○前面所論是陽明病譫語之脈證。 |
|
傷寒論註卷之四 南陽 張機 仲景原文 慈谿 柯琴 韻伯編註 崑山 馬中驊驤北較訂 |
|
|
太陰脈證 |
|
|
太陰之為病,腹滿而吐,食不下,自利益甚,時腹自痛。若下之,必胸下結鞕。 |
|
|
陽明三陽之裡,故提綱屬裡之陽証。太陰三陰之裡,故提綱皆裡之陰證。太陰之上,濕氣主之,腹痛吐利,從濕化也。脾為濕土,故傷於濕,脈先受之。然寒濕傷人,入於陰經,不能動藏,則還於府。府者,胃也。太陰脈布胃中,又發於胃,胃中寒濕,故食不內,而吐利交作也。太陰脈從足入腹,寒氣時上,故腹時自痛,法宜溫中散寒。若以腹滿為實而誤下,胃口受寒,故胸下結鞕。 |
陽明為三陽之裏,所以陽明病提綱證屬於裏之陽證。太陰為三陰之裏,所以太陰病提綱證都是裏之陰證。太陰之上,濕氣主之,所以腹痛、嘔吐、下利之證都是從濕而化。脾為濕土,所以被濕所傷,太陰之脈先受到傷害。但是寒濕傷人而入於陰經,如果不能干犯臟氣,就會回到其腑。腑,就是指胃。太陰之脈分佈於胃中,又從胃中發出,因為寒濕犯胃,所以不能食,而嘔吐、下利交替出現。太陰之脈從足進入腹中,寒氣不時上逆,所以腹部有時自然疼痛,治法宜溫中散寒。如果以為腹滿為實證而誤下,則胃口受寒,而有胸下結硬之變。 |
|
自利不渴者,屬太陰,以其藏有寒故也,當溫之,宜四逆輩。 傷寒四五日,腹中痛,若轉氣下趨少腹者,此欲自利也。 |
|
|
上條明自利之因,此條言自利之兆,四五日是太陰發病之期。 |
上條說明自利之原因,本條則說明自利之徵兆,四五日是太陰病發病之日期。 |
|
傷寒脈浮而緩,手足自溫者,繫在太陰。太陰當發身黃,若小便自利者,不能發黃。至七八日,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,必自止,以脾家實,腐穢當去故也。 |
|
|
前條是太陰寒濕,脈當沉細。此條是太陰濕熱,故脈浮緩。首揭「傷寒」,知有惡寒証。浮而緩,是桂枝脈。然不發熱而手足溫,是太陽傷寒,非太陽中風矣。然亦暗對「不發熱」言耳,非太陰傷寒,必手足溫也。夫病在三陽,尚有手足冷者,何況太陰?陶氏分太陰「手足溫」,少陰「手足寒」,厥陰「手足厥冷」,是大背太陰「四肢煩疼」,少陰「一身手足盡熱」之義。第可言「手足為諸陽之本」,尚自溫,不可謂「脾主四肢」,故當溫也。凡傷於寒則病熱,太陰為陰中之陰,陰寒相合,故不發熱。太陰主肌肉,寒濕傷於肌肉而不得越于皮膚,故身當發黃。若水道通調,則濕氣下輸膀胱,便不發黃矣。然寒濕之傷於表者,因小便而出。濕熱之蓄於內者,必從大便而出也。「發於陰者六日愈」,至七八日陽氣來復,因而暴煩下利,雖日十餘行,不須治之,以脾家積穢臭塞於中,盡自止矣。手足自溫,是表陽猶在。暴煩,是裡陽陡發。此陰中有陽,與前「藏寒」不同。能使小便利,則利自止。不須溫,亦不須下也。 |
前條屬於太陰寒濕,脈應當沉細。本條屬於太陰濕熱,所以脈浮緩。條文開首即冠以「傷寒」,則知當有惡寒。脈浮而緩,是桂枝湯證之脈。但不發熱卻手足溫,是太陽病傷寒證,而不是太陽病中風證。然而亦是暗中相對於「不發熱」而言,不是說太陰病之傷寒就一定會手足溫。病變在三陽,尚且有手足冷,何況太陰病呢?陶氏用太陰病則「手足溫」,少陰病則「手足寒」,厥陰病則「手足厥冷」作為區分,嚴重違背了太陰病則「四肢煩疼」,少陰病則「一身手足盡熱」之義。只可以說「手足為諸陽之本」,所以手足尚能自溫,而不可以說「脾主四肢」,所以應當手足溫。凡是傷寒病就會出現發熱,太陰是陰中之陰,陰與寒相合,所以不發熱。太陰主肌肉,寒濕傷於肌肉而不能外散於皮膚,所以身體應該發黃。如果水道通調,則濕氣可以下輸膀胱,便不會發黃。但是寒濕傷及於表,就會隨小便而排出。而濕熱蓄積在內,必然要從大便而出。「發於陰者六日愈」,到第七八日陽氣恢復,因而會會突然心煩而下利,雖然每日十幾次,但不需要治療,因為這是脾家之腐穢積塞於中,只要通過下利而被完全排除後下利就能自然停止。手足自溫,反映表陽仍在。而突然心煩,則反映裏陽突然恢復。這是陰中有陽,與前面之「臟寒」不同。能使小便通利,則下利自然停止。不需要用溫法,亦不需要用下法。 |
|
傷寒下利,日十餘行,脈反實者,死。 |
|
|
脾氣虛而邪氣盛,故脈反實也。 |
脾氣虛而邪氣盛,所以反而出現實脈。 |
|
太陰病,脈弱,其人續自便利。設當行大黃、芍藥者,宜減之,以其胃氣弱,易動故也。 |
|
|
太陰脈本弱,胃弱則脾病,此內因也。若因於外感,其脈或但浮,或浮緩,是陰病見陽脈矣。下利為太陰本証。自利因脾實者,腐穢盡則愈。自利因藏寒者,四逆輩溫之則愈。若自利因太陽誤下者,則腹滿時痛,當加芍藥。而大實痛者,當加大黃矣。此下後脈弱,胃氣亦弱矣。小其制而與之,動其「易動」,合乎「通因通用」之法。 |
太陰病之脈本應是弱脈,胃弱則脾病,這是內因。如果因為外感邪氣,或只是浮脈,或會脈浮緩,這是在陰病而見陽脈。下利屬於太陰病之本證。自利如果是因為脾氣充實所致,腐穢被排盡則愈。自利如果因為臟寒,則用四逆湯類方劑溫散寒邪則愈。如果自利是因為太陽誤下所致,就會出現腹滿而有時疼痛,應當加芍藥。如果出現腹部之大實痛,則應當加大黃。這是攻下之後脈弱,胃氣亦會弱。製定小方讓病人服用,使其「易動」之胃氣下行,則符合「通因通用」之法。 |
|
大黃瀉胃,是陽明血分下藥。芍藥瀉脾,是太陰氣分下藥。下利、腹痛,熱邪為患,宜芍藥下之。下利、腹痛為陰寒者,非芍藥所宜矣。仲景於此芍藥與大黃並提,勿草草看過。 |
大黃能瀉胃,是陽明血分之下藥。芍藥能瀉脾,是太陰氣分之下藥。下利、腹痛如果是熱邪所致,則宜用芍藥下之。如果下利、腹痛屬於陰寒所致,則不是芍藥所能治。仲景在這裏將芍藥與大黃並提,不要草草地看過。 |
|
惡寒,脈微而復利,亡血也,四逆加人參湯主之。 |
|
|
方註見四逆湯註中。 |
方註參見《四逆湯》之註文。 |
|
○右論太陰傷寒脈証。 |
○前面所論是太陰病之傷寒脈證。 |
|
太陰病,脈浮者,可發汗,宜桂枝湯。 |
|
|
太陰主裡,故提綱皆屬裡証。然太陰主開,不全主裡也。脈浮者,病在表,可發汗,太陰亦然也。尺寸俱浮者,太陰受病也。沉為在裡,當見腹痛、吐利等証。此浮為在表,當見四肢煩疼等証。裡有寒邪,當溫之,宜四逆輩。表有風熱,可發汗,宜桂枝湯。太陰脈沉者,因於寒。寒為陰邪,沉為陰脈。太陰有脈浮者,因乎風。風為陽邪,浮為陽脈也。謂「脈在三陰則俱沉,陰經不當發汗」者,非也。但浮脈,是麻黃脈。沉脈,不是桂枝証,而反用桂枝湯者,以太陰是裡之表証,桂枝是表之裡藥也。 |
太陰主裏,所以提綱證都屬於裏證。然而太陰之氣主開,不全都主於裏。脈浮者,病邪在表,可以發汗,太陰病亦是如此。尺寸之脈都浮,是太陰受邪。脈沉表示病邪在裏,應會出現腹痛、嘔吐、下利等證。而這裏脈浮表示病邪在表,則應當出現四肢煩疼之證。裏有寒邪,應該用溫法,宜用四逆湯等類方。表有風熱,可以發汗,宜用桂枝湯。太陰病脈沉者,是因為寒邪。寒邪是陰邪,脈沉為陰脈。太陰病出現脈浮,是因為風邪。風為陽邪,脈浮為陽脈。「三陰病之脈都應是沉脈,所以三陰病不應當發汗」之說,其實不是這樣的。只見浮脈,是麻黃湯證之脈。沉脈則不是桂枝湯證之脈,此處反而用桂枝湯,是因為太陰病屬於裏之表證,桂枝湯則是表之裏藥。 |
|
太陰中風,四肢煩疼,陽微陰濇而長者,為欲愈。 |
|
|
風為陽邪,四肢為諸陽之本。脾主四肢,陰氣衰少,則兩陽相搏,故煩疼。脈濇與長,不是並見。濇本病脈,濇而轉長,病始愈耳。風脈本浮,今而微,知風邪當去。濇則少氣少血,今而長則氣治,故愈。 |
風為陽邪,四肢為諸陽氣之本。脾主四肢,陰氣衰減時,就會出現陽邪與陽氣相搏,所以會煩疼。脈澀與脈長,不是一同出現。澀脈本來是病脈,由脈澀而轉變為脈長,表示疾病開始好轉。風邪之脈本浮,如今卻脈微,就知道風邪應當消散。脈澀表示少氣少血,如今出現脈長則氣血恢復正常,所以病愈。 |
|
四肢煩疼,是中風未愈。前証微濇而長,是中風將愈之脈,宜作兩截看。 |
四肢煩疼,是中風證尚未痊愈。前證脈微澀而長,是中風將愈之脈,應該分成二段來看。 |
|
太陽以惡風、惡寒別風寒,陽明以能食、不能食別風寒,太陰以四肢煩溫別風寒,是最宜著眼。少陽為半表半裡,又屬風藏,故傷寒、中風互称。少陰、厥陰,則但有欲愈脈,無未愈証,惜哉。 |
太陽病以惡風、惡寒來區分中風與傷寒,陽明病用能食、不能食來區分中風與中寒,太陰病則用四肢煩疼、四肢溫來區分中風與傷寒,這是最應該留心之處。少陽為半表半裏,又屬於風臟,所以將傷寒與中風互稱。而少陰病與厥陰病中,則只描述了將要痊愈之脈象,而沒有未愈之證,實在是可惜啊。 |
|
○右論太陰中風脈証。 |
○前面所論為太陰病之中風脈證。 |
|
太陰病,欲觧時,從亥至丑上。 |
|
|
《經》曰「夜半後而陰隆,為重陰」,又曰「合夜至雞鳴,天之陰,陰中之陰也」。脾為陰中之至陰,故主亥子丑時。 |
《內經》說「夜半之後陰氣隆盛,為重陰」,又「從黃昏至雞鳴之時,屬於天之陰,為陰中之陰」。脾為陰中之至陰,所以其氣主於亥、子、丑三個時辰。 |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