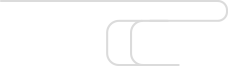
傷寒附翼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傷寒附翼卷之上 |
||
|
慈谿 柯琴 韻伯編 崑山 馬中驊驤北較 |
||
|
太陽方總論 |
||
|
太陽主表,故立方以發表為主,而發表中更兼治裏,故種種不同。麻黃湯於發表中降氣,桂枝湯於發表中滋陰,乾葛湯於發表中生津,大青龍湯與麻杏甘膏湯、麻翹赤豆湯於發表中清火,小青龍湯與五苓散於發表中利水。清火中復有輕重,利水中各有淺深也。若白虎之清火,十棗之利水,又解表後之證治。其陷胸、瀉心、抵當、調胃、四逆、真武等劑,又隨症救逆之法矣。大抵太陽之表,不離桂枝、麻黃二湯加減,以心為太陽之裏也。今將諸方詳論,表章仲景治法,令後人放膽用之,則「麻黃湯治傷寒而不治中風,桂枝湯治中風而不治傷寒」等說,其可少息乎? |
太陽之氣主表,因此創立方劑以發散表邪為主,而發表同時又兼治裏證,所以有各種不同方劑。麻黃湯於發表中降氣,桂枝湯於發表中滋陰,葛根湯於發表中生津,大青龍湯與麻杏甘膏湯、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於發表中清火,小青龍湯與五苓散於發表中利水。清火之中又有輕重,利水之中各有淺深。至於白虎湯之清火,十棗湯之利水,則屬於解表之後之證治。其它如陷胸湯、瀉心湯、抵當湯、調胃承氣湯、四逆湯、真武湯等,則是針對誤治而隨證治之之救逆法。總的來說,太陽病解表之劑離不開桂枝湯和麻黃湯二方之加減,這是因為心為太陽之裏。現在詳細討論各個方劑,將仲景之治法説清楚,使後人放心大膽地使用,這樣,「麻黃湯治傷寒而不治中風,桂枝湯治中風而不治傷寒」等說法,是否就可以停息了呢?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湯 桂枝 芍藥 甘草 生姜 大棗 |
||
|
此為仲景羣方之魁,乃滋陰和陽,調和營衛,解肌發汗之總方也。凡頭痛,發熱,惡風,惡寒,其脈浮而弱,汗自出者,不拘何經,不論中風、傷寒、雜病,咸得用此發汗。若妄汗妄下而表不解者,仍當用此解肌。如所云「頭痛、發熱、惡寒、惡風、鼻鳴、乾嘔」等病,但見一症即是,不必悉具,惟以脉弱自汗為主耳。桂枝赤色,通心溫經,能扶陽散寒,甘能益氣生血,辛能解散外邪,內輔君主,發心液而為汗。故麻黃、乾葛、青龍輩,凡發汗禦寒者咸用之。惟桂枝湯不可用麻黃,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。本方皆辛甘發散,惟芍藥微苦微寒,能益陰斂血,內和營氣。先輩之「無汗不得用桂枝湯」者,以芍藥能止汗也。芍藥之功,本在止煩,煩止汗亦止,故「反煩」、「更煩」,與「心悸而煩」者咸賴之。若倍加芍藥,即建中之劑,非復發汗之劑矣。是方也,用桂枝發汗,即用芍藥止汗。生姜之辛,佐桂以解肌;大棗之甘,佐芍以和裏。桂芍之相須,姜棗之相得,陰陽表裏,並行而不悖,是剛柔相濟以為和也。甘草甘平,有安內攘外之功,用以調和氣血者,即以調和表裏,且以調和諸藥矣。而精義尤在「啜稀熱粥以助藥力」。蓋穀氣內充,外邪勿復入,熱粥以繼藥之後,則餘邪勿復留,複方之妙用又如此。故用之發汗,自不至於亡陽;用之止汗,自不至於貽患。今人凡遇發熱,不論虛實,悉忌穀味。刊桂枝方者,俱削此法,是豈知仲景之心法乎?要知此方專治表虛,但能解肌以發營中之汗,不能開皮毛之竅,以出衛分之邪。故汗不出者,是麻黃症;脈浮緊者,是麻黃脉,即不得與桂枝湯矣。然初起無汗,當用麻黃發汗。如汗後復煩,即脉浮數者,不得再與麻黃而更用桂枝。如汗後不解,與下後脉仍浮,氣上冲,或下利止而身痛不休者,皆當用此解外。蓋此時表雖不解,腠理已疏,邪不在皮毛而在肌肉。故脉證雖同麻黃,而主治當屬桂枝也。粗工妄謂桂枝湯專治中風一證,印定後人耳目,而所稱「中風」者,又與此方不合,故置之不用。愚常以此湯治自汗、盜汗、虛瘧、虛痢,隨手而愈。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,與後人分門證類,使無下手處者,可同年而語耶? |
這是仲景眾方之首,是滋陰和陽、調和營衛、解肌發汗之總方。但凡頭痛,發熱,惡風,惡寒,脈浮而弱,汗自出者,不用拘泥於是何經之病,不論是中風、傷寒,還是雜病,都可以用此方發汗。如果誤用發汗、攻下後而表證不解者,仍然應該使用此方解肌。如條文所說「頭痛、發熱、惡寒、惡風、鼻鳴、乾嘔」等證,只要出現其中一種證候即可用桂枝湯,而不必諸證都具備,主要以脈弱而自汗為主。桂枝赤色,溫通心經,能扶陽散寒,味甘能益氣生血,味辛能解散外邪,內輔君主,使心液化而為汗。因此,麻黃湯、葛根湯、青龍湯等,凡是用於發汗祛寒邪之方劑都會用桂枝。只是桂枝湯不可以用麻黃,而麻黃湯不可以沒有桂枝。此方之藥都具辛甘發散之用,只有芍藥微苦微寒,能益陰斂血,內和營氣。前輩所說「無汗不得用桂枝湯」,就是因為芍藥能止汗。芍藥之功原本在於止煩,煩止則汗亦止,因此,「反煩」、「更煩」,與「心悸而煩」者都要用芍藥。如果加倍用芍藥,就變成小建中湯,而不再是發汗之方。本方用桂枝發汗,即同時用芍藥止汗。生薑味辛,輔助桂枝以解肌;大棗味甘,輔助芍藥以和裏。桂枝和芍藥相須為用,生薑和大棗相得益彰,則陰陽表裏同時兼顧而不衝突,通過剛柔相濟而達至和諧。甘草甘平,有安內攘外之功,用於調和氣血者,就是為了調和表裏,而且還用來調和諸藥。本方精妙之處在於「啜稀熱粥以助藥力」。因為穀氣內充,則外邪不再進入,服藥之後食熱粥,則餘邪不會留存,複方又有如此之妙用。因此,用此方來發汗,自然不會引致亡陽;用此方來止汗,亦自然不會帶來不良後果。如今醫家在遇到發熱時,無論虛實,都避食水穀。書中列出桂枝湯時,都刪去了啜熱稀粥之法,這難道可以說是知道仲景之心法嗎?關鍵要知道此方專治表虛,只能解肌以宣發營中之汗,而不能打開皮毛之孔竅以宣發衛分之邪。因此,汗不出者就屬於麻黃湯證,脈浮緊者就是麻黃湯之脈,就不可服桂枝湯。然而,初起無汗時,應該用麻黃湯發汗。如果發汗後又出現心煩,即使脈浮數者,亦不能再使用麻黃湯,而要改用桂枝湯。如果發汗後表證不解,或誤下後脈仍浮,氣上衝,或下利止而身體疼痛不止,都應該用桂枝湯來解表。因為此時表證雖然未解,但腠理已經疏鬆,邪氣不在皮毛而在肌肉之中。因此,雖然脈證與麻黃湯相似,但主治之方當屬於桂枝湯。一般指醫家誤認為桂枝湯專治中風證,對後世影響很大,而所稱之「中風」證,又與此方所主治不同,所以常使此方閒置而不用。我經常用此方來治療自汗、盜汗、虛瘧、虛痢,隨手而愈。由此而知仲景方可以通治百病,這與後人將病證分門別類,使人無法有效應用經方,難道可以相提並論嗎?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麻黃湯 麻黃 桂枝 杏仁 甘草 |
||
|
治風寒在表,頭痛項強,發熱,身痛,腰痛,骨節煩疼,惡風,惡寒,無汗,胸滿而喘,其脉浮緊、浮數者,此為開表逐邪發汗之峻劑也。古人用藥用「法象」之義,麻黃中空外直,宛如毛竅骨節,故能去骨節之風寒,從毛竅而出,為衛分發散風寒之品。桂枝之條縱橫,宛如經脉系絡,能入心化液,通經絡而出汗,為營分散解風寒之品。杏仁為心果,溫能助心散寒,苦能清肺下氣,為上焦逐邪定喘之品。甘草甘平,外拒風寒,內和氣血,為中宮安內攘外之品。此湯入胃,行氣於玄府,輸精於皮毛,斯毛脉合精而溱溱汗出。在表之邪,其盡去而不留,痛止喘平,寒熱頓解,不煩啜粥而藉汗於穀也。其不用薑、棗者,以生薑之性,橫散解肌,礙麻黃之上升;大棗之性,滯泥於膈,礙杏仁之速降。此欲急於直達,稍緩則不迅,橫散則不峻矣。若脉浮弱,汗自出者,或尺脉微遲者,是桂枝所主,非此方所宜。蓋此乃純陽之劑,過於發散,如單刀直入之將,投之恰當,一戰成功,不當則不戢而召禍。故用之發表,可一而不可再。如汗後不解,便當以桂枝湯代之。若汗出不透,邪氣留連於皮毛骨肉之間,又有麻桂合半與桂枝二麻黃一之妙用。若陽盛於內而無汗者,又有麻黃杏仁石膏連翹赤小豆等劑。此皆仲景心法也。予治冷風哮與風寒濕三氣成痺等證,用此輒效,非傷寒一證可拘也。 |
用於治療風寒在表,頭痛項強,發熱,身痛,腰痛,關節煩疼,惡風,惡寒、無汗,胸滿而喘,脈浮緊或浮數,這是發表逐邪而發汗之峻劑。古代醫家是依據「法象」來用藥,麻黃中空外直,就像毛孔和關節,因此能消除關節之風寒,使之從毛孔而出,用作發散衛分風寒邪氣之藥。桂枝之條紋縱橫,就像經脈系統,可以入心化液,疏通經絡而令汗出,用作散解營分風寒之藥。杏仁屬心果,性溫能助心氣以散寒,味苦能清肺以降氣,用作上焦逐邪以定喘之藥。甘草之性甘平,可以外禦風寒,在內和氣血,用作中宮安內攘外之藥。此湯入胃後,能行氣於玄府,輸精於皮毛,這樣皮毛和經脈之精氣彙聚一起而使汗水外出。在表之邪從透過皮毛而盡散,疼痛止而喘息平,惡寒發熱立即解除,不需要透過啜粥而借水穀之氣以發汗。方劑中之所以不用生薑和大棗,是因為生薑之性能橫散解肌,阻礙了麻黃之上升;而大棗之性黏滯於胸膈,阻礙了杏仁快速降氣之用。此方之特點在於能迅速直達病位,稍有延緩則不迅速,橫散則使效果減弱。如果脈浮弱而汗自出者,或者尺脈微遲者,都屬於桂枝湯所治,不適合用麻黃湯。因為此方為純陽之方,過於發散,猶如單刀直入之將軍,使用得當就能一戰而成功,使用不當則不能停止而招致禍害。因此,用麻黃湯發表,可一而不可二。如果發汗後病證不解,就應該使用桂枝湯來代替。如果汗出不暢,邪氣停留在皮膚骨肉之間,則又有麻黃桂枝各半湯與桂枝二麻黃一湯之妙用。若陽邪內盛而無汗,又有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、麻黃連翹赤小豆湯等方。這些都是仲景之心法。我用此方治療冷風哮喘和風寒濕三氣引發之痹證等疾病,都非常有效,並不僅僅局限於傷寒一證。 |
|
|
按:麻桂二方,治傷寒中風者,遇當用而不敢用,註疏傷寒家於不當用者,妄言其當用。如太陽衄血證,「宜桂枝湯句」,語意在「當須發汗」下;「麻黃主之」句,在「當發其汗」下。二句皆於結句補出,是倒序法也。仲景於論證時,細明其所以然,未及於方故耳。夫桂枝乃行血之品,仲景用桂枝發汗,不是用桂枝止衄。是用在未衄時,非用在已衄後。且「奪血者無汗」,此理甚明。麻黃乃上升之品,夫既云「衄乃解」,又云「自衄者愈」,若復用升提之藥,衄流不止可必矣。且「衄家不可發汗」,此禁甚明矣。又如「小青龍主之」句,語意在「服湯已」上,豈有「寒去欲解」,反用燥熱之劑重亡津液,令渴不解乎?且云「服藥已」,「服藥已」者,是何藥何湯耶?觀仲景於所服藥不合法者,必明斥之。如所云「服瀉心湯,復以他藥下之,利不止」,又云「知醫以他藥下之,非其治也」。粗工不知倒序等法,又溺於「風寒」二字,而曰「是雖熱甚,邪由在經,以麻黃治衄,是發散經中邪氣耳」。請問邪氣,寒乎?熱乎?若寒邪則血凝不流,焉得有衄?若熱邪則清降不遑,而敢升發耶?且云「點滴不成流者,必用服藥」。若成流不止,將何法以善其後乎?此誤天下蒼生之最盛者,余因表而出之。 |
按:麻黃湯和桂枝湯二方是用來治療傷寒、中風,遇到應該使用之病證時卻不敢用,而注解《傷寒論》之醫家對於不應當使用此兩方之病證時,卻妄言是可以用的。例如,對於太陽病中衄血證,「宜桂枝湯」一句,語意是在「當須發汗」之後;「麻黃湯主之」一句,應當在「當發其汗」之後。這兩句話都是在結尾處補出來,是寫作技巧上之倒序法。仲景在論述病證時詳細說明了其原理,只是沒有涉及到所用之方劑。桂枝為行血之品,仲景是用桂枝湯發汗,而不是用來止衄。是用在衄血沒有發生之前,而不用在衄血發生之後。況且「奪血者無汗」,其道理非常明確。麻黃則屬於上升之品,既然說「衄乃解」,又說「自衄者愈」,如果再用升提之藥,衄血必然不止。況且「衄家不可發汗」,這項治療禁忌非常明確。又譬如「小青龍湯主之」一句,語意是在「服湯已」之前,怎會有「寒去欲解」時卻反而用燥熱之劑更加傷亡陰液,而使口渴不解?而且說「服藥已」,所謂「服藥已」到底指的是什麼藥、什麼方呢?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仲景對於不合理使用藥物的情況,必定會明確加以指責。例如所說的「服瀉心湯,復以他藥下之,利不止」,以及「知醫以他藥下之,非其治也」。粗疏之醫不知道倒序等文法,又糾結於「風寒」這兩個字,而說「這裏雖然發熱嚴重,但邪氣仍在經絡,用麻黃湯治衄,只是發散經絡中之邪氣」。請問:所謂邪氣是寒邪?還是熱邪的?如果是寒邪,則是血液凝固不流,怎麼會有衄血?如果是熱邪,用清降都怕來不及,怎麼敢用提升發散之藥呢?而且還說「衄血點滴而不成流者,必須使用此方」。如果血流不止,又該用何種方法來善後處理呢?這些說法最容易傷害天下之蒼生,我因此要將其清楚說明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葛根湯 葛根 麻黃 桂枝 白芍 甘草 姜棗 |
||
|
治頭項強痛,背亦強,牽引??然,脉浮,無汗,惡寒,兼治風寒在表而自利者,此開表逐邪之輕劑也。其證身不疼,腰不痛,骨節不痛,是骨不受寒矣。頭項強痛,下連於背,牽引不寧,是筋傷於風矣。不喘,不煩躁,不乾嘔,是無內症。無汗而惡風,病只在表。若表病而兼下利,是表實裏虛矣。比麻黃、青龍之劑較輕,然??更甚於項強,而無汗不失為表實。脉浮不緊數,是中於鼓動之陽風,故以桂枝湯為主而加麻、葛以攻其表實也。葛根味甘氣涼,能起陰氣而生津液,滋筋脉而舒其牽引,故以為君。麻黃、生薑能開玄府腠理之閉塞,祛風而出汗,故以為臣。寒熱俱輕,故少佐桂、芍,同甘、棗以和裏。此於麻、桂二方之間,衡其輕重,而為調和表裏之劑也。故用之以治表實,而外邪自解,不必治裏虛,而下利自瘳,與大青龍治表裏俱實者異矣。要知葛根秉性輕清,賦體厚重,輕可去實,重可鎮動,厚可固裏,一物而三美備。然惟表實裏虛者宜之,胃家實者,非所宜也,故仲景於陽明經中不用葛根。東垣用藥分經,不列於太陽而列於陽明。易老云「未入陽明者不可服」,皆未知此義。喻氏謂「仲景不用於陽明,恐亡津液」,與《本草》「生津」之說左。又謂「能開肌肉,」又與仲景治汗出惡風桂枝湯中加葛根者左矣。蓋桂枝、葛根俱是解肌和裏之劑,故有汗、無汗,下利、不下利,皆可用,與麻黃專於治表者不同。麻黃、葛根俱有沫,沫者濁氣也。故仲景皆以水煮去其沫,而後入諸藥,此取其「清陽發腠理」之義。桂枝湯啜稀粥者,因無麻黃之開,而有芍藥之斂,恐邪有不盡,故假穀氣以逐之,此「汗生於穀」也。 |
治頭項強痛,背亦強痛,項背相互牽引??然,脈浮,無汗,惡寒,同時能兼治風寒在表而自下利者,這是開表逐邪之輕劑。其證沒有身疼、腰痛、骨節疼痛,說明骨節沒有受寒。頭項強痛,下連於背部,拉扯不安,說明是筋脈傷於風邪。不喘、不煩躁、不乾嘔,表示沒有裏證。無汗而惡風,病位只在表。如果表病而兼下利,是表實裏虛。相比麻黃湯、青龍湯之發散則較輕,然而項背??則比項背強痛更嚴重,無汗則不失為表實證。脈浮而不緊數,這是中於鼓動之陽風,因此本方以桂枝湯為主,加麻黃、葛根以攻其表實。葛根味甘氣涼,能升提陰氣而生津液,滋養筋脈並舒緩其拉扯感,因此以葛根為君藥。麻黃、生薑能疏通玄府腠理之閉塞,祛除風邪並使出汗,因此用作臣藥。發熱惡寒輕微,因此用少量桂枝、芍藥為輔佐,與甘草、大棗一同調和裏氣。此方是在麻黃湯、桂枝湯二方之間,衡量其輕重作為調和表裏之劑。因此用來治療表實證,則外邪自然解除,不必治療裏虛,而下利自然能愈,與大青龍湯用來治療表裏俱實是不同的。關鍵要知道葛根稟性輕清而質地厚重,輕可去實,重可鎮動,厚可固裏,一種藥物具備三種良好特性。然而只適用於表實裏虛,胃家實則不適用。因此仲景在陽明經病中不用葛根。李東垣用藥時按經絡分類,不列葛根於太陽經而列於陽明經。張元素說「邪氣未進入陽明者不可服葛根」,二位醫家未能明仲景用葛根之意。喻嘉言說「仲景不在陽明病中用葛根,是恐其傷亡津液」,這與《神農本草經》「生津」之說不相符。又說葛根「能開肌肉」,又與仲景治療汗出惡風時用桂枝湯中加葛根之法不相符。因為桂枝湯、葛根湯都是解肌和裏之劑,所以有汗、無汗,下利、不下利者,都可以使用,與麻黃湯專門用於治表不同。煮麻黃和葛根時都有泡沫,泡沫是渾濁之氣。因此仲景都用水先煮去其泡沫,然後再放入其他藥物,這種方法是取「清陽發腠理」之意。服桂枝湯後要啜稀粥,是因為沒有麻黃之開發,而有芍藥之收斂,恐怕邪氣不能被完全排除,因此借助穀氣來驅逐邪氣,其原理是「汗生於穀」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大青龍湯 麻黃 桂枝 石膏 杏仁 甘草 薑棗 |
||
|
太陽中風,脉浮緊,頭痛,發熱,惡寒,身疼,不汗出而煩躁,此麻黃證之劇者,故加味以治之也。諸證全是麻黃,有喘與煩躁之別。喘者是寒鬱其氣,升降不得自如,故多用杏仁之苦以降氣。煩躁是熱傷其氣,無津不能作汗,故特加石膏之甘以生津。然其性沉而大寒,恐內熱頓除而表寒不解,變為寒中而挾熱下利,是引賊破家矣。故必倍麻黃以發表,又倍甘草以和中,更用薑棗以調營衛。一汗而表裏雙解,風熱兩除,此大青龍清內攘外之功,所以佐麻、桂二方之不及也。夫青龍以發汗命名,其方分大小,在麻黃之多少,而不關石膏,觀小青龍之不用可知。石膏不能驅在表之風寒,但能清中宮之燔灼,觀白虎之多用可知。世不知石膏為煩躁用,妄為發汗用,「十劑」之「輕可去實」,豈至堅至重之質而能發汗哉?「汗多亡陽」者,過在麻黃耳。少陰亦有發熱,惡寒,煩躁之症,與大青龍同,但脉不浮、頭不痛為異。若脉浮弱,汗自出者,是桂枝證。二證妄與石膏,則胃氣不至於四肢而手足厥冷。妄用麻黃,則衛陽不周於身而筋惕肉瞤。此仲景所深戒也。要知少陰見陽證而用麻黃,必固以附子。太、少異位,陰陽殊途,故寒溫有別。桂枝證之煩,因於木旺,故用微苦微寒之劑以升降之。大青龍之兼躁,因於風動,故用至陰至重之品以鎮墜之。有汗、無汗,虛實不同,輕重有差也。必細審其所不用,然後不失其所當用耳。 |
太陽中風,脈浮緊,頭痛,發熱,惡寒,身疼,不汗出而煩躁,這是麻黃湯證之嚴重表現,因此需要增加藥物來治療。所有證候都是麻黃湯證,只是喘和煩躁是不同的。喘是因為寒邪鬱閉氣機,升降失常,所以經常用杏仁之苦以降氣。煩躁是因為熱邪傷氣,沒有津液而無法使其汗出,所以特別添加石膏甘味生津。然而,石膏質重且大寒,恐怕內熱突然去除而表寒不解,反而變成寒中而挾熱下利,這樣等於引狼入室。因此,必須加倍用麻黃以發表,再倍用甘草以和中,更用生薑、大棗來調整營衛。一旦汗出則表裏雙解,風熱兩除,這是大青龍湯清內攘外之功效,所以可以補充麻黃湯和桂枝湯二方之不及。大青龍湯以發汗來命名,其方大小之分,取決於麻黃之用量,而與石膏無關,從小青龍湯中不用石膏就可知。石膏無法驅散在表之風寒,只能清除中焦之熱邪,從白虎湯中重用石膏就可知。世人不知石膏用於煩躁,卻錯誤地將其用於發汗,「十劑」中所謂「輕可去實」,怎麼會有質地堅固重實之藥可以用來發汗?服大青龍湯後「汗多亡陽」者,其過在於麻黃。少陰病亦有發熱,惡寒,煩躁之證,與大青龍湯證相似,只是以脈不浮、頭不痛為不同之處。如果脈浮弱,汗自出者,那就是桂枝湯證。以上二證如果誤用石膏,則胃氣無法到達四肢而導致手足厥冷。濫用麻黃,則衛陽無法周流於全身而引發筋惕肉瞤。這是仲景特別提出之治療禁忌。關鍵要知道少陰病見陽證而用麻黃,一定要用附子以固護陽氣。太陽和少陰異位,陰陽之途不同,所以發病時寒溫有別。桂枝湯證之煩躁是由於木氣過旺,因此用微苦微寒之劑以升降氣機;大青龍湯證之兼見煩躁是由於風之動,因此用至陰至重之石膏來重鎮下降。有汗、無汗,虛實不同,輕重有異。必須仔細審查其為什麼不用,然後才能知道什麼時候需要用。 |
|
|
按:許叔微云:「桂枝治中風,麻黃治傷寒,大青龍治中風見寒脉、傷寒見風脉,三者如鼎立。」此方氏三大綱所由來。而大青龍之證治,自此不明於世矣。不知仲景治表,只在麻、桂二法。麻黃治表實,桂枝治表虛,方治在虛實上分,不在風寒上分也。蓋風寒二證,俱有虛實,俱有淺深,俱有營衛,大法又在虛實上分淺深,並不在風寒上分營衛也。夫有汗為表虛,立桂枝湯治有汗之風寒,而更有加桂、去桂,加芍、去芍,及加附子、人參、厚朴、杏仁、茯苓、白朮、大黃、龍骨、牡蠣等劑,皆是桂枝湯之變局。因表虛中更有內虛內實淺深之不同,故加減法亦種種不一耳。以無汗為表實,而立麻黃湯治無汗之風寒。然表實中亦有夾寒、夾暑,內寒、內熱之不同,故以麻黃為主而加減者,若葛根湯,大小青龍、麻黃附子細辛甘草、麻黃杏仁甘草石膏、麻黃連翹赤豆等劑,皆麻黃湯之變局,因表實中亦各有內外寒熱淺深之殊也。葛根湯因肌肉津液不足而加芍藥、葛根,大青龍因內熱煩躁而加石膏,小青龍以乾嘔而咳而加半夏、細辛、乾薑,麻黃附子細辛甘草二方,以脉沉而加附子,若連翹、赤豆、梓皮,濕熱發黃而加。諸劑皆因表實,從麻黃湯加減,何得獨推大青龍為鼎立耶?何但知有風寒,而不知有風熱?但知有中風見寒、傷寒見風之症,而不知小青龍之治風寒,大青龍之治風熱,麻杏甘膏之治溫熱,麻翹豆湯之治濕熱,表實中更有如是之別耶?且前輩之鑿分風寒者,拘於脉耳。不知仲景之論脉甚活而不拘,如大青龍之條,有中風而脉浮緊、傷寒而脉浮緩,是互文見意處。言中風脉緩,然亦有脉浮緊者;傷寒脉緊,然亦有脉浮緩者。蓋中風、傷寒,各有淺深,或因人之強弱而異,地之高下而異,時之乖和而異。證既不可拘,脉即不可執。如「陽明中風而脉浮緊」,「太陰傷寒而脉浮緩」,不可謂脉緊必傷寒,脉緩必中風矣。按《內經》「脉滑曰風」,則風脉原無定象;又「盛而緊曰脹」,則緊脉不專屬傷寒;又「緩而滑為熱中」,則緩脉亦不專指中風矣。且陽明中風,有脉浮而緊者,又有脉弦浮大者。必欲以太陽之脉緩自汗、脉緊無汗定分風寒,割裂營衛,他經皆有中風,皆不言及何耶?要知脉緊固為有力,脉浮緩亦不是浮弱,即《內經》「緩而滑為熱中」之脉也。蓋仲景憑脉辨症,只審虛實。故不論中風、傷寒脉之緩緊,但於指下有力者為實,脉弱無力者為虛;不汗出而煩躁者為實,汗出多而煩躁者為虛;證在太陽而煩躁者為實,症在少陰而煩躁者為虛。實者可服大青龍,虛者便不可服,此最易知也。凡先煩不躁而脉浮者,必有汗而自解;煩躁而脉浮緊者,必無汗而不解。大青龍湯為風寒在表而兼熱中者設,不是為有表無裏而設。故中風無汗煩躁者可用,傷寒而無汗煩躁者亦可用。蓋風寒本是一氣,故湯劑可以互投。論中有「中風」「傷寒」互稱者,如大青龍是也;有「中風」「傷寒」兼提者,如小柴胡是也。仲景但細辨脉症而施治,何嘗拘拘於中風、傷寒之別其名乎?如既立麻黃湯治寒,桂枝湯治風,而中風見寒、傷寒見風者,曷不用桂枝麻黃合半湯,而更用大青龍為主治耶?且既有「中風」惡風不惡寒,「傷寒」惡寒不惡風之說,曷不用大青龍之惡寒主傷寒,麻黃證之惡風主中風,桂枝症之惡風復惡寒,主中風見寒、傷寒見風耶?方氏因三綱之分,而有「風寒多少」之陋見。喻氏又因大青龍之名,而為龍背、龍腹、龍尾之奇說。又謂「縱橫」者,龍之所以飛期門及大青龍之位。「青龍」之說愈工,而青龍之法愈湮,此所謂「好龍」而不識真龍者也。大青龍之點睛,在「無汗煩躁」、「無少陰證」二句。合觀之,知本方本為太陽煩躁而設。仲景恐人誤用青龍,不特為「脉弱汗出」者禁,而喫緊尤在「少陰」。蓋少陰亦有發熱、惡寒、身疼、無汗而煩躁之症,此陰極似陽,寒極反見熱化也。誤用則厥逆、筋惕肉瞤所必至,全在此處著眼,故必審其非少陰症,而為太陽煩躁無疑。太陽煩躁為陽盛,非大青龍不解。故不特脉浮緊之中風可用,即浮緩而不微弱之傷寒,亦可用也。不特身疼身重者可用,即身不疼與身重而乍有輕時者,亦可用也。蓋胃脘之陽,內鬱胸中而煩,外擾四肢而躁,第用麻黃發汗於外,不加石膏泄熱於內,煩躁不解,陽盛而死矣。諸家不審煩躁之理,以致「少陰」句無所著落,妄謂「大青龍為風寒兩傷營衛而設」,不知其為兩解表裏而設。請問石膏之設,為治風歟?治寒歟?營分藥歟?衛分藥歟?只為熱傷中氣,用之治內熱耳。
|
按:許叔微說:「桂枝湯治療中風證,麻黃湯治療傷寒證,大青龍湯治療中風證而見寒脈、傷寒證而見風脈,此三者如鼎立一般。」這是方有執將太陽病分為三大綱之源頭。自此以後,大青龍湯之證治就不再為世人所明。他們不知道仲景治療表證,只在於麻黃湯和桂枝湯二種方法,麻黃湯治療表實證,桂枝湯治療表虛證,方劑之治法只在於虛證和實證之不同,而不是在於風邪或寒邪之區別。因為中風、傷寒都有虛證和實證,各有淺深之分,都涉及到營衛,大法又在虛實上分其淺深,並不是基於風寒來區分營分或衛分。有汗出為表虛證,所以立桂枝湯來治療有汗之風寒,而又有桂枝加桂湯、桂枝去桂湯、桂枝加芍藥湯、桂枝去芍藥湯,以及桂枝加附子湯、及桂枝湯中加入人參、厚朴、杏仁、茯苓、白朮、大黃、龍骨、牡蠣等方,都是桂枝湯之變方。由於表虛證中還有裏虛、裏實之不同淺深,因此加減之方亦有種種不同。以無汗為表實證,所以立麻黃湯來治療無汗之風寒。表實證中亦有夾寒、夾暑,裏寒、裏熱之不同,因此以麻黃湯為主方進行加減,例如葛根湯、大小青龍湯、麻黃附子細辛湯、麻黃附子甘草湯、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、麻黃連翹赤小豆湯等方,都是麻黃湯之變方,因為表實中亦有內外寒熱淺深之不同。葛根湯是因為肌肉津液不足而加芍藥、葛根,大青龍湯是因內熱煩躁而加石膏,小青龍湯是因乾嘔咳嗽而加半夏、細辛、乾薑,麻黃附子細辛湯、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是因為脈沉而加附子,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是因濕熱發黃加連翹、赤小豆、梓白皮。這些方劑都是基於表實證而從麻黃湯進行加減,怎麼能單獨推出大青龍湯而為三者鼎立呢?為什麼只知道有風寒,卻不知道有風熱?只知道中風見寒、傷寒見風之證,卻不知道小青龍湯之治風寒,大青龍湯之治風熱,麻杏甘膏湯之治溫熱,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之治濕熱,表實證中還有如此多之不同呢?況且前輩們堅持將風與寒分開,只是拘泥於脈象。他們不瞭解仲景論脈非常靈活而不拘泥,就如大青龍湯條文,有中風證而脈浮緊,傷寒證而脈浮緩,這只是互文見意。說中風證脈緩,但亦有脈浮緊者;傷寒證脈緊,但亦有脈浮緩者。因為中風證和傷寒證各有輕重,或因人稟賦之強弱而異,或因地勢之高低而異,或因氣候之差異而異。證候既然不能固定,脈象亦不能一概而論。比如「陽明中風而脈浮緊」,「太陰傷寒而脈浮緩」,不能說脈緊一定是傷寒證,脈緩一定是中風證。按照《內經》「滑脈為風」之說法,則風脈本來就沒有固定之象;又說「盛而緊曰脹」,則緊脈並不專屬於傷寒證;又說「緩而滑為熱中」,則緩脈亦不專指中風證。而且陽明中風,有脈浮而緊者,亦有脈弦浮大者。如果一定要以太陽病之脈緩自汗、脈緊無汗來定風寒而割裂營衛,那麼其他經病中都有中風證,為什麼卻又沒有提及於此呢?要知道脈緊固然是有力,但脈浮緩亦不是浮弱,就像《內經》中所說的「緩而滑為熱中」之脈一樣。因為仲景憑脈辨證,只審虛實。所以無論中風或傷寒脈之緩或緊,只要在指下有力就是實,脈虛弱無力就是虛;不出汗而煩躁是實,汗出多而煩躁是虛;證候在太陽病而煩躁是實,證候在少陰病而煩躁是虛。實證可以用大青龍湯,虛證就不可用,這是最容易明確的。凡是先煩不躁而脈浮者,必然會有汗而自解;煩躁而脈浮緊者,必然無汗而不解。大青龍湯是為了風寒在表兼有熱中者而設,不是為了只有表證而沒有裏證者而設。所以中風無汗而煩躁者可用,傷寒無汗而煩躁者亦可用。因為風寒本來就同屬一氣,所以方藥可以相互使用。《傷寒論》中有「中風」「傷寒」可以相互稱謂者,如大青龍湯所治;有「中風」「傷寒」分別提及者,如小柴胡湯所治。仲景只是認真辨別脈證而加以論治,哪裏會受中風或傷寒之名所拘泥呢?譬如既然已經確立麻黃湯治療傷寒,桂枝湯治療中風,那麼對於中風見寒證、傷寒見風證者,為何不使用桂枝麻黃各半湯,而要換以大青龍湯為主治呢?而且既然有「中風」惡風而不惡寒,「傷寒」惡寒而不惡風之說,為何不用大青龍湯證之惡寒而主治「傷寒」,麻黃湯證之惡風而主治「中風」,桂枝湯證既有惡風,又有惡寒,則用其主治「中風」見寒證,「傷寒」見風證呢?方有執因為有「三綱」之分,所以就有有了「風寒多少」這樣狹隘之見解。喻嘉言又因大青龍湯之名,提出了龍背、龍腹、龍尾之奇說。又提出「縱橫」之說,認為龍能飛期門以及大青龍之位置。「青龍」之說越精妙,大青龍湯之應用就越模糊,這就是所謂「葉公好龍」但卻不能認識真龍。大青龍湯證點睛之筆在於「無汗煩躁」、「無少陰證」二句。綜合而言,就知道此方為治療太陽病煩躁而設。仲景擔心醫者誤用大青龍湯,不僅提出「脈弱汗出」之禁忌,而最緊要的是在於「少陰證」。因為少陰病亦有發熱、惡寒、身疼、無汗而煩躁之證候,這是陰極似陽,寒極反而熱化。如果誤用大青龍湯,則必然導致厥逆、筋惕肉瞤,重點就在於這一點,所以必須審查其不是少陰病證,而毫無疑問是屬於太陽病之煩躁。太陽病之煩躁屬於陽盛,非大青龍湯不能解除。所以不只是脈浮緊之中風證可用大青龍湯,即使是是脈浮緩而不微弱之傷寒證亦可用。不僅身疼而身重者可用,即使是身不疼,但重而乍有輕時者亦可用。因為胃脘之陽內鬱於胸中而煩躁,外擾四肢而躁動,只用麻黃發汗於外,而不加石膏泄熱於內,煩躁不解,則陽盛而死。諸家因為不能理解煩躁之理,導致「少陰」之文無處著落,妄謂「大青龍湯是為風寒兩傷營衛而設」,而不知道此方是為兩種解表裏而設。請問:本方用石膏,是為了治療風嗎?還是治療寒嗎?是治療營分嗎?還是治療衛分嗎?其實只是為了熱傷中氣,用於治療內熱而已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小青龍湯 麻黃 桂枝 白芍 甘草 乾薑 細辛 半夏 五味 |
||
|
傷寒表不解,心下有水氣,乾嘔發熱而渴,或利、或噎、或小便不利少腹滿、或喘者,用此發汗利水。夫陽之汗,以天地之雨名之。水氣入心則為汗,一汗而外邪頓解矣。此因心氣不足,汗出不徹,故寒熱不解而心下有水氣。其咳是水氣射肺之徵,乾嘔知水氣未入於胃也。心下乃胞絡相火所居之地,水火相射,其病不可擬摹。如水氣下而不上,則或渴或利;上而不下,則或噎或喘;留於腸胃,則小便不利而少腹應滿耳。惟發熱、乾嘔而渴,是本方之當證。此於桂枝湯去大棗之泥,加麻黃以開玄府,細辛逐水氣,半夏除嘔,五味、乾薑以除咳也。以乾薑易生薑者,生薑之味氣不如乾薑之猛烈,其大溫足以逐心下之水,苦辛可以解五味之酸。且發表既有麻黃、細辛之直銳,更不藉生薑之橫散矣。若渴者,是心液不足,故去半夏之燥熱,加栝婁根之生津。若微利與噎,小便不利與喘者,病機偏於向裏,故去麻黃之發表,加附子以除噎,芫花、茯苓以利水,杏仁以定喘耳。兩青龍俱兩解表裏法,大青龍治裏熱,小青龍治裏寒,故發表之藥同,而治裏之藥殊也。此與五苓同為治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氣。在五苓治水畜而不行,故大利其水而微發其汗,是為「水鬱折之」也。本方治水之動而不居,故備舉辛溫以散水,並用酸苦以安肺,培其化源也,兼治膚脹最捷。葛根與大、小青龍,皆合麻、桂二方加減。葛根減麻黃、杏仁者,以不喘故。加葛根者,和太陽之津,升陽明之液也。大青龍減桂枝、芍藥者,以汗不出故。加石膏者,煩躁故也。若小青龍減麻黃之杏仁,桂枝之生薑、大棗,既加細辛、乾薑、半夏、五味,而又立加減法。神而明之,不可勝用矣。
|
傷寒病表證不解,心下有水氣,乾嘔發熱而渴,或下利、或噎隔、或小便不利而少腹脹滿、或喘者,用此方可發汗利水。汗為陽氣所化,猶如天地間之有雨。水液入心則化為汗,一旦汗出則外邪立刻解除。此證乃因心氣不足,汗出不透,導致寒熱不解而心下有水氣。咳嗽是水氣射肺之象,乾嘔則知水氣尚未入胃。心下是心胞絡相火所居之處,水火相互衝撞,其病狀難以形容。如水氣下行而不上升,則口渴或下利;水氣上行而不下降,則噎隔或喘息;水氣停留於腸胃,則小便不利而少腹脹滿。只有發熱、乾嘔而口渴,才是本方必然會出現之證候。本方是在桂枝湯中去黏滯之大棗,再加麻黃以開通玄府,細辛驅散水氣,半夏以除嘔,五味子和乾薑以止咳。用乾薑代替生薑,是因為生薑之氣味不及乾薑之猛烈,而乾薑大溫之性足以驅逐心下之水,其苦辛之味可以中和五味子之酸味。且發表之藥既然已有銳利之麻黃、細辛,則不再需要借助生薑橫散之性。如果口渴,是心液不足,因此去燥熱之半夏,加栝蔞根以生津。如果輕微下利及噎隔,小便不利和氣喘,病機偏於向裏,因此去發表之麻黃,加附子以止噎,芫花和茯苓以利水氣,杏仁以止喘。大青龍湯和小青龍湯都是表裏雙解之法,大青龍治裏熱,小青龍治裏寒,因此發表之藥相同,而治裏之藥就不同。本方與五苓散都用於治療表證不解而心下有水氣。五苓散治療水邪停蓄不行,所以利水為主而微發其汗,體現「水鬱折之」之法。本方治療水氣之變動不定,因此全面使用辛溫藥物以散水邪,同時使用酸苦藥物以安肺氣,培養水之化源,同時兼能有效治皮膚水腫。葛根湯與大、小青龍湯均是麻黃湯、桂枝湯二方之加減。葛根湯所以去麻黃、杏仁,是因為其人不喘。而加葛根則是為了調和太陽之津液,升發陽明之津液。大青龍湯所以去桂枝、白芍,是因為汗出不暢。而加石膏則是因為煩躁。至於小青龍湯去麻黃湯中之杏仁,桂枝湯中之生薑和大棗,已經增加了細辛、乾薑、半夏和五味子,還設立加減法。此方之變化與與運用,真是太多了。
|
|
|
此方又主水寒在胃,久咳肺虛。
|
此方還主治水寒在胃,以及久咳所致肺虛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五苓散 澤瀉 白朮 茯苓 猪苓 桂枝 |
||
|
太陽本病脉浮,發汗表証雖解,而膀胱之熱邪猶存,用之利水止渴,下取上效之法。桂性熱,少加為引導。五苓能通調水道,培助土氣,其中有桂枝以宣通衛陽,停水散,表裏和,則火熱自化,而津液得全,煩渴不治而治矣。
|
太陽本病脈浮,發汗後表證雖然解除,但膀胱之熱邪尚在,用本方可以利水止渴,通過治下而達到治上之目的。桂枝性熱,少量使用可以作為引導。五苓散能通調水道,輔助土氣,其中有桂枝可以宣通衛陽,停留之水濕得散,表裏之氣得和,則火熱自然消除,而津液得以保存,不需專門治煩渴而煩渴卻得以治愈。 |
|
|
治太陽發汗後,表熱不解,脉浮數,煩渴飲水,或水入即吐,或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。凡中風傷寒,結熱在裏,熱傷氣分,必煩渴飲水。治之有二法:表症已罷而脉洪大,是熱邪在陽明之半表裏,用白虎加人參,清火以益氣。表症未罷,而脉仍浮數,是寒邪在太陽之半表裏,用五苓散,飲煖水,利水而發汗。此因表邪不解,心下之水氣亦不散,既不能為溺,更不能生津,故渴。及與之水,非上焦不受,即下焦不通,所以名為「水逆」。水者,腎所司也。澤瀉味鹹入腎,而培水之本。猪苓黑色入腎,以利水之用。白朮味甘歸脾,制水之逆流。茯苓色白入肺,清水之源委而水氣順矣。然表裏之邪,諒不因水利而頓解。故必少加桂枝,多服煖水,使水精四布,上滋心肺,外達皮毛,溱溱汗出,表裏之煩熱兩除也。「白飲和服」,亦「啜稀粥」之微義,又複方之輕劑矣。
|
治療太陽發汗後,表熱仍解,脈浮數,煩渴飲水,或飲水即吐,或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。凡是中風或傷寒,熱邪滯留於裏而傷氣分,必然煩渴飲水。治療有二種方法:如果表證已消,但脈洪大,此為熱邪在陽明之半表裏,用白虎加人參湯,清熱以益氣。如果表證未消,而脈仍浮數,此為寒邪在太陽之半表裏,用五苓散,飲用溫水,利水而發汗。這是因為表邪不解,心下之水氣亦不消散,既不能化為尿,更不能化生津液,所以口渴。當飲水後,不是上焦不受,就是下焦不通,所以稱之為「水逆」。水是由腎所主司。澤瀉味鹹入腎,用以培水之本。豬苓黑色入腎,有利於水發揮作用。白朮甘味而歸於脾,能制約水氣之逆行。茯苓白色入肺,能清理水氣塞滯之源頭而使水氣順暢。然而,表裏之邪氣亦不會因為水氣通暢而立刻消除。因此,必須加入少量桂枝,多飲溫水,使水之精氣四布,上能滋養心肺,外達皮毛,使汗外出,則表裏之煩熱得以兩除。「白飲和服」,即是桂枝湯「啜稀粥」之意,同時是複方之輕劑。本方並非能治消渴,註家不能明察消渴發生之理以及「水逆」之特點,稱五苓散為化氣回津之方。四苓之燥,桂枝之熱,靠什麼能使津液回復?哪裏知道「消渴」與「水逆」是不同的,從「消」這個字中就可以看出,飲水多,但能被消,就不會發生水逆。《傷寒論》說:「飲水多者,小便利,必心下悸」,這是水氣停留在上焦而為逆;「小便少者,必苦裏急」,這是水氣滯留在下焦而為逆。又說:「渴欲飲水者,以五苓散救之。」由此可知使用五苓散原本是治療水氣,而不是治療口渴,用來散所飲之水,而不是治療煩渴、消渴。而且本方所重在於內煩外熱,用桂枝是通過逐水以除煩,而不是「熱因熱用」;是稍稍發汗以解表,而不是輔助四苓以利水。方中用四苓是為了消散積滯之水氣,而不是疏通水道。後人不明此理,一概以為是用來治療水道不通。熱邪盛於裏之時,心下已無水氣,則已經是無水氣可利,無汗可發。此時如果再進一步使用燥烈之藥,津液更加耗竭,怎麼能承受得住呢?《傷寒論》說:「下後復發汗,小便不利者,亡津液故也,勿治之。」又說:「若亡津液,陰陽自和者,必自愈。」又說:「汗出多,胃中燥,不可用豬苓湯復利其小便。」各種利水之方,只有豬苓湯是滋潤之劑,尚且不可用,對於不欲飲水而小便不利者,應當禁用五苓散,就無需多言了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十棗湯 大棗 芫花 甘遂 大戟 |
||
|
治太陽中風,表解後裏氣不和,下利,嘔逆,心下至脅痞滿硬痛,頭痛,短氣,汗出,不惡寒者。仲景利水之劑種種不同,此其最峻者也。凡水氣為患,或喘或咳,或利或吐,或吐利而無汗,病一處而已。此則外走皮毛而汗出,內走咽喉而嘔逆,下走腸胃而下利,水邪之泛溢者,既浩浩莫御矣。且頭痛,短氣,心腹脇下皆痞鞕滿痛,是水邪尚留結於中,三焦升降之氣拒隔而難通也。表邪已罷,非汗散所宜;裏邪充斥,又非滲泄之品所能治。非選利水之至銳者以直折之,中氣不支,亡可立待矣。甘遂、芫花、大戟,皆辛苦氣寒,而秉性最毒,並舉而任之,氣同味合,相須相濟,決瀆而大下,一舉而水患可平矣。然邪之所湊,其氣已虛,而毒藥攻邪,脾胃必弱。使無健脾調胃之品主宰其間,邪氣盡而元氣亦隨之盡。故選棗之大肥者為君,預培脾土之虛,且制水勢之橫,又和諸藥之毒,既不使邪氣之盛而不制,又不使元氣之虛而不支。此仲景立法之盡善也。用者拘於「甘能緩中」之說,豈知五行承制之理乎?張子和製濬川、禹功、神祐等方,治水腫痰飲,而不知君補劑以護本,但知用毒藥以攻邪,所以善全者鮮。
|
治太陽中風,表解後裏氣不和,下利,嘔逆,心下至脅部痞滿硬痛,頭痛,短氣,汗出,不惡寒者。仲景利水之方有各種不同,而本方是其中最峻猛的一種。對於水氣所引致之病證,或喘或咳,或下利或嘔吐,是吐利而無汗,病位只局限於某一處而已。此方所主之證,則水氣外走皮膚而汗出,內走咽喉而嘔吐,下走腸胃而下利,水邪泛溢,已經浩浩蕩蕩難以抵禦。而且頭痛,短氣,心腹脅下皆痞硬滿痛等,說明水邪仍停留於內,三焦升降之氣受阻而難以通暢。表邪已經解除,所以不適合再用發汗;裏邪充斥上下,所以亦不能用滲泄之品來治療。如果不用最有力的利水之方來直接攻伐水邪,則中氣難以支撐,病者很快就會死去。甘遂、芫花、大戟皆為辛苦而寒,稟性最劇烈,將其合併使用,氣味相合,相須相濟,破解水滯而大下之,一舉而平息水氣之患。然而,邪氣所湊,正氣已經虛弱,而毒藥攻邪,脾胃必然受損。假如沒有健脾調胃之藥來主宰中氣,邪氣雖盡但元氣亦隨之耗盡。因此選擇肥大棗為君藥,預先培補脾土之虛,同時阻止水邪之橫溢,又能調和諸藥峻猛之性,既不使邪氣亢盛而難以控制,又不使元氣虛弱而無法支撐。這是仲景立法盡善之處。有些醫者拘泥於「甘能緩中」之說,他們怎麼會知道五行承制之理呢?張子和製定的浚川散、禹功散、神祐丸等方劑,治療水腫痰飲,卻不知道應該以補益藥為君藥來預先顧護正氣,只懂得使用毒藥來攻邪,所以很少能夠萬無一失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|
||
|
此溫病發汗逐邪之主劑也。凡冬不藏精之人,熱邪內伏於藏府,至春風解凍,伏邪自內而出,法當乘其勢而汗之,勢隨汗散矣。然發汗之劑多用桂枝,此雖頭項強痛,反不惡寒而渴,是有熱而無寒。「桂枝下咽,陽盛則斃」,故於麻黃湯去桂枝之辛熱,易石膏之甘寒以解表裏俱熱之症。岐伯所云「未滿三日,可汗而已」者,此法是也。此病得於寒時而發於風令,故又名「風溫」。其脉陰陽俱浮,其症自汗,身重。蓋陽浮則強於衛外而閉氣,故身重,當用麻黃開表以逐邪。陰浮不能藏精而汗出,當用石膏鎮陰而清火。表裏俱熱,則中氣不運,升降不得自如,故多眠息鼾,語言難出,當用杏仁、甘草以調氣。此方備升降輕重之性,足以當之。若攻下、火熏等法,此粗工促病之術也。凡風寒在表,頭痛,發熱,惡寒,無汗者,必用麻黃發汗。汗後復煩,更用桂枝發汗。若溫病發汗已而身灼熱,是內熱猖獗,雖汗出而喘,不可更用桂枝湯。蓋溫暑之邪,當與汗俱出,而勿得止其汗。即灼然之大熱,仍當用此方開表,以清裏降火而平喘。蓋治內蘊之火邪,與外感之餘熱不同法也。若被下而小便不利、直視、失溲者,真陰虛極而不治。若汗出而喘,是熱勢仍從外越,雖未下前之大熱,因下而稍輕,仍當涼散,亦不得仿風寒未解之例。下後氣上冲者,更行桂枝湯也。是方也,溫病初起,可用以解表而清裏,汗後可復用,下後可復用,與風寒不解而用桂枝湯同法。仲景因治風寒汗下不解之症,必須桂枝,故特出此「涼解」之義,以比類桂枝加厚朴杏仁湯證,正與風寒、溫病分涇渭處,合觀溫病提綱,而大旨顯然矣。此大青龍之變局,白虎湯之先着也。石膏為清火重劑,青龍、白虎皆賴以建功,然用之謹甚。故青龍以惡寒脉緊,兼用薑、桂以扶衛外之陽。白虎以汗後煩渴,兼用參、米以保胃脘之陽也。此但熱無寒,佐薑、桂則脉流薄疾,斑、黃、狂亂作矣。此但熱不虛,加參、米則「食入於陰,氣長於陽」,詀語,腹脹矣。凡外感之汗下後,汗出而喘為實,重在存陰者,不必慮其亡陽也。然此為解表之劑,若無喘鼾、語言難出等症,則又白虎湯之證治矣。此方治溫病表裏之實,白虎加參、米,治溫病表裏之虛,相須相濟者也。若葛根黃連黃芩湯,則治利而不治喘。要知溫病下後,無利不止證,葛根、黃連之燥,非治溫藥。且麻黃專於外達,與葛根之和中發表不同。石膏甘潤,與黃連之苦燥懸殊。同是涼解表裏,同是汗出而喘,而用藥有毫釐千里之辨矣。
|
此方是治溫病用以發汗逐邪之主方。凡是冬不藏精之人,熱邪內伏於臟腑,到春天和暖之時,伏邪從內而出,就應順其勢而發汗,邪氣即隨汗散去。然而,發汗之方通常多用桂枝,儘管本方主治有頭項強痛,但卻不惡寒而渴,是有熱邪而無寒邪。「桂枝下咽,陽盛則斃」,所以從麻黃湯中去除辛熱之桂枝,而換成甘寒之石膏以解除表裏俱熱之證。岐伯所謂「未滿三日,可汗而已」,就是指這種方法。此病在寒冷之時受邪,而發作於行風令之春時,因此亦被稱為「風溫」。其脈陰陽俱浮,其證自汗、身重。脈陽浮則衛外之氣過強而使氣機閉塞,所以身重,應當用麻黃發表以驅邪。脈陰浮則不能藏精而汗出,應當用石膏鎮陰而清火。表裏俱熱,則中氣不運,升降無法自如,所以嗜睡而鼻鼾,語言難出,應當用杏仁、甘草以調氣機。此方具備升降輕重之性,足以擔當此任。如果採用攻下、火熏等方法,這是粗工使病情惡化之做法。凡風寒邪氣在表,頭痛,發熱,惡寒,無汗者,必須用麻黃湯發汗。汗後又煩躁,再用桂枝湯發汗。如果溫病發汗後身體灼熱,是內熱猖獗,雖然汗出而喘,不可再用桂枝湯。因為溫暑之邪應當與汗一同外出,而不能阻止其汗出。即使身體灼熱,仍然應當用此方打開表氣,以清降裏火而平喘。因為治療內蘊之火邪與外感餘熱之方法不同。如果被攻下後小便不利、直視、遺尿,是真陰虛極而不治之證。如果汗出而喘,說明熱勢仍然能向外散,雖然未經攻下前之大熱,因為攻下而稍有緩解,仍然應當涼散之法,不可效仿風寒未解之治法。攻下後氣上衝者,可再用桂枝湯。對於溫病初起,用本方可以解表而清裏,發汗後可再次使用,攻下後亦可再次使用,與風寒不解而使用桂枝湯之法相同。仲景因為治療風寒表證汗下後不解時必須用桂枝湯,所以特別提出「涼解」這個概念,與桂枝加厚朴杏仁湯相對,正好在風寒與溫病不同之處,結合溫病提綱條文,其主旨就非常明確了。此方是大青龍湯之變局,及運用白虎湯之先手。石膏是有力清火之藥,大青龍湯和白虎湯都依賴石膏來發揮效用,但使用時十分謹慎。因此,大青龍湯因為惡寒,脈緊而同時用生薑和桂枝以扶衛外之陽。白虎湯則因為汗後煩渴,所以要同時配合人參和粳米以保護胃中之陽氣。而本方所治之證但熱而不寒,如果用生薑和桂枝則會迫使脈流加快,則可能會導致發斑、黃疸、狂亂之證。本方所治之證又是但熱而不虛,如果用人參和粳米,則會「食入於陰,長氣於陽」而導致譫語、腹脹。凡是外感病發汗攻下後,汗出而喘屬實,重點在於保護陰氣,而不須擔心亡陽。然而本方為解表之劑,如果沒有喘息鼻鼾、語言困難等證,則又屬於白虎湯之證治。本方治療溫病表裏之實證,白虎湯用人參和粳米則治療溫病表裏之虛證,二方可以相須相濟。而葛根黃連黃芩湯,則治下利而不治喘。關鍵要知道溫病攻下後,沒有下利不止之證,葛根和黃連之燥性並非治療溫病之藥物。而且麻黃專於達外,與葛根之和中而發表不同。石膏甘潤,與黃連之苦燥又明顯不同。雖然治法都是涼解表裏,所治之證同樣都是汗出而喘,但用藥卻有「謬之毫釐,差之千里」之辨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麻黃 連翹 赤小豆 梓白皮 杏仁 甘草 生薑 大棗 |
||
|
治太陽傷寒妄下熱入,但頭汗出,小便不利,身體發黃。此以赤小豆、梓皮為君,而冠以麻黃者,見此為麻黃湯之壞症,此湯為麻黃湯之變劑也。傷寒不用麻黃發汗,而反下之,熱不得越,因瘀於裏,熱邪上炎,故頭有汗。無汗之處,濕熱熏蒸,身必發黃。水氣上溢皮膚,故小便不利。此心肺為瘀熱所傷,營衛不和故耳。夫皮膚之濕熱不散,仍當發汗,而在裏之瘀熱不清,非桂枝所宜。必擇味之酸苦,氣之寒涼而能調和營衛者,以涼中發表,此方所山1製也。小豆赤色,心家穀也,酸以收心氣,甘以瀉心火,專走血分,通經絡,行津液而利膀胱。梓白皮色白,肺家藥也,寒能清肺熱,苦以瀉肺氣,專走氣分,清皮膚,理胸中而散煩熱,故以為君。佐連翹、杏仁以瀉心,麻黃、生姜以開表,甘草、大棗以和胃。潦水味薄,流而不止,故能降火而除濕,取而煮之。半日服盡者,急方通劑,不必緩也。夫麻黃一方,與桂枝合半,則小發汗。加石膏、姜、棗,即於發表中清火而除煩躁。去桂枝之辛熱,加石膏之辛寒,則於發表中清火而定喘。君以文蛤2,即於發表中祛內外之濕熱。加連翹等之苦寒,即於發表中清火而治黃。仲景於太陽中隨証加減,曲盡麻黃之長技,不拘於冬月之嚴寒而用矣。若加附子、細辛之大辛熱,加附子、甘草之辛甘,亦因少陰表裏之微甚,並非為嚴寒之時拘。醫咸謂麻黃不可輕用,安知仲景之神化哉? |
治太陽病傷寒誤下後熱邪入裏,但頭汗出,小便不利,身體發黃。此方以赤小豆、梓白皮為君藥,而方名冠以麻黃,可視為麻黃湯證之壞證,而此方則是麻黃湯之變劑。對於太陽傷寒證不用麻黃湯發汗,反而攻下,則熱邪不得外越,因而瘀於裏,熱邪上炎,所以頭部有汗。無汗之部位,由於濕熱蒸騰,身體必然發黃。水邪外溢於皮膚,所以小便不利。這是心肺被瘀熱所傷,營衛不和之結果。皮膚之濕熱邪氣不散,仍需發汗,而在裏之瘀熱未清,則不是桂枝湯所能治。必須選擇味酸苦而氣寒涼之藥,能夠調和營衛以涼中發表,這就是創製此方之原因。赤小豆色赤,屬於與心氣相同之穀物,味酸可以收斂心氣,味甘可以瀉心火,專走血分,能通經絡,行津液而利膀胱之氣化。梓白皮色白,屬於肺家之藥,氣寒能清肺熱,味苦可以瀉肺氣,專走氣分,能清皮膚,理胸中而散煩熱,所以用為君藥。佐以連翹、杏仁以瀉心,麻黃、生薑以發表,甘草、大棗以和胃。潦水之味薄,流動而不停,因此能降火而祛濕,取此水煎煮藥物。之所以半日服盡,因為這是急方通利之劑,不必緩用。麻黃湯與桂枝湯合用之麻黃桂枝各半湯,可輕微發汗。加入石膏、生薑、大棗,則在發表過程中清熱除煩躁。去掉桂枝之辛熱,加入石膏之辛寒,則在發表過程中清熱定喘。以赤小豆為君藥,即可在發表過程中祛除內外之濕熱。加連翹之苦寒,即可在發表過程中清熱而治黃疸。仲景在太陽病中隨證加減,充分發揮麻黃湯之長處,而不僅僅局限於嚴寒之冬季才使用。若加大辛大熱之附子、細辛,或加辛甘之附子、甘草,亦是因為少陰病表裏證之微甚,並非受限於嚴寒之時使用。醫者都認為麻黃不應隨便運用,他們怎麼知道仲景對麻黃湯有如此神奇之變化呢? |
|
|
1 山:他本作「由」,當為「由」。 |
||
|
2 文蛤:本方中無「文蛤」,此處當為「赤小豆」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文蛤湯 文蛤 麻黃 石膏 杏仁 甘草 姜棗 |
||
|
病發於陽,應以汗解。庸工用水攻之法,熱被水劫而不得散。外則肉上粟起,因濕氣凝結於玄府也。內則煩熱,意欲飲水,是陽邪內鬱也。當渴而反不渴者,皮毛之水氣入肺也。夫皮肉之水氣,非五苓散之可任,而小青龍之溫散,又非內煩者之所宜,故製文蛤湯。文蛤生於海中而不畏水,其能制水可知。鹹能補心,寒能勝熱,其殼能利皮膚之水,其肉能止胸中之煩,故以為君。然陽為陰鬱,非汗不解,而濕在皮膚,又不當動其經絡,熱淫於內,亦不可發以大溫,故於麻黃湯去桂枝而加石膏、姜、棗,此亦大青龍之變局也。其不差者,更與五苓散以除未盡之邪。若汗出已而腹中痛者,更與芍藥湯以和肝脾之氣。 |
病發於陽,應以發汗解表。庸醫用水攻之法,使得熱邪被水鬱而無法外散。在外見皮膚上起粟粒狀,這是因為濕氣凝結於玄府。在內則出現煩熱而欲飲水,這是因為陽邪內鬱。由口渴變成不渴,是皮毛之水邪入肺。由於皮肉間之水氣不是五苓散所能治,而小青龍湯之溫散又不適用於有內煩者,因此創製文蛤湯。文蛤生長於海中而不畏水,因此知其能制衡水氣。味鹹能補心,氣寒能制熱,其殼能利皮膚之水,其肉能平胸中之煩,因此用作君藥。然而陽邪被水氣所鬱,非發汗不可,但濕氣滯留在皮膚,又不宜擾動經絡,熱邪內鬱,亦不可用大溫之法,因此在麻黃湯中去桂枝,加石膏、生薑、大棗,這亦算是大青龍湯之變局。服藥後,如果病情未有好轉,再用五苓散以除未盡之邪。如果汗出後而腹中痛者,再用芍藥湯以和肝脾之氣。 |
|
|
按:本論以文蛤一味為散,以沸湯和方寸匕,服滿五合。此等輕劑,恐難散濕熱之重邪。《金匱要畧》云:「渴欲飲水不止者,文蛤湯主之。」審症用方,則此湯而彼散,故移彼方而補入於此。 |
按:《傷寒論》是以文蛤一味為散,用沸水沖服方寸匕,服用滿五合。如此力量薄弱之劑,恐怕難以驅散濕熱之重邪。《金匱要略》中說:「渴欲飲水不止者,文蛤湯主之。」審證用方,則應該是此用文蛤湯而彼用文蛤散,因此將彼之文蛤湯補入於此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湯二分 麻黃湯一分 |
||
|
服桂枝湯後而惡寒發熱如瘧者,是本當用麻黃發汗,而用桂枝則汗出不徹故也。凡太陽發汗太過則轉屬陽明,不及則轉屬少陽。此雖寒熱往來,而頭項強痛未罷,是太陽之表尚在,故仍在太陽。夫瘧因暑邪久留而內著於募原,故發作有時,日不再作。此因風邪泊於營衛,動靜無常,故一日再發,或三度發耳。邪氣稽留於皮毛肌肉之間,固非桂枝湯之可解。已經汗過,又不宜麻黃湯之峻攻。故取桂枝湯三分之二,麻黃湯三分之一,合而服之,再解其肌,微開其表。審發汗於不發之中,此又用桂枝後更用麻黃法也。後人合為一方者,是大背仲景比較二方之輕重,偶中出奇之妙理矣。 |
服用桂枝湯後,如果出現惡寒發熱類似於瘧病者,是原本應該用麻黃湯發汗,而用了桂枝湯則導致汗出不暢所致。凡是太陽病發汗過多則轉屬為陽明病,發汗不足則轉屬為少陽病。這裏雖然有寒熱往來,但頭頸強痛並未消失,說明太陽表證尚在,因此仍屬於太陽病。瘧病是因為暑邪久留而內著於募原,所以寒熱發作有時,每天只發作一次。這裏則因為風邪停留於營衛,動靜無常,所以一日內發作二次,甚至三次。邪氣滯留在皮膚肌肉之間,固然不是桂枝湯所能解決。而且已經發過汗,又不適宜用發汗力強之麻黃湯。因此,取桂枝湯原方三分之二,麻黃湯原方三分之一,將兩方合在一起服用,再次解肌以稍微開發其表。謹慎地審察在不發汗之情況下進行發汗,這又是用桂枝湯之後再用麻黃湯之法。後人將此二方合為一方,完全背離仲景根據二方發汗力之輕重,偶方之中又出奇方之巧妙原理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麻黃合半湯 桂枝湯三合 麻黃湯三合 |
||
|
太陽病得之八九日,如瘧狀,發熱惡寒,熱多寒少,面有赤色者,是陽氣拂鬱在表不得越。因前此當汗不汗,其身必癢,法當小發汗,故以麻、桂二湯各取三分之一,合為半服而急汗之。蓋八九日來,正氣已虛,表邪未解,不可不汗,又不可多汗。多汗則轉屬陽明,不汗則轉屬少陽。此欲祗從太陽而愈,不再作經,故立此法耳。此與前症大不同,前方因汗不如法,雖「不徹」,而已得汗,故取桂枝二分,入麻黃一分,合為二升,分再服而緩汗之。此因未經發汗,而病日已久,故於二湯各取三合,併為六合,頓服而急汗之。兩湯相合,涇渭分明,見仲景用偶方輕劑,其中更有緩急、大小、反佐之不同矣。原法兩湯各煎而合服,猶水陸之師,各有節制,兩軍相為表裏,異道夾攻之義也。後人算其分兩合為一方,與葛根、青龍輩何異? |
太陽病八九日之後,發熱惡寒如瘧病一般,發熱多而惡寒少,面部發紅,此乃陽氣鬱滯在表而無法外越。在此之前應該發汗而未發汗,身體必癢,則應該輕微發汗,因此取麻黃湯和桂枝湯各三分之一,合為半劑藥之劑量以求速汗。因為得病八九日以來,正氣已經虛弱,而表邪未解,不能不發汗,又不能發汗太過。汗出過多則轉屬為陽明病,汗不出則轉屬為少陽病。在此只想從太陽病將其治癒,不使其發生傳變,因此創立此法。這與之前之病證大不相同,前方桂枝二麻黃一湯所治是由於汗不如法,雖然發汗沒有透徹,但已經有汗出,所以取桂枝湯二分,加入麻黃湯一分,合為二升,分兩次服用以緩和地發汗。這是因為尚未經過發汗,而且病程已久,所以從二湯中各取三合,合併為六合,一次性服下以取速汗。兩湯相合,其作用涇渭分明,可見仲景用偶方之輕劑,其中還有緩急、大小、反佐之不同。原來之方法是將兩湯分別煎煮後合併服用,猶如水陸軍隊,各有節制,兩軍相為表裏,從不同方向夾擊敵人。後人計算其分兩後再將兩方合而為一,這與葛根湯、青龍湯等方有什麼不同呢?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二越婢一湯 金匱越婢湯 麻黃 石膏 甘草 姜1 |
||
|
太陽病,發熱惡寒,熱多寒少,脉微弱者,此無陽也,不可發汗,故立此方。按:本論無越婢症,亦無越婢湯,後人取《金匱》方補之。竊謂仲景言「不可發汗」,則必不用麻黃。言「無陽」,是無胃脘之陽,亦不用石膏。古方多有名同而藥不同者,安可循名而不審其實也?此等脉症最多,宜用柴胡桂枝為恰當。 |
太陽病,發熱惡寒,發熱多而惡寒少,脈微弱者,此為無陽,不可發汗,因此創製此方。按:《傷寒論》中沒有越婢證,亦沒有越婢湯,後人取《金匱要略》方補充。我以為仲景說「不可發汗」,則必然不會用麻黃。說「無陽」,是指無胃脘之陽,亦不會用石膏。古方中常有名稱相同而藥物不同者,怎麼可以只因循其名而不審察其實際?這樣的脈證臨床最多見,適宜使用柴胡桂枝湯較為合適。 |
|
|
按:喻嘉言云:「越婢者,石膏之辛涼也,以此兼解其寒。柔緩之性,比女婢為過之。」夫辛涼之品,豈治寒之劑?而金石之堅重,豈能柔緩如女婢哉?考越婢方,比大青龍無桂枝、杏仁,與麻黃杏子石膏湯同為涼解表裏之劑。此不用杏仁之苦,而用姜、棗之辛甘,可以治太陽陽明合病熱多寒少而無汗者,猶白虎湯症「背微惡寒」之類,而不可以治脉弱、無陽之證也。 |
按:喻嘉言說:「越婢,就是指石膏之辛涼,用此藥兼能解其寒。其柔緩之性,比女婢更柔和。」辛涼之品,豈能用作治寒之劑?而屬於金石堅重之品,豈能有如女婢一樣柔緩呢?考查越婢湯一方,與大青龍湯相比,沒有桂枝、杏仁,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一樣同為涼解表裏之劑。此方不用苦味之杏仁,而用辛甘之生薑和大棗,可以治療太陽陽明合病發熱多、惡寒少而且無汗者,類似於白虎湯證中「背微惡寒」之類,所以本方不能治療脈弱、無陽之證。 |
|
|
按:《外臺秘要》云:「越脾湯易此一字,便合《內經》『脾不濡,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』之義。」是脾經不足而無汗者,可用此起太陰之津,以滋陽明之液而發汗,如成氏所云「發越脾氣者」是也。然必兼見煩渴之症,脉雖不長大,浮緩而不微弱者宜之。 |
按:《外台秘要》說:「將越婢湯轉換一字,就成越脾湯,便符合《內經》中『脾不濡,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』之義。」這是脾氣不足而無汗,可以通過此方來升提太陰之津液,用以滋養陽明之液而發汗,即如成無己所說「發越脾氣者」。但必須同時伴有煩渴之證,脈雖不長大,但脈浮緩而不微弱之人才適宜用此方。 |
|
|
1 《金匱要略》越婢湯中有大棗,在此未有提及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加附子湯 |
||
|
太陽病發汗,遂漏不止,其人惡風,小便難,四肢微急,難以屈伸者,此發汗不如法也。病在太陽,固當發汗,然得微似有汗者佳。發汗太過,陽氣無所止息,而汗出不止矣。汗多亡陽,玄府不蔽,風乘虛入,故復惡風。津液外泄,不能潤下,故小便難。四肢者,諸陽之本。陽氣者,柔則養筋。開闔不得,寒氣從之,故筋急而屈伸不利。此離中陽虛,不能斂液,當用桂枝湯補心之陽,陽密則漏汗自止,惡風自罷矣。坎中陽虛,不能制水,必加附子以固腎之陽,陽回則小便自利,四肢自柔矣。「漏不止」與「大汗出」不同。服桂枝湯後,大汗出而大煩渴,是陽陷於裏,急當滋陰,故用白虎加參以和之。用麻黃湯遂漏不止,是陽亡於外,急當扶陽,故用桂枝加附以固之。要知發汗之劑,用桂枝太過,則陽陷於裏。用麻黃太過,則陽亡於外。因桂枝湯有芍藥而無麻黃,故雖大汗出,而玄府仍能自閉,但能使陽盛,斷不致亡陽。又與「汗出不解」者異。此發汗,汗遂不止,是陽中之陽虛,不能攝汗,所以本證之惡風不除,而變症有四肢拘急之患,小便難之理,故仍用桂枝加附以固太陽衛外之氣也。彼發汗,汗出不解,是陰中之陽虛,汗雖出而不徹,所以本症之發熱不除,而變症見頭眩身振之表,心下悸之裏,故假真武湯以固坎中真陰之本也。與「傷寒,自汗」1條似同而實異。彼腳攣急在未汗前,是陰虛。此四肢急在發汗後,是陽虛。自汗因心煩,其出微。遂漏因亡陽,故不止。小便數,尚不難;惡寒微,不若惡風之甚;腳攣急,尚輕於四肢不利也。彼用芍藥甘草湯,此用桂枝加附子,其命劑懸殊矣。 |
太陽病發汗後,隨即汗漏不止,患者惡風,小便難,四肢微急,難以屈伸者,這是發汗未能達到要求。病在太陽,當然應該發汗,但應該微微並持續汗出為佳。如果發汗過度,不能阻止陽氣外泄,則會汗出不止。汗多則損耗陽氣,玄府不閉,風邪乘虛而入,所以又出現惡風。津液外泄,不能滋潤下焦,所以小便難。四肢,是諸陽之本。陽氣養筋,則筋脈柔順。由於陽氣虛弱而玄府不能正常開合,寒氣因而侵襲,所以筋脈拘急而屈伸不利。這是離中陽虛而不能收斂陰液,應該用桂枝湯補心之陽,陽氣充實而玄府固密則漏汗自止,惡風自罷。坎中陽虛則不能制水,必須加附子以固腎之陽,陽氣回復則小便自利,四肢自然柔順。「漏不止」與「大汗出」是不同的。服桂枝湯後,大汗出而大煩渴,是陽氣陷於裏,急需滋養陰液,因此用白虎加人參湯以和之。用麻黃湯後隨即漏汗不止,是陽氣外亡,急需扶助陽氣,因此用桂枝加附子湯以固陽。關鍵要知道發汗之劑,用桂枝湯太過,則陽氣陷於裏。用麻黃湯太過,陽氣則亡於外。因為桂枝湯中有芍藥而無麻黃,所以雖然大汗出,玄府仍能自我關閉,只能令陽盛,絕不會導致亡陽。又與「汗出不解」不同。這裏是發汗後因而汗出不止,是陽中之陽虛而不能固攝汗液,因此原本之惡風不除,而又有四肢拘急和小便困難等變證,因此仍然要用桂枝加附子湯以固護太陽衛外之氣。而後者是發汗後,汗雖出而證不解,是陰中之陽虛,雖然有汗出但不透徹,所以原本之發熱不除,而又有在表之頭暈、身振動,以及在裏心下悸動之變證,因此要通過真武湯以固坎中真陰之本。本證與「傷寒,自汗」條所論看似相似但實際是不同的。那條所論腳抽搐是發生在未發汗之前,是陰虛。而本證之四肢拘急是發生在發汗後,是陽虛。那條所論自汗是由於心煩,所以汗出較微。而本條漏汗是因為亡陽,所以汗出不止。那條所論小便頻,尚未至於難;惡寒微,則不如惡風嚴重;腳攣急,則比四肢不利要輕。因此,對於前者用芍藥甘草湯,而本條則用桂枝加附子湯,從命名來看,二方之差異是非常明顯的。 |
|
|
1 指《傷寒論》第29條,原文為:「傷寒,脈浮,自汗出,小便數,心煩,微惡寒,腳攣急,反與桂枝,欲攻其表,此誤也。得之便厥,咽中乾,煩躁,吐逆者,作甘草乾薑湯與之,以復其陽。若厥愈足溫者,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,其腳即伸。若胃氣不和、譫語者,少與調胃承氣湯。若重發汗,復加燒針者,四逆湯主之。」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芍藥甘草附子湯 |
||
|
發汗而病不解,反惡寒,其裏虛可知也。夫發汗所以逐寒邪,故祗有寒去而熱不解者。今惡寒比未汗時反甚,表雖不解,急當救裏矣。蓋太陽有病,本由少陰之虛,不能藏精而為陽之守。若發汗以扶陽,寒邪不從汗解,是又太陽陽虛,不能衛外,令陰邪得以久留。亡陽之兆,已見於此,仍用姜、桂以攻裏,非以扶陽,而反以亡陽矣。故於桂枝湯去桂枝、姜、棗,取芍藥收少陰之精,甘草緩陰邪之逆,加附子固坎中之火,但使腎中元陽得位,表邪不治而自解矣。按:少陰亡陽之症,未曾立方,本方恰與此症相合。芍藥止汗,收肌表之餘津。甘草和中,除咽痛而止吐利。附子固少陰而招失散之陽,溫經絡而緩脉中之緊。此又仲景隱而未發之旨歟?作芍藥甘草湯治腳攣急,因其陰虛。此陰陽俱虛,故加附子,皆治裏不治表之義。 |
發汗而病不解,反惡寒,可知其裏虛。發汗是為了驅逐寒邪,所以只有寒邪去而熱不解。現在惡寒比未發汗時反而更加嚴重,表證雖然未解,但急需救治其裏。因為太陽病本來就是由於少陰虛弱,無法藏精而起到守護陽氣之作用。如果通過發汗來扶持陽氣,卻無法使寒邪隨汗而解,那就是太陽之陽氣虛弱,不能捍衛肌表,導致陰邪得以久留。亡陽之徵兆已經在此表現出來,如果仍然用生薑和桂枝來治裏,這並不是扶持陽氣,反而加速亡陽。因此在桂枝湯中去掉桂枝、生薑和大棗,只取芍藥以收斂少陰之精氣,用甘草緩解陰邪之逆亂,再加附子鞏固坎中之火,只要使腎中之元陽復位,表邪就會不治而自行解除。按:對於少陰亡陽之證,未曾為此專門立方,此方正好與少陰亡陽證相符。芍藥止汗,可以收斂肌表剩餘之津液。甘草和中,可以除咽痛而止吐利。附子鞏固少陰而招回散失之陽氣,能溫經絡而緩和脈絡之拘急。這又是仲景隱而未發之旨意嗎?創製芍藥甘草湯治療腳攣急,是由於屬於陰虛。這裏是陰陽俱虛,所以加附子,都是為了治裏而不治表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甘草湯 |
||
|
此補心之峻劑也。發汗過多,則心液虛,心氣餒,故心下悸。叉手冒心則外有所衛,得按則內有所依。如此不堪之狀,望之而知其虛矣。桂枝本營分藥,得麻黃、生姜則令營氣外發而為汗,從辛也。得芍藥則收斂營氣而止汗,從酸也。得甘草則內補營氣而養血,從甘也。此方用桂枝為君,獨任甘草為佐以補心之陽,則汗出多者,不至於亡陽矣。姜之辛散,棗之泥滯,固非所宜,並不用芍藥者,不欲其苦泄也。甘溫相得,氣和而悸自平,與心中悸而煩、心下有水氣而悸者迥別。 |
這是峻補心陽之方。發汗過多則心液虛而心氣不足,所以心下悸。叉手冒心則在外有所護衛,得按則在內有所依托。如此嚴重之狀態,透過望診就可知是虛證。桂枝本屬營分藥,得麻黃、生薑則令營氣外發而為汗,這是辛味藥之作用。得芍藥則能收斂營氣而止汗,這是酸味藥之作用。得甘草則能內補營氣而養血,這是甘味藥之作用。此方用桂枝為君藥,只是用甘草作為輔助以補益心陽,則汗出過多之人就不至於亡陽。生薑之辛散,大棗之黏滯,固然是不適宜的,而又不用芍藥,是不願其苦泄。甘溫之氣相互配合,氣和而心悸自平,這與心中悸而煩、心下有水氣而悸等證是明顯不同的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|
||
|
發汗後,心下悸欲得按者,心氣虛而不自安,故用桂枝甘草湯以補心。若臍下悸欲作奔豚者,是腎水乘心而上剋,故製此方以瀉腎。豚為水畜,奔則昂首疾馳,酷肖水勢上攻之象,此症因以為名。臍下悸時,水氣尚在下焦,欲作奔豚之兆而未發也,當先其時而急治之。君茯苓之淡滲以伐腎邪,佐桂枝之甘溫以保心氣,甘草、大棗培土以制水。「亢則害」者,「承乃制」矣。瀾水狀似奔豚,而性則柔弱,故又名「勞水」,用以先煮茯苓,「水鬱折之」之法。繼以諸甘藥投之,是制以所畏,令一惟下趨耳。 |
發汗後,心下悸欲得按者,是心氣虛弱而不能自安,所以用桂枝甘草湯以補心。如果是臍下悸欲作奔豚者,是腎水乘心虛而上逆克火,因此製作此方以瀉腎水。豚是屬水之家畜,奔跑時昂首而快速向前,非常類似水勢上攻之象,此證因此而得以命名。臍下悸時,水氣尚在下焦,有奔豚之兆但尚未發作,應該在未發作之前迅速治療。以淡滲之茯苓為君藥以伐腎邪,佐以甘溫之桂枝以保護心氣,甘草和大棗培土以制水。所謂「亢則害」者,「承乃制」。甘瀾水之象亦似奔豚,但性則柔弱,所以又稱為「勞水」,用此水先煮茯苓,是「水鬱折之」之法。然後再放入其他甘味藥,是以相畏之法制約水氣,使水邪只能往下泄出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去芍藥生姜新加人參湯 |
||
|
發汗後,又見身疼痛,是表虛,不得更兼辛散,故去生姜。脉沉為在裏,遲為藏寒,自當遠斥陰寒,故去芍藥。惟在甘草大棗以佐桂枝,則桂枝當入心養血之任,不復為解肌發汗之品矣。然不得大補元氣之味以固中,則中氣不能遽復,故加人參以通血脉,則營氣調和,而身痛自瘳。名曰「新加」者,見表未解者,前此無補中法,今因脉沉遲,故爾始加也。此與用四逆湯治身疼脉沉之法同。彼在未汗前而脉反沉,是內外皆寒,故用乾姜、生附大辛大熱者,協甘草以逐裏寒,而表寒自解。此在發汗後而脉沉遲,是內外皆虛,故用人參之補中益氣者,以助桂枝、甘草而通血脉,是調中以發表之義也。此與桂枝人參湯不同者,彼因妄下而胃中虛寒,故用姜、朮。表尚協熱,故倍桂、甘。此因發汗不如法,亡津液而經絡空虛,故加人參。胃氣未傷,不須白朮。胃中不寒,故不用乾姜耳。是敦厚和平之劑也(坊本作加芍藥、生姜者誤)。 |
發汗後,又見身疼痛,這是表虛,不可再同時用辛散之藥,所以去生薑。脈沉為病在裏,脈遲為臟寒,自然應當遠離陰寒之藥,所以去芍藥。只用甘草和大棗輔助桂枝,則桂枝就當入心以滋養心血,而不再是解肌發汗之藥。然而,如果沒有大補元氣之藥來固護中焦,則中氣無法迅速恢復,所以加人參以通血脈,則營氣調和,而身體疼痛自然痊愈。名之為「新加」,是因為之前表未解之治法中,並沒有補中之法,現在因為脈沉遲,所以才開始增加補中之法。這與用四逆湯治療身疼痛而脈沉之法相同。四逆湯證是在未發汗之前脈反沉,屬於內外皆寒,所以用乾薑、生附子這類大辛大熱之藥,配合甘草以驅散裏寒,則表寒自然解除。這是在發汗後而脈沉遲,屬於內外皆虛,所以用具有補中益氣作用之人參以輔助桂枝和甘草通利血脈,屬於調和中焦以發散表邪之義。這與桂枝人參湯之不同,在於桂枝人參湯所治是因為誤下所致胃中虛寒,所以用乾薑和白朮。在表尚發熱,所以倍用桂枝和甘草。而此方所治則是因為發汗不如法,亡津液而經絡空虛,所以加人參。胃氣未受傷,則不需用白朮。胃中不寒,則不需用乾薑。這是一種敦厚平和之劑(坊間版本指本方加芍藥和生薑,是錯誤的)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|
||
|
服桂枝湯已,桂枝症仍在者,當仍用桂枝如前法。而或妄下之,下後,其本症仍頭痛項強,翕翕發熱,而反無汗。其變症心下滿微痛,而小便不利,法當利小便則愈矣。凡汗下之後,有表裏症兼見者,見其病機向裏,即當救其裏症。心下滿而不鞕,痛而尚微,此因汗出不徹,有水氣在心下也。當問其小便,若小便利者,病仍在表,仍須發汗。如小便不利者,病根雖在心下,而病機實在膀胱。由膀胱之水不行,致中焦之氣不運,營衛之汗反無,乃太陽之府病,非桂枝症未罷也。病不在經,不當發汗。病已入府,法當利水。故於桂枝湯去桂而加苓、朮,則姜、芍即為利水散邪之佐,甘、棗得效培土制水之功,非復辛甘發散之劑矣。蓋水結中焦,可利而不可散,但得膀胱水去,而太陽表裏之邪悉除,所以與小青龍、五苓散不同法。《經》曰:「血之與汗,異名而同類。」又曰:「膀胱津液,氣化而後能出。」此汗由血化,小便由氣化也。桂枝為血分藥,但能發汗,不能利水。觀五苓方未云「多服煖水,出汗愈」,此云「小便利則愈」。比類二方,可明桂枝去桂之理矣。今人不審,槩用五苓以利水,豈不悖哉? |
服桂枝湯後,而桂枝湯證仍在者,應當仍舊用桂枝湯,並按照前法服用。但或者被誤下,攻下後其本證仍在,頭痛項強,翕翕發熱,而反無汗。而變證則見心下脹滿微痛,小便不利,治法上應利小便則愈。凡是發汗攻下後,有表裏證並存者,見其病機向裏,就應治其裏證。心下滿而不硬,疼痛還較輕微,這是因為汗出不透徹,有水氣在心下。應當詢問患者之小便,如果小便利,病變仍然在表,仍需要發汗。如果小便不利,其病根雖然在心下,但病機實際上在膀胱。因為膀胱之水液不行,導致中焦之氣機不運轉,營衛之汗反而無法化生,這是太陽之腑病,並非桂枝湯證未罷。病變不在經,則不應該發汗。病變已經入腑,則應當利水。因此在桂枝湯中去桂枝而加茯苓和白朮,如此則生薑和芍藥隨即成為利水散邪之輔助藥物,甘草和大棗則能起到培土制水之功,而不再是辛甘發散之劑。由於水邪凝結在中焦,只可以利而不可以散,只要能去除膀胱之水邪,太陽表裏之邪就都可以被清除,所以這與小青龍湯、五苓散之治法不同。《內經》說:「血與汗,名稱不同但都屬於同一類。」又說:「膀胱所藏之津液,經過氣化然後能出。」這就說明汗是由血所化,而小便則是通過氣化。桂枝為血分藥,只能發汗而不能利水。看看五苓散方後提到「多服暖水,汗出愈」,本方方後說「小便利則愈」。通過比較此二方,就可以明白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之原理。今人不明此理,一概用五苓散利水,難道不是錯誤嗎?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人參湯 桂枝 甘草 乾姜 白朮 人參 |
||
|
葛根黃連黃芩湯 葛根 黃連 黃芩 甘草 |
||
|
太陽病,外症未解而反下之,遂協熱而利,心下痞鞕,脉微弱者,用桂枝人參湯。本桂枝症,醫反下之,利遂不止,其脉促,喘而汗出者,用葛根黃連黃芩湯。二症皆因下後外熱不解,下利不止。一以脉微弱而心下痞硬,是脉不足而症有餘。一以脉促而喘,反汗出,是脉有餘而症不足。表裏虛實,當從脉而辨症矣。弱脉見於數下後,則痞鞕為虛,非辛熱何能化痞而軟鞕?非甘溫無以止利而解表。故用桂枝、甘草為君,佐以乾姜、參、朮。先煎四味,後內桂枝,使和中之力饒而解肌之氣銳,是又於兩解中行權宜法也。桂枝症,脉本緩,誤下後而反促,陽氣重可知。邪束於表,陽擾於內,故喘而汗出。利遂不止者,此「暴注下迫,屬於熱」,與脉微弱而協熱利者不同。表熱雖未解,而大熱已入裏,故非桂枝、芍藥所能和,亦非厚朴、杏仁所能解矣。故君氣輕質重之葛根,以解肌而止利。佐苦寒清肅之芩、連,以止汗而除喘。用甘草以和中。先煮葛根,後內諸藥,解肌之力優而清中之氣銳,又與補中逐邪之法迥殊矣。上條脉症是陽虛,表雖有熱,而裏則虛寒。下條脉症是陽盛,雖下利不止,而表裏俱熱。同一協熱利,同是表裏不解,而寒熱虛實攻補不同。前方用理中加桂枝,而冠桂枝於人參之上。後方用瀉心加葛根,而冠葛根於芩、連之首。不名「理中」、「瀉心」者,總為表未解,故仍不離解肌之名耳。仲景製兩解方,神化莫測,補中亦能解表,涼中亦能散表;補中亦能散痞,涼中亦能止利。若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矣。 |
太陽病,外證未解而反攻下,因而協熱下利,心下痞硬,脈微弱者,用桂枝人參湯。原本為桂枝湯證,卻被醫者誤下,因而下利不止,脈促,喘而汗出者,用葛根黃連黃芩湯。這兩種情況都是由於攻下後外熱不解,又有下利不止。一是脈微弱而心下痞硬,是脈象屬虛而證候屬實。另一是脈促而喘,反汗出,是脈象屬實而證候屬虛。表裏之虛實應當跟從其脈象來辨證。弱脈出現在多次攻下之後,則痞硬屬虛證,不用辛熱之藥怎麼能化痞而軟硬?不用甘溫之藥則不能止利而解表。因此用桂枝、甘草作為君藥,輔以乾薑、人參、白朮。先煮四味藥物,後下桂枝,使和中之力強而解肌之氣銳,這又是在表裏兩解之中採取之權宜治法。桂枝湯證之脈本應緩,誤下後脈反促,可見陽氣重。邪氣束縛於表,陽邪擾亂在內,所以喘而汗出。下利因而不止者,這是「暴注下迫,屬於熱」,與脈微弱而協熱下利不同。表熱雖然未解,但大熱已入於裏,所以不是桂枝、芍藥所能調和,亦不是厚朴、杏仁所能解除。因此用輕氣重質之葛根為君藥,用於解肌並止利。輔以苦寒清肅的之黃芩、黃連,以止汗而定喘。用甘草以調和中氣。先煮葛根,然後放入其他藥物,使其解肌之力強而清中焦之氣銳,這與補中逐邪之法明顯不同。上條脈證是陽虛,雖然表有熱,但在裏已是虛寒。下條脈證是陽盛,雖然下利不止,但表裏俱熱。同樣都是協熱下利,同樣都是表裏不解,但寒熱虛實所用攻補之法不同。前方用理中湯加桂枝,並於方名上將桂枝列在人參湯之前。後方用瀉心湯法加葛根,並於方名上將葛根放在黃連、黃芩之前。不將其命名為「理中湯」、「瀉心湯」,總是因為表證未解,因此其方名仍然離不開解肌。仲景創製此表裏兩解之方,變化莫測,補益之中亦能解表,涼解之中亦能解表;補益之中亦能散痞,涼解之中亦能止利。如果不能有此認識,則會失之毫釐,差之千里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去芍藥湯 |
||
|
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|
||
|
太陽病,下之後,脈促胷滿者,桂枝去芍藥湯主之。若更見微惡寒者,去芍藥方中加附子主之。夫促為陽脈,胸滿為陽症。然陽盛則促,陽虛亦促。陽盛則胸滿,陽虛亦胸滿。此下後脈促而不汗出,胸滿而不喘,非陽盛也,是寒邪內結,將作結胸之脈。桂枝湯陽中有陰,去芍藥之酸寒,則陰氣流行而邪自不結,即扶陽之劑矣。若微見惡寒,則陰氣凝聚,恐姜、桂之力薄不能散邪,加附子之辛熱,為純陽之劑矣。仲景於桂枝湯一減一加,皆成溫劑,而更有淺深之殊也。 |
太陽病,下之後,脈促而胸滿者,桂枝去芍藥湯主治。如果兼見微惡寒者,桂枝去芍藥方中加附子來主治。脈促屬陽脈,胸滿為陽證。然而,陽盛則脈促,陽虛亦脈促。陽盛則胸滿,陽虛亦胸滿。這是下後脈促而不汗出,胸滿而不喘,則非陽盛,而是寒邪內結,即將形成結胸之脈證。桂枝湯中陽中有陰,去除芍藥之酸寒,則陰氣得以流行而邪氣自然不會凝聚,這就變成了扶陽之方。如果見微惡寒,則陰氣凝聚,恐怕生薑、桂枝之力量單薄而不能驅散邪氣,因此加辛熱之附子,則變成為純陽之方。仲景在桂枝湯之基礎上一減一加,都成為溫補之方,而又有淺深之別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|
||
|
治太陽下後微喘,而表未解者。夫喘為麻黃症,方中治喘者,功在杏仁。桂枝本不治喘,此因妄下後,表雖不解,腠理已疏,則不當用麻黃而宜桂枝矣。所以宜桂枝者,以其中有芍藥也。既有芍藥之斂,若但加杏仁,則喘雖微,恐不能勝任,必加厚朴之辛溫,佐桂以解肌,佐杏仁以降氣。故凡喘家不當用麻黃湯而作桂枝湯者,加厚朴、杏仁為佳法矣。 |
治療太陽病被攻下後出現微喘,而表證未解者。喘屬於麻黃湯證,而方中治喘之藥則在於杏仁。桂枝湯本身並不治喘,這是因為誤下後表證雖然不解,但腠理已經疏鬆,則不宜用麻黃湯而應該用桂枝湯。之所以適合用桂枝湯,是因為其中有芍藥。既然有了芍藥之收斂,如果只是加杏仁,喘雖然輕微,恐怕亦不能勝任,必須在桂枝湯中加入辛溫之厚朴,既能輔助桂枝以解肌,又能輔助杏仁以降氣。因此,凡是喘家而不宜用麻黃湯,而改用桂枝湯者,加厚朴和杏仁是較好之方法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加芍藥湯 |
||
|
桂枝加大黃湯 |
||
|
妄下後,外不解而腹滿時痛,是太陽太陰併病。若大實痛,是太陽陽明併病。此皆因妄下而轉屬,非太陰、陽明之本症也。脾胃同處中宮,位同而職異。太陰主出,太陰病則穢腐之出不利,故腹時痛。陽明主納,陽明病則穢腐燥結而不行,故大實而痛。仍主桂枝湯者,是桂枝證未罷,不是治病求本,亦不是升舉陽邪。仲景治法,只舉目前,不拘前症。如二陽併病,太陽症罷,但潮熱汗出,大便難而詀語者,即用大承氣矣。此因表症未罷,而陽邪已陷入太陰,故倍芍藥以滋脾陰而除滿痛,此用陰和陽法也。若表邪未解,而陽邪陷入於陽明,則加大黃以潤胃燥而除其大實痛,此雙解表裏法也。凡妄下必傷胃氣,胃陽虛即陽邪襲陰,故轉屬太陰。胃液涸則兩陽相搏,故轉屬陽明。屬太陰則腹滿時痛而不實,「陰道虛」也。屬陽明則腹大實而痛,「陽道實」也。滿而時痛,下利之兆。大實而痛,是燥屎之徵。桂枝加芍藥,小試建中之劑。桂枝加大黃,微示調胃之方。 |
誤用攻下後,外證不解而出現腹滿時痛,這是太陽與太陰併病。如果大實痛,則屬於太陽與陽明併病。這些都是因為誤下所導致疾病之轉屬,而不是太陰和陽明之本證。脾胃同處於中焦,位置相同但功能不同。太陰主出,太陰病則穢濁之排出不暢,因此會腹滿時痛。陽明主納,陽明病則穢濁成燥結而無法排出,因此會大實痛。此時之所以仍然用桂枝湯,是由於桂枝湯證仍在,本方不是治病求本,亦不是升舉陽邪。仲景之治法只關注當前情況,而不拘泥於先前之證候。例如二陽併病,太陽證已罷,只是潮熱汗出、大便難和譫語者,即用大承氣湯。這裏因為表證未罷,而陽邪已經陷入於太陰,因此倍用芍藥以滋脾陰而除滿痛,這是用陰和陽之法。如果表邪未解,而陽邪陷入於陽明,則加大黃以潤胃燥而除其大實痛,這是表裏雙解法。凡誤下必然會傷及胃氣,胃陽虛則陽邪侵襲陰位,因此轉屬為太陰病。胃液乾則兩陽相搏,因此轉屬為陽明病。轉屬為太陰病則腹滿時痛而不實,這是「陰道虛」。轉屬為陽明病則腹部大實而痛,這是「陽道實」。滿而時痛,是下利之徵兆。大實而痛,則是燥屎之徵兆。桂枝加芍藥湯是小建中湯之輕劑,桂枝加大黃湯則是調胃承氣湯之輕劑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|
||
|
治傷寒吐下後,心下逆滿,氣上衝胸,起則頭眩,脉沉緊,復發汗而動經,身為振搖者。此太陽轉屬厥陰之症也。吐下後,既無下利、胃實症,是不轉屬太陰、陽明。心下又不痞硬而逆滿,是病已過太陽矣。此非寒邪自外而內結,乃肝邪自下而上達,其氣上冲心可知也。下實而上虛,故起則頭眩。脈因吐下而沉,是「沉為在裏」矣。復發汗以攻其表,經絡空虛,故一身振搖也。夫「諸緊為寒」,而指下須當深辨。浮沉俱緊者,傷寒初起之脈也。浮緊而沉不緊者,中風脈也。若下後結胸熱實而脉沉緊,便不得謂之裏寒。此吐下後熱氣上冲,更非裏寒之脈矣。緊者,弦之轉旋,「浮而緊者名弦」,是風邪外傷。此沉而緊之弦,是木邪內發。凡厥陰為病,氣上冲心。此因吐下後胃中空虛,木邪因而為患,是太陽之轉屬,而非厥陰之自病也。君以茯苓以清胷中之肺氣,則治節出而逆氣自降。用桂枝以補心血,則營氣復而經絡自和。白朮培既傷之元氣,而胃氣可復。甘草調和氣血,而營衛以和,則頭自不眩而身不振搖矣。若粗工遇之,鮮不認為真武症。 |
治療傷寒病吐下後,心下逆滿,氣上衝胸,起身則頭暈,脈沉緊,再次發汗而擾動經脈,身體振顫動搖者。這是太陽病轉屬為厥陰之證。吐下後,既沒有下利與胃實之證,這不是轉屬為太陰病和陽明病。心下又不痞硬而逆滿,說明疾病已經離開太陽病。這不是寒邪自外而內結,乃是肝邪自下而上達,因此會氣上衝心。下實而上虛,因此起身時頭暈。因為吐下後而脈沉,這就是所謂「沉為在裏」。再次發汗以攻其表,經絡空虛,所以全身振顫動搖。雖說「諸緊為寒」,但仍然需要診脈時仔細辨別。脈浮沉俱緊者,是傷寒初起之脈。脈浮緊而沉不緊者,是中風之脈。如果攻下後熱實結胸而脈沉緊,就不能稱之為裏寒。這是吐下後熱氣上衝,更不是裏寒之脈象。緊脈,是弦脈之轉旋,所謂「浮而緊者名弦」,是指風邪外傷。本證沉而緊之弦,則是木邪內發。凡是厥陰為病,則氣上衝心。這是因為吐下後胃中空虛,木邪因此而為患,是太陽病轉屬為厥陰病,而不是厥陰自身所發之病。用茯苓為君藥以清胸中之肺氣,則肺能主治節而逆氣自降。用桂枝補益心血,使營氣恢復運用而經絡自和。白朮補益已經受損之元氣,則胃氣可以恢復。甘草調和氣血,則營衛可以和諧,如此則頭不眩暈和身體不再振顫動搖。如果粗工遇到此證,很少不會認為這是真武湯證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加桂湯 |
||
|
燒鍼令其汗,鍼處被寒,核起而赤者,必發奔豚,氣從少腹上冲心者,先灸其核上各一壯,乃與此湯。寒氣外束,火邪不散,發為赤核,是將作奔豚之兆也。從少腹上冲心,是奔豚已發之象也。此因當汗不發汗,陽氣不舒,陰氣上逆,必灸其核以散寒,仍用桂枝以解外。更加桂者,補心氣以益火之陽而陰自平也。前條「發汗後,臍下悸」,是水邪乘陽虛而犯心,故君茯苓以清水之源。此表寒未解,而少腹上冲,是水邪挾陰氣以凌心,故加肉桂以溫水之主。前症已在裏而奔豚未發,此症尚在表而奔豚已發,故治有不同。桂枝不足以勝風,先刺風池、風府,復與桂枝以祛風。燒針不足以散寒,先灸其核,與桂枝加桂以散寒。皆內外夾攻法,又先治其外後治其內之理也。桂枝加芍藥,治陽邪下陷。桂枝更加桂,治陰邪上攻。只在一味中加分兩,不於本方外求他味,「不即不離」之妙如此。 |
用燒針使病者出汗,針處受寒而出現腫核發紅,必然引發奔豚,氣從小腹上衝心,先在其腫核上各灸一壯,然後給與此湯。寒邪外束,火邪不散,因此發為紅色腫核,這是將要成為奔豚之前兆。氣從小腹上衝心,則是奔豚已經發作之象。這是因為本來應該出汗而沒有發汗,陽氣不能舒展,陰氣逆而上行,必須灸其腫核以驅散寒氣,仍用桂枝以解表邪。再加肉桂,是補益心氣以補陽氣,則陰氣自然平伏。前條所述「發汗後,臍下悸」是水邪乘陽虛而犯心,因此以茯苓為君以清水氣之源。本條所論是表寒未解,而氣從少腹上衝,是水邪夾陰氣而凌心,因此加肉桂以溫水之所主。前條病在裏而奔豚尚未發作,本條是病在表而奔豚已經發作,所以治療方法不同。桂枝湯不足以驅散風邪時,可先刺風池、風府,再用桂枝湯以祛除風邪。燒針不足以驅散寒氣時,可先灸其腫核,再與桂枝湯加肉桂以散寒。這都是內外夾攻之法,是先治其外然後治其裏之治療原理。桂枝加芍藥湯,是治療陽邪下陷。桂枝加桂湯,是治療陰邪上攻。用藥只在一味藥之份量作變化,而不在本方之外去尋求其他藥物,這就是「不即不離」之妙用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|
||
|
傷寒者,寒傷君主之陽也。以火迫劫汗,并亡君主之陰,此為「火逆」矣。蓋太陽傷寒,以發汗為主,用麻黃發汗是為扶陽。用火劫汗猶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,權不由主,此汗不由心也。故驚狂而起卧不安,猶芒刺在背之狀矣。心為陽中之陽,太陽之汗,心之液也。凡發熱,自汗出者,是心液不收,桂枝方用芍藥以取之。此因迫汗,津液既亡,無液可斂,故去芍藥。加龍骨牡蠣者,是取其醎以補心,重以鎮怯,濇以固脫,故曰「救逆」也。且去芍藥之酸,則肝家得辛甘之補;加龍骨、牡蠣之醎,腎家既有既濟之力。此「虛則補母」之法,又五行承制之理矣(蜀漆未詳。昔云「常山之苗」則謬)。 |
傷寒病,就是寒邪傷及君主之陽氣。用火療法迫使汗出,同時會傷及君主之陰,這就是「火逆」。因為太陽病傷寒證以發汗為主,用麻黃湯發汗是為了扶持陽氣。而用火療法迫使汗出猶如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,失去君主之權,此時之汗出並非由心而出。因此出現驚恐狂躁而起臥不安,猶如芒刺在背之狀。心為陽中之陽,太陽病所發之汗,屬於心液所化。凡是發熱而自汗出者,屬於心液不能收斂,用桂枝湯方加芍藥來收斂心液。這是由於用火法強行發汗,津液已傷,已無陰液可以被收斂,因此在桂枝湯中去芍藥。加龍骨、牡蠣是為了利用其鹹味來補心,同時重鎮以定驚恐,味澀能固脫,因此稱之為「救逆湯」。而且去芍藥之酸,則可以使辛甘之味補養肝氣;而加龍骨、牡蠣之鹹味,則使腎能有交通心腎,使水火相濟之作用。這是「虛則補其母」之法,又體現五行承制之原理。(不清楚蜀漆這味藥。前人說是「常山之苗」是錯誤的。)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|
||
|
火逆又下之,因燒針而煩躁,即驚狂之漸也。急用桂枝、甘草以安神,加龍骨、牡蠣以救逆,比前方簡而切當。近世治傷寒者,無火熨之法,而病傷寒者,多煩躁、驚狂之變,大抵用白虎、承氣輩,作有餘治之。然此症屬實熱者固多,而屬虛寒者間有,則溫補安神之法不可廢也。更有陽盛陰虛而見此症者,當用炙甘草加減,用棗仁、遠志、茯苓、當歸等味,又不可不知。
|
火逆後又攻下,因為燒針而煩躁,就是驚狂之前期。迅速用桂枝和甘草來安神,加龍骨和牡蠣來救逆,比前面之方更加簡單而切實。近代治療傷寒病,已沒有火熨之法,而病傷寒之人,經常有煩躁、驚狂之變證,大多是用白虎湯、承氣湯等方,當作實證來治療。然而,這種證候固然有較多是屬於實熱,但亦有屬於虛寒者,則溫補安神之法不可偏廢。另外,還有陽盛陰虛而見此證者,則應使用炙甘草湯加減,用酸棗仁、遠志、茯苓、當歸等藥,這一點亦不可不知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桂枝附子湯 桂枝 附子 甘草 生姜 大棗 |
||
|
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 |
||
|
治傷寒八九日,風濕相搏,身體煩疼不能轉側,不嘔,不渴,脉浮虛而濇者。若其人大便鞕,小便自利,去桂加白朮。按:桂枝附子湯,即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也。彼治下後,脈促,胸滿而微惡寒,是病在半表,仍當是桂枝為君,加附子為佐。此風寒濕相合而相搏於表,當從「君君臣臣」之制,則桂、附並重可知。舊本兩方分兩相同,誤亦甚矣。夫脈浮為風,濇為虛,浮而濇則知寒之不去,而濕之相承也。風寒濕三氣合至,合而成痹,故身體煩疼而不能轉側,病只在表而不在內。桂枝能驅風散寒而勝濕,故重其分兩,配附子之辛熱,率甘草、姜、棗以主之,三氣自平,營衛以和矣。若其人又兼裏氣不和,大便反鞕,小便反利者,此非「胃家實」,乃脾家虛也。蓋「脾家實,腐穢當自去」,此濕流肌肉,因脾土失職,不能制水,故大便反見燥化。不嘔,不渴,是上焦之化源清,故小便自利。濡濕之地,風氣常存,故風寒相搏而不解耳。病本在脾,法當培土以勝濕,而風寒自解,故君白朮以代桂枝。白朮專主健脾。脾虛則濕勝而不運,濕流於內,故使大便不實;濕流於表,更能使大便不濡。脾健則能制水,水在內,能使下輸膀胱而大便實;水在外,能使還入胃中而大便濡。故方末云:「初服其人身如痺,三服盡,其人如冒狀。此以朮、附并走皮肉,逐水氣未得除,故使然耳」,法當加桂四兩。此本一方二法,以大便鞕,小便自利,去桂也。以大便不鞕,小便不利,當加桂。因桂枝治上焦,大便鞕,小便利,是中焦不治,故去桂。服湯已,濕反入胃,故大便不鞕。小便不利,是上焦不治,故仍須加桂。蓋小便由於上焦之氣化,而後膀胱之藏者能出也。《內經》曰:「風氣勝者為行痺,寒氣勝者為痛痺,濕氣勝者為着痺。」此身痛而不能轉側,是風少而寒濕勝,必賴附子雄壯之力,以行痺氣之着。然附子治在下焦,故必同桂枝,始能令在表之痺氣散。同白朮,又能令在表之痺氣內行。故桂枝附子湯是上下二焦之表劑,去桂加白朮湯是中下二焦之表劑,附子白朮湯仍加桂枝是通行三焦之表劑也。是又一方三法也。世以仲景方法分兩,動稱「一百一十三方,三百九十七法」,不知從何處而起?
|
治傷寒病八九日,風濕邪氣相搏,身體煩痛不能轉側,不嘔,不渴,脈浮虛而澀。如果患者大便硬,小便自利,則去桂枝加白朮。按:桂枝附子湯,即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。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是治療攻下後,脈促,胸滿而微惡寒,這是病屬於半表,仍然需要以桂枝為君藥,加附子作為輔助。本證因為風寒濕三氣相合而相搏於表,應當遵從「君君臣臣」之製方原則,如此則知桂枝和附子應該並重。舊版本中二方之份量相同,是非常錯誤的。脈浮表示有風,脈澀表示體虛,脈浮而澀則知寒邪未去,而濕氣已經來臨。風寒濕三氣相合而至,則成為痹病,因此身體煩痛而不能轉側,其病僅在於表而不在裏。桂枝能驅風散寒而除濕氣,因此重用其份量,配以辛熱之附子,率領甘草、生薑和大棗來主治此病,則三氣自然消散,營衛得以和諧。如果患者同時兼有裏氣不和,大便反硬,小便反利,這不是「胃家實」,而是脾家虛證。因為「脾家實,腐穢當自去」,這是濕邪流注於肌肉,由於脾土失職,不能制水,因此大便反而出現燥化。不嘔,不渴,是由於上焦對水液之氣化功能正常,所以小便自利。潮濕之環境中,經常有風氣存在,所以風寒二氣相搏不解。其病原本在脾,治法上應當培土以勝濕,則風寒可自然消解,因此用白朮代替桂枝作為君藥。白朮專主健脾。脾虛則濕氣盛而無法被運化,濕氣內流,所以大便不實;濕氣外流於表,則又能使大便不濕潤。脾氣健則能制水,水在內,能使其下輸膀胱則大便實;水在外,能使其回歸胃中則大便濕潤。因此本方方後注說:「初服氣人身如痺,三服盡,其人如冒狀。此以朮、附並走皮肉,逐水氣未得除,故使然耳」,治法上應當用四兩桂枝。這原本是一方二法,因為大便硬,小便自利,則去桂枝。因為大便不硬,小便不利,則應當加桂枝。因為桂枝所治在上焦,大便硬而小便利是中焦之問題,所以去桂枝。服用湯藥後,濕氣反入胃中,所以大便不硬。小便不利是上焦之問題,所以仍然需要加桂枝。因為小便是由上焦氣化水液後,膀胱所藏之津液才能排出。《內經》說:「風氣勝者為行痹,寒氣勝者為痛痹,濕氣勝者為着痹。」這裏身痛而不能轉側,反映風邪較少而寒濕較盛,必須依靠附子雄壯之力來行散留著之痹氣。然而附子所治在下焦,所以必須與桂枝一同使用,才能消散在表之痹氣。與白朮一同使用,又能使在表之痹氣消散於內。因此,桂枝附子湯是治上下兩焦之表劑,去桂加白朮湯是治中下兩焦之表劑,而附子白朮湯仍加桂枝則是通行三焦之表劑。這又體現了一方三法。世人將仲景之方和治法號稱「一百一十三方,三百九十七法」,真不知是從何談起?」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甘草附子湯 甘草 附子 白朮 桂枝 |
||
|
治風濕相搏,骨節疼痛,不得屈伸,近之則痛劇,汗出,短氣,小便不利,惡風不欲去衣,或身微腫者。此即桂枝附子湯加白朮去薑、棗者也。前症得之傷寒,有表無裏。此症因於中風,故兼見汗出,身腫之表,短氣,小便不利之裡。此《內經》所謂「風氣勝者,為行痺」之症也。然上焦之化源不清,總因在表之風濕相搏,故於前方仍重用桂枝,而少減朮、附。去薑棗者,以其短氣,而辛散濕泥之品,非所宜耳。
|
治風濕相搏,骨節疼痛,不得屈伸,近之則痛劇,汗出,短氣,小便不利,惡風不欲去衣,或身微腫者。此即桂枝附子湯加白朮去薑、棗者也。前症得之傷寒,有表無裏。此症因於中風,故兼見汗出,身腫之表,短氣,小便不利之裡。此《內經》所謂「風氣勝者,為行痺」之症也。然上焦之化源不清,總因在表之風濕相搏,故於前方仍重用桂枝,而少減朮、附。去薑棗者,以其短氣,而辛散濕泥之品,非所宜耳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大陷胸丸 大黃 芒硝 杏仁 葶藶 甘遂 |
||
|
大陷胸湯 大黃 芒硝 甘遂 |
||
|
病發於陽而反下之,邪入於胃中,與不得為汗之水氣結而不散,心中硬痛,因名「結胷」。然結胷一症,有只在太陽部分者,有并病陽明者。此或丸或湯,有輕重緩急之不同也。結在太陽部分者,身無大熱,但頭汗出,項亦強如柔痓狀,寸脉浮,関脉沉,是病在上焦。因氣之不行,致水之留結耳。夫胸中者,太陽之都會,宗氣之所主,故名「氣海」。太陽為諸陽主氣,氣為水母,氣清則水精四布,氣熱則水濁而壅瘀矣。此水結因於氣結,用杏仁之苦溫以開胸中之氣,氣降則水下矣。氣結因於熱邪,用葶藶之大寒以清氣分之熱,源清而流潔矣。水結之所,必成窠臼,甘遂之苦辛,所以直達其窠臼也。然太陽之氣化不行於胸中,則陽明之胃府亦因熱而成實,必假大黃、芒硝,小其制而為丸,和白蜜以緩之,使留戀於胷中,過一宿乃下,即解心胷之結滯,又保腸胃之無傷。此太陽裡病之下法,是以攻劑為和劑者也。其併病陽明者,因水結於胷,上焦不通則津液不下,無以潤腸胃。故五六日不大便,因而舌乾口渴,日晡潮熱,是陽明亦受病矣。心下至小腹鞕滿而痛不可近,脉沉緊者,此水邪結於心胸,而熱邪實於腸胃。用甘遂以濬太陽之水,硝黃以攻陽明之實,湯以蕩之,是為兩陽表裏之下法也。二方比大承氣更峻,治水腫、痢疾之初起者甚捷。然必視其人之壯實者施之,如平素虛弱,或病後不任攻伐者,當念「虛虛」之禍。
|
病發於陽而反下之,邪入於胃中,與不得為汗之水氣結而不散,心中硬痛,因名「結胷」。然結胷一症,有只在太陽部分者,有并病陽明者。此或丸或湯,有輕重緩急之不同也。結在太陽部分者,身無大熱,但頭汗出,項亦強如柔痓狀,寸脉浮,関脉沉,是病在上焦。因氣之不行,致水之留結耳。夫胸中者,太陽之都會,宗氣之所主,故名「氣海」。太陽為諸陽主氣,氣為水母,氣清則水精四布,氣熱則水濁而壅瘀矣。此水結因於氣結,用杏仁之苦溫以開胸中之氣,氣降則水下矣。氣結因於熱邪,用葶藶之大寒以清氣分之熱,源清而流潔矣。水結之所,必成窠臼,甘遂之苦辛,所以直達其窠臼也。然太陽之氣化不行於胸中,則陽明之胃府亦因熱而成實,必假大黃、芒硝,小其制而為丸,和白蜜以緩之,使留戀於胷中,過一宿乃下,即解心胷之結滯,又保腸胃之無傷。此太陽裡病之下法,是以攻劑為和劑者也。其併病陽明者,因水結於胷,上焦不通則津液不下,無以潤腸胃。故五六日不大便,因而舌乾口渴,日晡潮熱,是陽明亦受病矣。心下至小腹鞕滿而痛不可近,脉沉緊者,此水邪結於心胸,而熱邪實於腸胃。用甘遂以濬太陽之水,硝黃以攻陽明之實,湯以蕩之,是為兩陽表裏之下法也。二方比大承氣更峻,治水腫、痢疾之初起者甚捷。然必視其人之壯實者施之,如平素虛弱,或病後不任攻伐者,當念「虛虛」之禍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小陷胸湯 黃連 半夏 瓜婁實 |
||
|
熱入有淺深,結胷分大小。心腹硬痛,或連小腹不可按者,為大結胷。此土燥水堅,故脉亦應其象而沉緊。止在心下,不及胷腹,按之知痛不甚硬者,為小結胷。是水與熱結,凝滯成痰,留於膈上,故脉亦應其象而浮滑也。穢物據清陽之位,法當瀉心而滌痰,用黃連除心下之痞實,半夏消心下之痰結,寒溫並用,溫熱之結自平。瓜婁實色赤形圓,中含津液,法象於心,用以為君,助黃連之苦,且以滋半夏之燥,洵為除煩滌痰、開結寬胷之劑。雖同名「陷胷」,而與攻利水穀之方懸殊矣。 |
熱入有淺深,結胷分大小。心腹硬痛,或連小腹不可按者,為大結胷。此土燥水堅,故脉亦應其象而沉緊。止在心下,不及胷腹,按之知痛不甚硬者,為小結胷。是水與熱結,凝滯成痰,留於膈上,故脉亦應其象而浮滑也。穢物據清陽之位,法當瀉心而滌痰,用黃連除心下之痞實,半夏消心下之痰結,寒溫並用,溫熱之結自平。瓜婁實色赤形圓,中含津液,法象於心,用以為君,助黃連之苦,且以滋半夏之燥,洵為除煩滌痰、開結寬胷之劑。雖同名「陷胷」,而與攻利水穀之方懸殊矣。 |
|
|
大、小青龍攻太陽之表,有水火之分;大、小陷胸攻太陽之裏,有痰飲之別,不獨以輕重論也。
|
大、小青龍攻太陽之表,有水火之分;大、小陷胸攻太陽之裏,有痰飲之別,不獨以輕重論也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生姜瀉心湯 人參 甘草 黃連 黃芩 乾姜 半夏 生姜 大棗 (此小柴胡湯去柴胡加乾姜、黃連,又即黃連湯去桂易芩。) |
生薑瀉心湯 人參 甘草 黃連 黃芩 乾薑 半夏 生薑 大棗 (此方為小柴胡湯去柴胡,加乾薑和黃連,又即是黃連湯去桂枝而換上黃芩。) |
|
|
傷寒,汗出外已解,胃中不和,心下痞鞕,乾嘔食臭,脇下有水氣,腹中雷鳴下利者,是陽不足而陰乘之也。凡外感風寒而陽盛者,汗出不解,多轉屬陽明而成胃實。此心下痞鞕而下利者,病雖在胃,不是轉屬陽明。下利不因誤下,腸鳴而不滿痛,又非轉屬太陰矣。夫心為陽中太陽,則心下是太陽之宮城,而心下痞是太陽之裏也。君主之火用不宣,汗出不徹,內之水氣不得越。水氣不得散,所以痞鞕。邪熱不殺穀,故乾嘔食臭。脇下為少陽之位,太陽之陽氣不盛,少陽之相火不支,故水氣得支脇下。土虛不能制水,水氣從脇入胃,泛溢中州,故腹中雷鳴而下利也。病勢已在腹中,病根猶在心下,總因寒熱交結於內,以致胃中不和。若用熱散寒,則熱勢猖獗;用寒攻熱,則水勢橫行。法當寒熱並舉,攻補兼施以和胃氣。故用芩、連除心下之熱,乾姜散心下之痞,生姜、半夏去脇下之水,參、甘、大棗培腹中之虛。因太陽之病為在裏,故「不從標本,從乎中治」也。且芩、連之苦,必得乾姜之辛,始能散痞;人參得甘、棗之甘,協以保心。又君生姜佐半夏,全以辛散甘苦之樞,而水氣始散。名曰「瀉心」,實以安心也。 |
傷寒,汗出外已解,胃中不和,心下痞鞕,乾嘔食臭,脇下有水氣,腹中雷鳴下利者,是陽不足而陰乘之也。凡外感風寒而陽盛者,汗出不解,多轉屬陽明而成胃實。此心下痞鞕而下利者,病雖在胃,不是轉屬陽明。下利不因誤下,腸鳴而不滿痛,又非轉屬太陰矣。夫心為陽中太陽,則心下是太陽之宮城,而心下痞是太陽之裏也。君主之火用不宣,汗出不徹,內之水氣不得越。水氣不得散,所以痞鞕。邪熱不殺穀,故乾嘔食臭。脇下為少陽之位,太陽之陽氣不盛,少陽之相火不支,故水氣得支脇下。土虛不能制水,水氣從脇入胃,泛溢中州,故腹中雷鳴而下利也。病勢已在腹中,病根猶在心下,總因寒熱交結於內,以致胃中不和。若用熱散寒,則熱勢猖獗;用寒攻熱,則水勢橫行。法當寒熱並舉,攻補兼施以和胃氣。故用芩、連除心下之熱,乾姜散心下之痞,生姜、半夏去脇下之水,參、甘、大棗培腹中之虛。因太陽之病為在裏,故「不從標本,從乎中治」也。且芩、連之苦,必得乾姜之辛,始能散痞;人參得甘、棗之甘,協以保心。又君生姜佐半夏,全以辛散甘苦之樞,而水氣始散。名曰「瀉心」,實以安心也。 |
|
|
此與十棗症皆表解而裏不和,見心下痞鞕,乾嘔,下利。然後因於中風之陽邪,故外症尚有餘熱,是痞鞕下利屬於熱,故可用苦寒峻利之劑以直攻之。此因於傷寒之陰邪,故內症反有鬱逆,是痞硬下利屬於虛,故當用寒溫兼補之劑以和解之。是治病各求其本也。按:「瀉心」本名「理中黃連人參湯」,此以病在上焦,故名「瀉心」耳。世徒知膀胱為太陽之裏,熱入膀胱為「犯本」,不知心下痞鞕為「犯本」,因有「傳足不傳手」之謬。
|
此與十棗症皆表解而裏不和,見心下痞鞕,乾嘔,下利。然後因於中風之陽邪,故外症尚有餘熱,是痞鞕下利屬於熱,故可用苦寒峻利之劑以直攻之。此因於傷寒之陰邪,故內症反有鬱逆,是痞硬下利屬於虛,故當用寒溫兼補之劑以和解之。是治病各求其本也。按:「瀉心」本名「理中黃連人參湯」,此以病在上焦,故名「瀉心」耳。世徒知膀胱為太陽之裏,熱入膀胱為「犯本」,不知心下痞鞕為「犯本」,因有「傳足不傳手」之謬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甘草瀉心湯 甘草 黃連 黃芩 乾姜 半夏 大棗 |
||
|
傷寒中風,初無下症,下之,利日數十行,完穀不化,腹中雷鳴,其人胃氣素虛可知。則心下痞鞕而滿非有形之結熱,以胃中空虛,客氣上逆於胃口,故乾嘔,心煩不得安,所云「當汗不汗,其人心煩」耳。若認為實熱而復下之,則痞益甚矣。本方君甘草者,一以瀉心而除煩,一以補胃中之空虛,一以緩客氣之上逆也。倍加乾姜者,本以散中宮下藥之寒,且以行芩、連之氣而消痞鞕,佐半夏以除嘔,協甘草以和中。是甘草得位而三善備,乾姜任重而四美具矣。中虛而不用人參者,以未經發汗,熱不得越,上焦之餘邪未散,與用小柴胡湯有「胸中煩者去人參」同一例也。乾嘔而不用生姜者,以上焦之津液已虛,無庸再散耳。此病已在胃,亦不曰「理中」,仍名「瀉心」者,以心煩痞鞕,病在上焦,猶未離乎太陽也。心煩是太陽裏症,即是陽明之表症,故雖胃中空虛,完穀不化,而不用人參。因心煩是胃實之根,太陽轉屬陽明之捷路也。凡傷寒中風,下利清谷屬於寒,下利完谷屬於熱,《內經》所云「暴注下迫屬於熱」者是也。仲景之去人參,預以防胃家之實歟? 傷寒中風,初時無可攻之證,但卻被攻下,然後下利每日多達十多次,完穀不化,腹中雷鳴,可知其人胃氣本就虛弱。則此時心下痞硬而脹滿並非是有形之結熱,而是由於胃中空虛,客氣上逆於胃口,所以有乾嘔,心煩不安,即所謂「當汗不汗,其人心煩」。如果誤認為是實熱而再次進行攻下,則痞硬會更加嚴重。本方以甘草為君藥,一方面是為了瀉心除煩,另一方面是為了補胃中之虛,還有一方面是為了緩解客氣之上逆。倍用乾薑是為了溫散因為寒涼藥攻下引致之脾胃虛寒,而且能運行黃芩和黃連之氣以消除痞硬,同時能輔助半夏以止嘔,協同甘草以調和中焦。這樣,甘草在方中得其位而兼備三種作用,乾薑則擔負重任而發揮四種功用。中焦虛弱而不使用人參,是因為未經發汗,熱邪不得外越,上焦之餘邪未散,與使用小柴胡湯時有「胸中煩者去人參」屬同一情況。有乾嘔而不用生薑,是因為上焦之津液已經虛弱,無需再次散發。此病已經在胃中,但方名不稱「理中」,卻仍然稱為「瀉心」,是因為心煩痞硬之病位在上焦,仍然未離開太陽。心煩是太陽病之裏證,即為陽明病治表證,所以雖然胃中空虛,完穀不化,亦不用人參。因為心煩是胃實之根源,太陽病轉屬成為陽明病治捷徑。凡是傷寒中風,下利清穀屬於寒,而下利完穀則屬於熱,即《內經》所說「暴注下迫屬於熱」這一類。仲景之所以去人參,難道是為了預防導致胃實嗎?」 |
傷寒中風,初無下症,下之,利日數十行,完穀不化,腹中雷鳴,其人胃氣素虛可知。則心下痞鞕而滿非有形之結熱,以胃中空虛,客氣上逆於胃口,故乾嘔,心煩不得安,所云「當汗不汗,其人心煩」耳。若認為實熱而復下之,則痞益甚矣。本方君甘草者,一以瀉心而除煩,一以補胃中之空虛,一以緩客氣之上逆也。倍加乾姜者,本以散中宮下藥之寒,且以行芩、連之氣而消痞鞕,佐半夏以除嘔,協甘草以和中。是甘草得位而三善備,乾姜任重而四美具矣。中虛而不用人參者,以未經發汗,熱不得越,上焦之餘邪未散,與用小柴胡湯有「胸中煩者去人參」同一例也。乾嘔而不用生姜者,以上焦之津液已虛,無庸再散耳。此病已在胃,亦不曰「理中」,仍名「瀉心」者,以心煩痞鞕,病在上焦,猶未離乎太陽也。心煩是太陽裏症,即是陽明之表症,故雖胃中空虛,完穀不化,而不用人參。因心煩是胃實之根,太陽轉屬陽明之捷路也。凡傷寒中風,下利清谷屬於寒,下利完谷屬於熱,《內經》所云「暴注下迫屬於熱」者是也。仲景之去人參,預以防胃家之實歟? 傷寒中風,初時無可攻之證,但卻被攻下,然後下利每日多達十多次,完穀不化,腹中雷鳴,可知其人胃氣本就虛弱。則此時心下痞硬而脹滿並非是有形之結熱,而是由於胃中空虛,客氣上逆於胃口,所以有乾嘔,心煩不安,即所謂「當汗不汗,其人心煩」。如果誤認為是實熱而再次進行攻下,則痞硬會更加嚴重。本方以甘草為君藥,一方面是為了瀉心除煩,另一方面是為了補胃中之虛,還有一方面是為了緩解客氣之上逆。倍用乾薑是為了溫散因為寒涼藥攻下引致之脾胃虛寒,而且能運行黃芩和黃連之氣以消除痞硬,同時能輔助半夏以止嘔,協同甘草以調和中焦。這樣,甘草在方中得其位而兼備三種作用,乾薑則擔負重任而發揮四種功用。中焦虛弱而不使用人參,是因為未經發汗,熱邪不得外越,上焦之餘邪未散,與使用小柴胡湯時有「胸中煩者去人參」屬同一情況。有乾嘔而不用生薑,是因為上焦之津液已經虛弱,無需再次散發。此病已經在胃中,但方名不稱「理中」,卻仍然稱為「瀉心」,是因為心煩痞硬之病位在上焦,仍然未離開太陽。心煩是太陽病之裏證,即為陽明病治表證,所以雖然胃中空虛,完穀不化,亦不用人參。因為心煩是胃實之根源,太陽病轉屬成為陽明病治捷徑。凡是傷寒中風,下利清穀屬於寒,而下利完穀則屬於熱,即《內經》所說「暴注下迫屬於熱」這一類。仲景之所以去人參,難道是為了預防導致胃實嗎?」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半夏瀉心湯 半夏 乾姜 黃連 黃芩 人參 甘草 大棗 |
||
|
本論云:「嘔而發熱者,小柴胡主之。」即所云「傷寒中風,有柴胡證,但見一症即是,不必悉具」者是也。又云:「嘔多,雖有陽明證,不可攻之。」可見少陽陽明合病,闔從樞轉,故不用陽明之三承氣,當從少陽之大柴胡。「上焦得通,則津液得下」,故大柴胡為少陽陽明之下藥也。若傷寒五六日,嘔而發熱,是柴胡湯證,而以他藥下之,樞機廢弛,變症見矣。少陽居半表半裏之位,其症不全發陽,不全發陰。故下後變症偏於半表者,熱入而成結胸;偏於半裏者,熱結心下而成痞也。結胸與痞同為鞕滿之症,當以痛為辨。滿而鞕痛為結胸熱實,大陷胸下之,則痛隨利減。如滿而不痛者為虛熱痞悶,宜清火散寒而補虛,蓋瀉心湯方即小柴胡去柴胡加黃連乾姜湯也。不往來寒熱,是無半表症,故不用柴胡。痞因寒熱之氣互結而成,用黃連、乾姜之大寒大熱者,為之兩解,且取其苦先入心,辛以散邪耳。此痞本於嘔,故君以半夏。生姜能散水氣,乾姜善散寒氣。凡嘔後痞鞕,是上焦津液已乾,寒氣留滯可知,故去生姜而倍乾姜。痛本於心火內鬱,故仍用黃芩佐黃連以瀉心也。乾姜助半夏之辛,黃芩協黃連之苦,痞鞕自散。用參、甘、大棗者,調既傷之脾胃,且以壯少陽之樞也。
|
《傷寒論》說:「嘔而發熱者,小柴胡湯主之。」即所謂的「傷寒中風,有柴胡證時,但見一證即是,不必悉具」。又說:「嘔多,雖有陽明證,不可攻之。」可見少陽陽明合病時,陽明之闔從少陽之樞而轉,因此不使用陽明病之三承氣湯,而應該用少陽病之大柴胡湯。「上焦得通,則津液得下」,因此大柴胡湯是少陽陽明合病攻下之方。如果傷寒病經過五六日,嘔而發熱,此屬柴胡湯證,但卻用其他藥物攻下,樞機不能發揮作用,則會導致變證。少陽位於半表半裏之位,其病證既不完全為陽證,亦不完全為陰證。因此在攻下後,如果變證偏於半表者,則熱入而成結胸證;偏於半裏者,則熱結心下而成痞證。結胸和痞證都是硬滿之證,應當以疼痛為辨別依據。脹滿而硬痛為結胸熱實,用大陷胸湯攻下,則疼痛會隨着下利而減輕。如果脹滿而不痛,則為虛熱之痞悶,應該清火散寒並補虛,因為瀉心湯即是小柴胡湯去除柴胡加黃連乾薑湯。不寒熱往來,即無半表證,所以不用柴胡。痞證是由寒熱之氣互結而成,用黃連和乾薑之大寒、大熱藥物能兩解寒熱,並且取其味苦先入心,味辛以散邪氣。此痞證本源於嘔吐,所以以半夏為君藥。生薑能散水氣,乾薑善於散寒氣。凡是嘔吐後出現痞硬,說明上焦津液已經乾枯,而寒氣則停滯不散,所以去生薑而倍用乾薑。疼痛本於心火內鬱,所以仍然使用黃芩輔助黃連以瀉心火。乾薑輔助辛味之半夏,黃芩輔助苦味之黃連,痞硬自然消散。用人參、甘草和大棗,既能調養受損之脾胃,又能強壯少陽之樞機。
|
|
|
《內經》曰「腰以上為陽」,故三陽俱有心胸之病。仲景立瀉心湯以分治三陽,在太陽以生姜為君者,以未經誤下而心下成痞,雖汗出表解,水氣猶未散,故微寓解肌之義也。在陽明用甘草為君者,以兩番妄下,胃中空虛,其痞益甚,故倍甘草以建中,而緩客邪之上逆,是亦「從乎中治」之法也。在少陽用半夏為君者,以誤下而成痞,邪已去半表,則柴胡湯不中與之,又未全入裏,則黃芩湯亦不中與之矣。未經下而胸脇苦滿,是裏之表症,用柴胡湯解表。心下滿而胸脇不滿,是裏之半裏症,故製此湯和裏,稍變柴胡半表之治,推重少陽半裏之意耳。名曰「瀉心」,實以瀉胆也。
|
《內經》說:「腰以上屬陽」,因此,三陽病都有心胸之病。仲景設立瀉心湯以分治三陽心胸之病,治太陽之方以生薑為君藥,是因為未經誤下而導致心下痞,雖然汗出表已解,水氣尚未消散,所以用生薑亦略帶帶解肌之意。治陽明之方以甘草為君藥,是因為兩次誤下,導致胃中空虛,而心下痞更加嚴重,所以倍用甘草以健立中氣,以緩客邪之上逆,這亦是「從乎中治」之法。治少陽之方以半夏為君藥,是因為誤下而成痞,邪氣已經離開半表,所以不能用小柴胡湯,但又未完全入裏,則黃芩湯亦不適用。未經攻下而胸脅苦滿,屬於裏之表證,則可使用小柴胡湯解表。如果心下滿而胸脅不滿,屬於裏之半裏證,因此創立此方以和裏,將治半表之小柴胡湯稍作變化,重點在於治少陽之半裏。名為「瀉心湯」,實際上是用來瀉膽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大黃黃連瀉心湯 |
||
|
附子瀉心湯 附子 大黃 黃連 黃芩 |
||
|
治心下痞,按之濡,其脉関上浮者,用大黃黃連瀉心湯。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,用附子瀉心湯。此皆攻實之劑,與前三方名雖同而法不同矣。濡者,濕也。此因妄下,汗不得出,熱不得越,結於心下而成痞。胃火熾於內,故心下有汗,而按之者,知其濡濕耳。結胸症,因症發於陽1,熱邪留於上焦,故其寸脉獨浮,而但頭汗出,餘處無汗。此心下痞,因病發於陰,熱邪已畜於中焦,故其脉獨関上浮,而汗但出於心下。心下者,胃口之氣。尺寸不浮而関上獨浮,此浮為胃實外見之徵,不得責之浮為在表矣。子能令母實,故心下之痞不解,母實而兼瀉其子,是又治太陽陽明併病之一法也。云「瀉心」者,瀉其實耳。熱有虛實,客邪內陷為實,藏氣自病為虛。黃連苦燥,但能解離宮之虛火,不能除胃家之實邪。非君大黃之勇以蕩滌之,則客邪協內實而據心下者,漫無出路。故用一君一臣,以麻沸湯漬其汁,乘其銳氣而急下之,除客邪須急也。夫心下痞而大便鞕者,是熱結於中,當不惡寒而反惡寒,當心下有汗而餘處皆無汗。若惡寒已罷,因痞而復惡寒,初無汗,今痞結而反出汗,是傷寒之陰邪不得散,而兩陽之熱邪不得舒,相搏於心下而成痞也。法當佐以附子,炮用而別煮,以溫其積寒。三物生用而取汁,欲急於除熱。寒熱各製而合服之,是又於偶方中用反佐之奇法也。夫結熱不速去,必成胃家之燥實。心下痞不散,必轉成為大結胷。此二方用麻沸湯之意歟?仲景瀉心無定法,正氣奪則為虛痞,雜用甘補、辛散、苦泄、寒溫之品以和之。邪氣盛則為實痞,用大寒、大熱、大苦、大辛之味以下之。和有輕重之分,下有寒熱之別,同名「瀉心」,而命劑不同如此。然五方中諸藥味數分兩,各有進退加減,獨黃連定而不移者,以其苦先入心,中空外堅,能疏通諸藥之寒熱,故為瀉心之主劑。
|
治心下痞,按之濡,其脉関上浮者,用大黃黃連瀉心湯。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,用附子瀉心湯。此皆攻實之劑,與前三方名雖同而法不同矣。濡者,濕也。此因妄下,汗不得出,熱不得越,結於心下而成痞。胃火熾於內,故心下有汗,而按之者,知其濡濕耳。結胸症,因症發於陽 ,熱邪留於上焦,故其寸脉獨浮,而但頭汗出,餘處無汗。此心下痞,因病發於陰,熱邪已畜於中焦,故其脉獨関上浮,而汗但出於心下。心下者,胃口之氣。尺寸不浮而関上獨浮,此浮為胃實外見之徵,不得責之浮為在表矣。子能令母實,故心下之痞不解,母實而兼瀉其子,是又治太陽陽明併病之一法也。云「瀉心」者,瀉其實耳。熱有虛實,客邪內陷為實,藏氣自病為虛。黃連苦燥,但能解離宮之虛火,不能除胃家之實邪。非君大黃之勇以蕩滌之,則客邪協內實而據心下者,漫無出路。故用一君一臣,以麻沸湯漬其汁,乘其銳氣而急下之,除客邪須急也。夫心下痞而大便鞕者,是熱結於中,當不惡寒而反惡寒,當心下有汗而餘處皆無汗。若惡寒已罷,因痞而復惡寒,初無汗,今痞結而反出汗,是傷寒之陰邪不得散,而兩陽之熱邪不得舒,相搏於心下而成痞也。法當佐以附子,炮用而別煮,以溫其積寒。三物生用而取汁,欲急於除熱。寒熱各製而合服之,是又於偶方中用反佐之奇法也。夫結熱不速去,必成胃家之燥實。心下痞不散,必轉成為大結胷。此二方用麻沸湯之意歟?仲景瀉心無定法,正氣奪則為虛痞,雜用甘補、辛散、苦泄、寒溫之品以和之。邪氣盛則為實痞,用大寒、大熱、大苦、大辛之味以下之。和有輕重之分,下有寒熱之別,同名「瀉心」,而命劑不同如此。然五方中諸藥味數分兩,各有進退加減,獨黃連定而不移者,以其苦先入心,中空外堅,能疏通諸藥之寒熱,故為瀉心之主劑。
|
|
|
1 症發於陽:與後文「病發於陰」相對,當為「病發於陽」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旋覆黛1赭湯 旋覆 代赭 人參 甘草 半夏 生姜 大棗 |
||
|
傷寒發汗,若吐若下,表解後,心下痞鞕,噫氣不除者,此心氣大虛,餘邪結於心下,心氣不得降而然也。心為君主,寒為賊邪。表寒雖解而火不得位,故使閉塞不通而心下痞鞕。君主不安,故噫氣不除耳。此方乃瀉心之變劑,以心虛不可復瀉心,故去芩、連、乾姜輩苦寒辛熱之品。心為太陽,通於夏氣。旋復花開於夏,醎能補心而軟痞鞕。半夏根成於夏,辛能散結氣而止噫。二味得夏氣之全,故用之以通心氣。心本苦緩,此為賊邪傷殘之後,而反苦急,故加甘草以緩之。心本欲收,今因餘邪留結,而反欲散,故倍生姜以散之。虛氣上逆,非得金石之重為之鎮墜,則痞鞕不能遽消,而噫氣無能頓止。代赭秉南方之赤色,入通於心,堅可除痞,重可除噫,用以為佐,急治其標也。人參、大棗,補虛於餘邪未平之時,預治其本也。扶正驅邪,神自安。若用芩、連以瀉心,能保微陽之不滅哉?旋覆、半夏作湯,調代赭末,治頑痰結於胸膈,或涎沫上湧者最佳。挾虛者加人參甚効。
|
傷寒發汗,若吐若下,表解後,心下痞鞕,噫氣不除者,此心氣大虛,餘邪結於心下,心氣不得降而然也。心為君主,寒為賊邪。表寒雖解而火不得位,故使閉塞不通而心下痞鞕。君主不安,故噫氣不除耳。此方乃瀉心之變劑,以心虛不可復瀉心,故去芩、連、乾姜輩苦寒辛熱之品。心為太陽,通於夏氣。旋復花開於夏,醎能補心而軟痞鞕。半夏根成於夏,辛能散結氣而止噫。二味得夏氣之全,故用之以通心氣。心本苦緩,此為賊邪傷殘之後,而反苦急,故加甘草以緩之。心本欲收,今因餘邪留結,而反欲散,故倍生姜以散之。虛氣上逆,非得金石之重為之鎮墜,則痞鞕不能遽消,而噫氣無能頓止。代赭秉南方之赤色,入通於心,堅可除痞,重可除噫,用以為佐,急治其標也。人參、大棗,補虛於餘邪未平之時,預治其本也。扶正驅邪,神自安。若用芩、連以瀉心,能保微陽之不滅哉?旋覆、半夏作湯,調代赭末,治頑痰結於胸膈,或涎沫上湧者最佳。挾虛者加人參甚効。
|
|
|
1 黛赭:當作「代赭」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 |
||
|
治傷寒吐下後,食入口即吐。此寒邪格熱於上焦也,雖不痞鞕而病本於心,故用瀉心之半。乾姜以散上焦之寒,芩、連以清心下之熱,人參以通格逆之氣而調其寒熱以至和平。去生姜、半夏者,胃虛不堪辛散。不用甘草、大棗者,嘔不宜甘也。凡嘔家夾熱者,不利於香、砂、桔、半,服此方而晏如。妄汗後,水藥不得入口,是為「水逆」。妄吐下後,食入口即吐,是為「食格」。此肺氣、胃氣受傷之別也。入口即吐,不使少留,乃火炎上之象,故苦寒倍於辛熱。不名「瀉心」者,以瀉心湯專為痞鞕之法耳。要知寒熱相結於心下而成痞鞕,寒熱相阻於心下而成格逆,源同而流異也。
|
治傷寒吐下後,食入口即吐。此寒邪格熱於上焦也,雖不痞鞕而病本於心,故用瀉心之半。乾姜以散上焦之寒,芩、連以清心下之熱,人參以通格逆之氣而調其寒熱以至和平。去生姜、半夏者,胃虛不堪辛散。不用甘草、大棗者,嘔不宜甘也。凡嘔家夾熱者,不利於香、砂、桔、半,服此方而晏如。妄汗後,水藥不得入口,是為「水逆」。妄吐下後,食入口即吐,是為「食格」。此肺氣、胃氣受傷之別也。入口即吐,不使少留,乃火炎上之象,故苦寒倍於辛熱。不名「瀉心」者,以瀉心湯專為痞鞕之法耳。要知寒熱相結於心下而成痞鞕,寒熱相阻於心下而成格逆,源同而流異也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赤石脂禹粮餘1湯 |
||
|
下後下利不止,與理中湯而痢益甚者,是胃関不固,下焦虛脫也。夫甘、姜、參、朮可以補中宮大氣之虛,而不足以固大腸脂膏之脫。故利在下焦者,槩不得以理中之理收功矣。夫大腸之不固,仍責在胃。関門之不閉,仍責在脾。土虛不能制水,仍當補土。然芳草之氣,稟甲乙之化。土之所畏,必擇夫稟戊土之化者以培土而制水,乃克有成。石者,克2之剛也。二石皆土之精氣所結,味甘歸脾,氣冲和而性凝靜,用以固隄防而平水土,其功勝於草木耳。且石脂色赤入丙,助火以生土;餘粮色黃入戊,實胃而濇腸。用以治下焦之標,實以培中宮之本也。此症土虛而火不虛,故不宜於姜、附。本條云:「復利不止者,當利其小便。」可知與桃花湯異局矣。凡下焦虛脫者,以二物為本,參湯調服最效。
|
攻下後下利不止,服理中湯而下利加劇者,是由於胃關不固,下焦虛脫。甘草、乾薑、人參、白朮可以補益脾胃元氣之虛弱,而不足以固攝大腸脂膏之滑脫。因此,對於下焦之下利,一概不能用理中湯之理來獲取功效。大腸之不固,仍然要歸咎於胃。門戶之不閉,仍然要歸咎於脾。土虛無法制水,仍然需要補益土氣。然而,芳草之氣,稟受於甲乙之化,土氣所畏懼者,一定要選擇那些稟受戊土之化之藥物以培養土氣來制水氣,方能取效。石類藥物屬於土氣之堅固者。赤石脂與禹餘糧都是土之精氣所凝結,味甘而歸於脾,其氣沖和而其性凝靜,用來堅固堤防平息水邪犯土,其功效勝過植物藥。而且赤石脂色赤通於丙氣,能助火以生土;禹餘糧色黃通於戊氣,能補胃氣而澀腸。用來治療下焦之標,實則培養脾胃之本。本證是土虛而火不虛,所以不宜用乾薑和附子。本條提到:「再次下利不止者,應當利小便。」可知本方與桃花湯所治是不同的。凡是下焦虛脫者,以赤石脂與禹餘糧為基礎,再用人參湯調服效果最佳。 |
|
|
1 根據宋本《傷寒論》,原方應為赤石脂禹餘糧湯 |
||
|
2 克之剛:根據前文「土之所畏」,「克之剛」應為「土之剛」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抵當湯丸 水蛭 大黃 蝱虫 桃仁 |
||
|
太陽病六七日,而表症仍在,陽氣重可知。脉當大而反微,當浮而反沉。沉為在裏,當作結胸之症,反不結胸,是病不在上焦。諸微無陽,而其人反發狂者,是病不在氣分矣。凡陽病者,上行極而下,是熱在下焦可知。下焦不治,少腹鞕滿,是熱結於膀胱,當有癃閉之患。而小便反利者,是上焦肺家之氣化行,經絡之營氣不利也。人知內熱則小便不通,此熱結膀胱,而小便反利,當知小便由肺氣矣。凡陽盛者陰必虛,氣勝者血必病。瘀熱內結於膀胱,營血必外溢於經絡。營氣傷,故脉微而沉。瘀血畜,故少腹鞕滿。血瘀不行,心不得主,肝無所藏,神魂不安,故發狂。或身黃而脉沉結者,皆由營氣不舒故也。只以小便之自利決之,則病在血分而不謬矣。夫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,營氣不流則五藏不通而死可立待。岐伯曰:「血清氣濇,疾瀉之,則氣竭焉。血濁氣濇,疾瀉之,則經可通也。」非得至峻之劑,不足以抵其巢穴而當此重任矣。水蛭,昆虫之巧於飲血者也。蝱,飛虫之猛於吮血者也。茲取水陸之善取血者攻之,同氣相求耳。更佐桃仁之推陳致新,大黃之苦寒以盪滌邪熱,名之曰「抵當」者,謂直抵其當攻之所也。若雖熱而未狂,小腹滿而未鞕,宜小其制,為丸以緩治之。若外証已解,少腹結急而滿,人如狂者,是轉屬陽明也,用桃仁、桂枝於調胃承氣湯中以微利之,胃和則愈矣。或問:血得熱則行,此何以反結?膀胱熱則小便不通,此何以反利乎?答曰:衝脉為血海,而位居少腹之上,膀胱居小腹之極底。膀胱熱而血多,則血自下而不畜。膀胱熱而血少,則血凝而結於少腹矣。水入於胃,上輸脾肺,下輸膀胱。膀胱為州都之官,全藉脾肺氣化而津液得出。此熱在下焦,上中二焦之氣化不病,故小便自利也。膀胱不利為癃,由太陰之不固;不約為遺溺,由太陰之不攝。仲景製大青龍、大柴胡、白虎湯,治三陽無形之熱結。三承氣之熱實,是糟粕為患。桃仁、抵當之實結,是畜血為眚。在有形中又有氣血之分也。凡仲景用硝、黃,是蕩熱除穢,不是除血。後人專以氣分、血分對講,誤認糟粕為血,竟推大黃為血分藥。不知大黃之芳香,所以開脾氣而去腐穢,故方名「承氣」耳。若不加桃仁,豈能破血?非加蛭、蝱,何以攻堅?是血劑中又分輕重也。凡癥瘕不散,久而成形者,皆畜血所致。今人不求其屬而治之,反用三稜等氣分之藥,重傷元氣。元氣日衰,邪氣易結。盖謂糟粕因氣行而除,瘀血因氣傷而反堅也。明知此理,則用抵當丸,得治癥瘕及追蟲攻毒之效。 |
太陽病六七日,而表證仍在,可知陽邪旺盛。脈應大而反微,脈應浮而反沉。脈沉為病在裏,應當成為結胸證,而反不結胸,是病不在上焦。各種微脈屬於陽氣不足,而患者反而發狂,是病不在氣分。凡是陽病,陽熱上行極至時則流於下,由此可知熱在下焦。下焦失常而出現少腹硬滿,使熱結於膀胱,應當會有癃閉之患。而小便反而通暢,是上焦肺氣之氣化正常,而經絡之營氣不暢通。大家都知道內熱則小便不通,這是熱結膀胱,而小便反而通暢,應該知道小便是源於肺氣之氣化。凡陽盛者陰氣必虛,氣勝者血必病。瘀血內結於膀胱,營血必然外溢於經絡。營氣受損,所以脈微而沉。瘀血積聚,所以少腹硬滿。血瘀而不行,心無所主,肝無所藏,神魂不安,所以發狂。或者身黃而脈沉結者,都是由於營氣不舒暢所致。臨床上只憑小便自利來判斷,就可以確定病在血分是不會錯的。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,營氣不流暢則五臟之氣不暢通,就會很快死亡。岐伯說:「血清氣澀,迅速用瀉法,則氣竭於此。血濁氣澀,迅速用瀉法,則經脈之氣可得通暢。」除非使用極其峻猛之劑,否則不足以抵達病之巢穴而能擔當此重任。水蛭是昆蟲中善於吸血者,虻蟲是飛蟲中吸血能手。現在選用水陸中善於吸血者來攻逐邪氣,為同氣相求。再輔以桃仁之推陳致新,大黃之苦寒用來蕩滌邪熱,將其命名為「抵當」,是指其能直達應當攻擊之部位。如果雖然有熱而尚未發狂,小腹滿但未硬,則應該減輕藥力,製成丸劑而緩治之。如果外證已解,少腹結急而滿,其人如狂者,是已經轉屬為陽明病,在調胃承氣湯中加桃仁、桂枝微微通下,使胃氣和則愈。有人問:血得熱則流動,為什麼在此會出現結聚?膀胱有熱則小便不通,為什麼在此反而小便自利呢?答:衝脈為血海,位於少腹之上,而膀胱位於小腹最底部。如果膀胱有熱而血多,則血自然會下行而不停留。如果膀胱有熱而血少,則血會凝結並積聚於少腹。水入於胃後,上輸於脾與肺,然後下輸膀胱。膀胱為州都之官,全賴脾肺之氣化而津液得以外出。這是熱在下焦,上中兩焦之氣化正常,因此小便自利。膀胱氣化不利則為癃閉,是因為太陰之氣不固;膀胱之氣不能約束則為遺尿,是因為太陰之氣不攝。仲景製大青龍湯、大柴胡湯、白虎湯三方,用於治療三陽無形之熱結。三承氣湯所治之熱實是糟粕為患。而桃仁承氣湯和抵當湯所治之實結則是蓄血為患。這是在有形病證中又有氣血之分。凡是仲景用芒硝、大黃,是為了蕩滌熱邪和祛除穢邪,而不是為了祛瘀。後人專門將氣分和血分作對應,誤認糟粕為瘀血,竟然將大黃推崇為血分藥。卻不知道大黃之芳香,可以啟動脾氣而祛除腐敗之物,所以方名被稱為「承氣」。如果不加桃仁,哪裏能夠破血呢?如果不加水蛭和虻蟲,哪裏能夠攻堅呢?這是治血方中亦有輕重之分。凡是癥瘕不散,久而成形者,都是蓄血所致。今人不求其因果而進行治療,反而用三棱等氣分之藥,嚴重損傷元氣。元氣日漸衰弱,邪氣更易於積聚。因為糟粕可以因氣行而排出,而瘀血卻因元氣受傷而變得堅固。明白了這個道理,則使用抵當丸就可以治療癥瘕和蟲毒證而取效。 |
|
|
按:水蛭賦體最柔,秉性最險,暗竊人血而人不知。若飲水而誤吞之,留戀胃中,消耗血液,腹中或痛或不痛,令人黃瘦而死。觀牛肚中有此者必瘦,可類推矣。蝱蟲之體,能高飛而遠舉,專吮牛血,其形氣猛於蒼蠅。觀蒼蠅取人血汗最痛,誤食入胃,即刻腹痛,必瀉出而後止。可知飛蟲為陽屬,專取營分之血,不肯停留胃中,與昆蟲之陰毒不同也。仲景取蝱、蛭同用,使蛭亦不得停留胃中,且更有大黃以蕩滌之,毒物與畜血俱去而無遺禍。然二物以毒攻毒者也,若非邪氣固結,元氣不虛者,二物不可輕用矣。 |
按:水蛭之體稟賦最柔軟,而其稟性最為兇險,偷偷地吸食人體之血而人不知曉。如果飲水中而誤吞入體內,水蛭會停留在胃中,消耗血液,導致腹痛或不疼痛,使人變得黃瘦並最終死亡。觀察牛胃中有水蛭者必然消瘦,就可以類推了。虻蟲則可以高飛遠行,專門吸取牛血,其形氣比蒼蠅兇猛。觀察蒼蠅吸人之血汗最痛,如果不小心吞入胃中,立刻會腹痛,必然要排出體外後方能痛止。可見飛蟲屬陽,專取營分之血,不願停留在胃中,與昆蟲之陰毒不同。仲景同用虻蟲和水蛭同用,使水蛭不得停留在胃中,並且用大黃以蕩滌胃腸,使毒物和蓄血都被除去而不留禍害。然而,用虻蟲和水蛭都是以毒攻毒,除非邪氣固結,元氣不虛者,否則不可輕易使用。 |
|
|
右共四十六方,其桂枝加葛根、葛根加半夏等,最為易曉,故不具論。如四逆、真武等劑,乃太陽所借用,其方論各歸本位,經論列于後。 |
前面共有四十六首方,其中桂枝加葛根湯、葛根加半夏湯等方,最容易為人知曉,所以不作具體論述。如四逆湯、真武湯等方則是太陽病中所借用的,其方論各自歸屬於其原本之章節,在後面會作論述。 |
|
|
傷寒附翼卷之上終 |
《傷寒附翼》卷上結束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傷寒附翼卷之下 |
||
|
慈谿 柯琴 韻伯編 |
||
|
崑山 馬中驊驤北較 |
||
|
陽明方總論 |
||
|
陽明之病在胃實,當以下為正法矣。然陽明居中,諸病咸臻,故治法悉具。如多汗、無汗,分麻黃、桂枝。在胸、在腹,分瓜蒂、梔豉。初鞕、燥堅,分大、小承氣。即用汗吐下三法,亦有輕重淺深之不同也。若大煩、大渴而用白虎,瘀血、發黃而用茵陳,小便不利而用猪苓,停飲不散而用五苓,食穀欲吐而用茱萸等法,莫不各有差等。以碁喻之,發汗是「先着」,湧吐是「要着」,清火是「穩着」,利水是「閒着」,溫補是「忿着」,攻下是「末着」。病至於攻下,無別着矣。故汗之得法,他着都不必用。其用吐法,雖是「奇着」,已是第二手矣。他着都非「正着」,惟攻下為「煞着」,亦因從前之失着也。然諸法皆因清火而設,則清火是陽明之「上着」與。
|
陽明之病在於胃實,應以下法為正治法。然而陽明居中,各種疾病均可到來,因此治療方法全面具備。例如,多汗或無汗,可分為麻黃湯證和桂枝湯證。病在胸部或腹部,可分為瓜蒂散證和梔子豉湯證。大便初硬或燥堅,可分為大、小承氣湯證。即使用汗吐下三法,亦有輕重淺深之差別。如果大煩、大渴則用白虎湯,瘀血、發黃則用茵陳蒿湯,小便不利則用豬苓湯,停飲不散則用五苓散,食穀欲嘔則用吳茱萸湯等方法,無一不有其特點。以下象棋來比喻,發汗是「先着」,湧吐是「要着」,清火是「穩着」,利水是「閑着」,溫補是「奮着」,攻下是「末着」。疾病達到需要攻下時,就沒有別的棋着可用了。因此,發汗得當,就不需要其他棋着。雖然用吐法是「奇着」,但已經是第二手了。其他的棋着都不是「正着」,只有攻下是「煞着」,亦是由於之前失誤所致。然而,各種治法都是基於清火而設立,因此清火是治療陽明病之「上着」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梔子豆豉湯 梔子甘草豆豉湯 |
||
|
梔子生姜豆豉湯 梔子厚朴湯 梔子 厚朴 枳實 |
||
|
梔子乾姜湯 梔子柏皮湯 梔子 蘖皮 甘草 |
||
|
此陽明半表裡湧泄之和劑也。少陽之半表是寒,半裡是熱。而陽明之熱自內達外,有熱無寒。故其外症身熱、汗出、不惡寒、反惡熱、身重,或目痛、鼻乾、不得眠。其內症咽燥、口苦、舌胎、煩躁、渴欲飲水、心中懊憹、腹滿而喘。此熱半在表半在裏也。脈雖浮緊,不得為太陽病,非汗劑所宜。又病在胸腹而未入胃府,則不當下,法當湧泄以散其邪。梔子苦能泄熱,寒能勝熱,其形象心,又赤色通心,故主治心中上下一切症。豆形象腎,又黑色入腎,製而為豉,輕浮上行,能使心腹之濁邪上出於口,一吐而心腹得舒,表裡之煩熱悉除矣。所以然者,「二陽之病發心脾」,已上諸症是心熱不是胃家熱,即本論所云「有熱屬臟者攻之,不令發汗」之謂也。若夫熱傷氣者少氣,加甘草以益氣,虛熱相搏者多嘔,加生姜以散邪,此可為夾虛者立法也。若素有宿食者,加枳實以降之。地道不通者,加大黃以潤之,此可為實熱者立法也。叔和用以治太陽差後勞復之症,誤甚矣。如妄下後而心煩、腹滿、起臥不安者,是熱已入胃,便不當吐,故去香豉。心熱未解,不宜更下,故只用梔子以除煩,佐枳、朴以泄滿。此兩解心腹之妙,是小承氣之變局也。或以丸藥下之,心中微煩,外熱不去,是知寒氣留中而上焦留熱,故任梔子以除煩,用乾姜逐內寒以散表熱,此甘草瀉心之化方也。若因於傷寒而肌肉發黃者,是寒邪已解而熱不得越,當兩解表裡之熱。故用梔子以除內煩,柏皮以散外熱,佐甘草以和之,是又茵陳湯之輕劑矣。此皆梔豉湯加減以禦陽明表症之變幻者。夫梔子之性,能屈曲下行,不是上湧之劑。惟豉之腐氣上熏心肺,能令人吐耳。觀瓜蒂散必用豉汁和服,是吐在豉而不在梔矣。觀梔子乾姜湯去豉用姜,是取其橫散,梔子厚朴湯以枳、朴易豉,是取其下泄,皆不欲「上越」之義。舊本二方後俱云「得吐止後服」,豈不謬哉?觀梔子柏皮湯與茵陳湯,方中俱有梔子,俱不言「吐」,又「病人舊微溏者,不可與」,則梔子之性自明矣。 |
這是陽明病半表半裏湧吐之和劑。少陽病之半表屬寒,半裏屬熱。而陽明病之熱是從內部向外擴散,有熱無寒。因此其外證為身熱、汗出、不惡寒、反惡熱、身體沉重,或見目痛、鼻乾、不得眠等。內證為咽燥、口苦、舌上有苔、煩躁、渴欲飲水、心中懊憹、腹滿而喘。此熱在半表半裏。脈雖浮緊,但不可認為是太陽病,不適合用發汗劑。病又在胸腹而未入胃腑,則不應該攻下,治法上應湧吐以驅散邪氣。梔子之苦能泄熱,寒能清熱,其形狀像心,又色赤而通於心,所以主治心中上下之一切病證。豆子形狀像腎,又色黑而通於腎,經過加工成豆豉,具有輕浮上行之性,能使心腹之濁邪上出於口,一經吐出而心腹得舒,表裏之煩熱悉除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為「二陽之病發心脾」,以上諸證是心熱而不是胃熱,即《傷寒論》所說「有熱屬於臟者攻之,不令發汗」。如果熱傷氣而少氣,加甘草以益氣,如果虛熱相搏而多嘔,加生薑以散邪,此法可以為夾虛之證立法。如果素有宿食者,加枳實以通降。如果大便不通,加大黃以潤下,此法可以為實熱之證立法。王叔和用來治療太陽病「瘥後勞復證」,是嚴重錯誤的。如果妄下後而心煩、腹滿、起臥不安者,是熱邪已入於胃,此時便不應該吐,因此去香豉。如果心熱未解,不宜再用下法,所以只用梔子以除煩,輔以枳實和厚朴以泄滿。這是兩解心腹之妙法,屬於小承氣湯之變化。或者因為用丸劑攻下,心中微煩,外熱未除,這是寒氣留於中焦而上焦依然有熱邪,因此用梔子以除煩,用乾薑驅散內寒以宣發表熱,這是甘草瀉心湯之變方。如果因為傷寒而肌肉發黃,這是寒邪已解而熱邪不得外越,應該兩解表裏之熱。因此用梔子以除內煩,用柏皮以散外熱,輔以甘草調和,這又是茵陳蒿湯之輕劑。這些都是梔豉湯之加減以應對陽明病表證之變化。梔子之性能屈曲向下,不是上湧之藥。只有豆豉之腐氣上升薰蒸心肺,從而引發嘔吐。看看瓜蒂散必須用豉汁調和服用,就知道湧吐作用在於豆豉而不在梔子。看看梔子乾薑湯去豆豉而用乾薑,是取乾薑橫散之性,梔子厚朴湯用枳實和厚朴來代替豆豉,是取其下泄之功,都不是想達到「上越」之目的。舊本《傷寒論》在此兩方後都說「得吐,止後服」,難道不是錯誤嗎?看看梔子柏皮湯和茵陳蒿湯兩方中都含有梔子,都不說「吐」,而且「病人舊微溏者,不可與」,那麼梔子之性質就自然明確了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瓜蒂散 瓜蒂 赤小豆 香豉 |
||
|
此陽明湧泄之峻劑,治邪結於胸中者也。胸中為清虛之府,三陽所受氣,營衛所由行。寒邪凝結於此,胃氣不得上升,內熱不得外達,以致痞鞕。其氣上冲咽喉不得息者,此寒格於上也。寸脉微浮,寒束於外也。此寒不在營衛,非汗法所能治。因得酸苦湧泄之品,因而越之,上焦得通,中氣得達,胸中之陽氣復,肺氣之治節行,痞鞕可得而消也。瓜蒂色青,象東方甲木之化,得春升生發之機,能提胃中陽氣以除胸中之寒熱,為吐劑中第一品。然其性走而不守,與梔子之守而不走者異,故必得穀氣以和之。赤小豆形色象心,甘酸可以保心氣。黑豆形色象腎,性本沉重,黴熟而使輕浮,能令腎家之精氣交於心,胃中之濁氣出於口。作為稀糜調服二味,雖快吐而不傷神,奏功之捷,勝於汗下矣。前方以梔子配豉,此方以赤豆配豉,皆以形色取其心腎合交之義。若夫「心中溫溫欲吐復不吐,始得之,手足寒,脈弦遲」者,以不腹滿,不得為太陰病。但以欲寐而知其為少陰病,不在上焦而在胸中,亦有可吐之理矣。夫病在少陰,當補無瀉,而亦有可吐、可下之法者,以其實也。實在胸中可吐,實在胃府當下,此皆少陰陽明合併之病,是吐下二法,仍屬陽明也。如「病人手足厥冷,脈乍緊,心下滿而煩,飢不能食」者,是厥陰陽明合病。病本發於厥陰,而實邪結於陽位,急則治其標,亦當從陽明湧吐之法矣。餘義見製方大法。
|
這是陽明病湧吐之峻劑,用於治療邪氣聚集在胸中。胸中為清虛之所,三陽受氣於此,營衛之氣由此開始運行。寒邪凝結在此,則胃氣無法上升,內熱無法外達,以致痞硬。其氣上衝至咽喉以致無法呼吸,這是寒邪格拒於上焦。寸脈微浮,是寒氣束縛在外。此寒不在營衛,不是汗法所能治。因此用酸苦湧泄之藥使之上越,使上焦通暢,中氣得以通達,胸中之陽氣恢復,肺氣能行治節之功,則痞硬可以消散。瓜蒂之色青,有如東方甲木之化,得春天升發之機,能提升胃中之陽氣以除胸中之寒熱,是涌吐藥中之第一品。然而,瓜蒂之性走而不守,與梔子之守而不走不同,因此必須要有水穀之氣來調和。赤小豆之形狀和顏色與心相類,甘酸之味可以保護心氣。黑豆之形狀和顏色與腎相類,質地沉重,經過發酵後變得輕浮,能使腎之精氣與心氣相交,胃中之濁氣排出於口。將淡豆豉煮爛來調服此二味藥,雖然迅速使人湧吐但不會傷及正氣,功效比發汗、攻下更快。前方用梔子配豆豉,此方用赤小豆配豆豉,都是根據其形狀及顏色而取心腎相交之理。至於「心中溫溫欲吐復不吐,始得之,手足寒,脈弦遲」者,由於沒有腹滿,不屬於太陰病。只是因為欲寐而知其為少陰病,病變不在上焦而在胸中,亦是有可吐之理。病在少陰,應該補而不能瀉,但亦有可吐、可下之法,這是因為其病機屬實。實證在胸中可吐,實證在胃腑則應該攻下,這是少陰陽明合併之病,所以吐下二法仍然屬於陽明病。如果「病人手足厥冷,脈乍緊,心下滿而煩,饑不能食」者,是厥陰陽明合病。疾病原本發於厥陰,而實邪則結在陽位,急則治其標,所以亦應從陽明病湧吐之法進行治療。其餘之醫理參見《製方大法》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甘草乾姜湯 |
||
|
芍藥甘草湯 |
||
|
二方為陽明半表半裏症,悞服桂枝之變症而設也。桂枝湯本為中風自汗而設,若陽明病汗出多、微惡寒而無裏症者,為表未解,故可用桂枝湯發汗。其脈遲,猶中風之緩,與「脈浮而弱」者同義。若但浮之脈,在太陽必無汗,在陽明必盜汗出,則傷寒之脈浮而自汗出者,是陽明之熱淫於內,而非太陽之「浮為在表」矣。心煩是邪中於膺,心脈絡小腸,心煩則小腸亦熱,故小便數。微惡寒而腳攣急,知惡寒將自罷,趺陽脈因熱甚而血虛筋急,故腳攣也。此病在半表半裏,服梔豉湯而可愈。反用桂枝攻表,汗多所以亡陽。胃脘之陽不至於四肢,故厥。虛陽不歸其部,故咽中乾、嘔吐逆而煩躁也。勢不得不用「熱因熱用」之法,救桂枝之誤以回陽。然陽亡實因於陰虛而無所附,又不得不用益津斂血之法以滋陰。故與甘草乾姜湯而厥愈,更與芍藥甘草湯腳伸矣。且芍藥酸寒,可以止煩,斂自汗而利小便。甘草甘平,可以解煩、和肝血而緩筋急,是又內調以解外之一法也。 |
此兩方是用於治療陽明病半表半裏證,是為了應對誤服桂枝湯引起之變證而設。桂枝湯本來是為中風自汗而設,如果陽明病出現汗多、微惡寒而沒有裏證,是表證尚未解除,所以可以用桂枝湯發汗。陽明病脈遲,猶如中風證之脈緩,與「脈浮而弱」同義。如果只是浮脈,在太陽病必然無汗,在陽明病必然盜汗,那麼傷寒之脈浮而自汗出者,是陽明之熱邪內盛,而非太陽病之「浮為在表」。心煩是邪氣犯於胸,心脈絡屬於小腸,心煩則小腸亦熱,所以小便頻數。微惡寒而腳抽急,可知惡寒即將消失,趺陽脈因熱甚而血虛筋急,所以腳攣急。此病在半表半裏,服梔子豉湯即可治愈。反而用桂枝湯治表,汗出多所以亡陽。胃脘之陽氣不能到達四肢,所以厥冷。虛陽無法回歸原來之位,所以咽中乾、嘔吐而煩躁。這種情況不得不用「熱因熱用」之法來回陽以救治因誤用桂枝湯所致之亡陽。然而亡陽實際上是因為陰虛而陽氣無所依附,又不得不用益津斂血之法以滋陰。所以給予甘草乾薑湯而厥冷可愈,又給予芍藥甘草湯則腳能伸直。而且芍藥酸寒,可以止煩,能收斂自汗而利小便。甘草甘平,可以解煩、和肝血而緩解筋脈之急,這又是一種調內以解除外邪之方法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白虎加人參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人參 |
||
|
外邪初解,結熱在裏,表裏俱熱,脈洪大、汗大出、大煩、大渴欲飲水數升者,是陽明無形之熱。此方乃清肅氣分之劑也。蓋胃中糟粕燥結,宜苦寒壯水以奪土。若胃口清氣受傷,宜甘寒瀉火而護金。要知承氣之品,直行而下泄。如胃家未實而下之,津液先亡,反從火化。故妄下之後,往往反致胃實之眚,《內經》所謂「味過於苦,脾氣不濡,胃氣反厚」者是已,法當助脾家之濕土以制胃家燥火之上炎。《經》曰「甘先入脾。」又曰:「以甘瀉脾。」又曰:「脾氣散津,上歸於肺。」是甘寒之品乃土中瀉火而生津液之上劑也。石膏大寒,寒能勝熱,味甘歸脾,性沉而主降,已備秋金之體,色白通肺,質重而含津,已具生水之用。知母氣寒主降,味辛能潤,泄肺火而潤腎燥,滋肺金生水之源。甘草土中瀉火,緩寒藥之寒,用為舟楫,沉降之性始得留連於胃。粳米稼穡作甘,培形氣而生津血,用以奠安中宮,陰寒之品,無傷脾損胃之慮矣。「飲入於胃,輸脾歸肺,水精四布」,煩渴可除也。更加人參者,以氣為水母,「邪之所湊,其氣必虛」,陰虛則無氣,此大寒劑中必得人參之力以大補真陰,陰氣復而津液自生也。若壯盛之人,元氣未傷,津液未竭,不大渴者,只須滋陰以抑陽,不必加參而益氣。若元氣已虧者,但用純陰之劑,火去而氣無由生,惟加人參,則火瀉而土不傷,又使金能得氣,斯立法之盡善歟!此方重在煩渴,是熱已入裏。若傷寒脈浮、發熱、無汗、惡寒,表不解者,不可與。若不惡寒而渴者,雖表未全解,如背微惡寒、時惡風者,亦用之。若無汗、煩渴而表不解者,是麻黃杏子甘草石膏症。若小便不利、發熱而渴欲飲水者,又五苓、猪苓之症矣。若太陽、陽明之瘧,熱多寒少、口燥舌乾、脈洪大者,雖不得汗,用之反汗出而解。陶氏以立夏後、立秋前,天時不熱為拘,悞人最甚。烏知方因症立,非為時用藥也。 |
外邪初解,結熱在裏,表裏俱熱,脈洪大、大汗出、大煩、大渴欲水數升者,這是陽明無形熱邪。此方乃清肅氣分之劑。因為胃中有糟粕燥結,應採用苦寒壯水之法以奪土氣之實。如果只是胃之清氣受傷,則應採用甘寒瀉火而養護肺氣。關鍵要知道承氣湯這類方劑能直接下行而泄熱。如果胃家未實而攻下,津液先亡,反從火化。所以誤下之後,往往反而導致胃實之病變,即《內經》所謂「味過於苦,脾氣不濡,胃氣反厚」,治法上應該輔助脾家之濕土以制約胃家燥熱之上炎。《內經》說:「甘先入脾。」又說:「以甘瀉脾。」又說:「脾氣散津,上歸於肺。」所以甘寒之品乃是土中瀉火而生津液之上好藥物。石膏大寒,寒能清熱,味甘入脾,質地沉重而主降,已經具有秋金之體,色白通於肺,質重而含有津液,已經具備生化水液之功。知母性寒而主降,味辛能潤,清泄肺火而滋潤腎燥,滋養肺金生水之源。甘草能於土中瀉火,緩和寒藥之寒性,用作舟楫,可以使具有沉降之性之藥物留連於胃中。粳米作為穀物而有甘味,能培養形氣而化生津血,用來補益中焦,則不用擔心陰寒之藥會傷及脾胃。「飲入於胃,輸脾歸肺,水精四布」,則可消除煩渴。再加人參,是因為氣為水之母,「邪之所湊,其氣必虛」,陰虛則無氣,這就是為什麼大寒之劑中必須要有人參之力以大補真陰,陰氣恢復則津液能自然生化。對於體質強盛,元氣未受損傷,津液未竭而不大渴之人而言,只需要滋養陰液以抑制陽氣,不必加人參而益氣。對於元氣已虛之人,如果只用純陰之劑,火氣去則氣失其生化之本,只有加人參,才能在瀉火之後而土氣不傷,又能補益肺氣,這才是立法之盡善啊!此方治療之重點在於煩渴,這是熱已入裏。如果是傷寒脈浮、發熱、無汗、惡寒而表未解者,不可用此方。如果不惡寒而口渴,即使表證未完全解除,例如背微惡寒、時時惡風,亦可以用此方。如果無汗、煩渴而表證未解,那是屬於麻黃杏仁甘草石膏證。如果小便不利、發熱而渴欲喝水者,那是屬於五苓散、豬苓湯證。如果是太陽病、陽明病之瘧疾,熱多寒少,口燥舌乾、脈洪大者,雖然未有汗出,用此方反而能汗出而癒。陶氏受到立夏後到立秋前,天氣不是那麼炎熱時則不可用白虎湯之說束縛,最能誤導人。他哪裏知道方劑是根據證候而立,不應根據季節來用的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竹葉石膏湯 竹葉 石膏 人參 甘草 半夏 麥冬 粳米 |
||
|
此加減人參白虎湯也。三陽合病,脈浮大,在関上,但欲睡而不得眠,合目則汗出,宜此主之。若用於傷寒解後,虛羸少氣、氣逆欲吐者,則謬之甚矣。三陽合病者,頭項痛而胃家實,口苦、咽乾、目眩者是也。夫脈浮為陽,大為陽,是三陽合病之常脈。今在関上,病機在肝胃兩部矣。凡胃不和則臥不安,如肝火旺則上走空竅,亦不得睡。夫腎主五液,入心為汗,「血之與汗,異名同類」,是汗即血也。心主血而肝藏血,「人臥則血歸於肝」。目合即汗出者,肝有相火,竅閉則火無從泄,血不得歸肝,心不得主血,故發而為汗。此汗不由心,故名之為「盜汗」耳。此為肝眚,故用竹葉為引導,以其秉東方之青色,入通於肝,大寒之氣足以瀉肝家之火。用麥冬佐人參以通血脈,佐白虎以回津,所以止盜汗耳。半夏稟一陰之氣,能通行陰之道,其味辛,能散陽蹺之滿,用以引衛氣從陽入陰,陰陽通,其臥立至,其汗自止矣。其去知母者何?三陽合病而遺尿,是肺氣不收,致少陰之津不升,故藉知母以上滋手太陰,知母外皮毛而內白潤,肺之潤藥也。此三陽合病而盜汗出,是肝火不寧,令少陰之精妄泄,既不可復濡少陰之津,又不可再泄皮毛之澤,故用麥冬以代之歟! |
此方是加減白虎加人參湯。三陽合病,關脈浮大,只想睡卻不得眠,閉上眼睛就出汗,適宜用此方主治。如果用於傷寒解後,虛羸少氣、氣逆欲吐,那就是嚴重錯誤。三陽合病者,就是頭項痛而胃家實,口苦、咽乾、目眩。浮脈為陽脈,大脈亦是陽脈,這是三陽合病常見之脈象。如今浮大之脈關上,病機在肝胃兩部。大凡胃不和則臥不安,如果肝火旺上衝清竅,亦無法使人入睡。腎主五液,入心則為汗,「血之與汗,異名同類」,則汗即是血。心主血而肝藏血,「人臥則血歸於肝」。合上眼睛則出汗,表示肝有相火,清竅閉塞則火無法宣泄,血不得歸於肝,心不得主血,所以外發而為汗。這種汗不是由心而出,所以稱之為「盜汗」。這是肝之病變,所以用竹葉為引導,因為它具有東方之青色,能夠入通於肝,其大寒之氣足以清瀉肝火。用麥冬輔助人參以通利血脈,以輔佐白虎湯回復津液,這是為了止盜汗。半夏具有一陰之氣,能通行陰氣之道,其味辛,能散陽蹺脈之壅滯,用來引導衛氣從陽入陰,陰陽相通,則立刻能使人入睡,盜汗自然停止。為什麼從白虎湯中去知母?三陽合病而遺尿,表示肺氣不收,從而導致少陰之津液無法上升,所以籍用知母來滋養手太陰,知母外皮有毛而內部白潤,是潤肺之藥。這裏三陽合病而盜汗出,是肝火不寧,導致少陰之精氣妄泄,此時既不能滋養少陰之津液,又不可再外泄皮毛之津液,所以用麥冬來代替知母罷了!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茵陳蒿湯 茵陳 梔子 大黃 |
||
|
太陽、陽明俱有發黃症。但頭汗而身無汗,則熱不外越;小便不利,則熱不下泄,故瘀熱在裏而渴飲水漿。然黃有不同,症在太陽之表,當汗而發之,故用麻黃連翹赤豆湯,為涼散法。症在太陽、陽明之間,當以寒勝之,用梔子柏皮湯,乃清火法。症在陽明之裏,當瀉之於內,故立本方,是逐穢法。茵陳秉北方之色、經冬不凋,傲霜凌雪,歷遍冬寒之氣,故能除熱邪留結。佐梔子以通水源,大黃以除胃熱,令瘀熱從小便而泄,腹滿自減,腸胃無傷,仍合「引而竭之」之義,亦陽明利水之奇法也。 |
太陽病和陽明病都有黃疸證。但頭汗出而身無汗,則熱邪無法外出;小便不利,則熱邪無法下泄,所以導致瘀熱在裏而渴飲水漿。然而,黃疸有不同,如果發黃在太陽之表,應該發汗,因此用麻黃連翹赤小豆湯,屬於涼散法。如果發黃在太陽和陽明之間,應該以寒涼為主,用梔子柏皮湯,屬於清火法。如果發黃在陽明之裏,應該瀉火,因此設立本方,是逐穢法。茵陳稟受北方之色,經歷冬季而不凋謝,傲霜凌雪,經歷了冬季寒冷之氣,因此能消除熱邪之留結。佐以梔子通暢水源,大黃清除胃熱,使瘀熱通過小便而泄,腹滿自然減輕,腸胃又不會受傷,,仍然符合「引而竭之」之義,亦是陽明病利水之奇特方法。 |
|
|
仲景治陽明渴飲有四法:本太陽轉屬者,五苓散微發汗以散水氣。大煩燥渴、小便自利者,白虎加參清火而生津。脉浮、發熱、小便不利者,猪苓湯滋陰而利水。小便不利、腹滿者,茵陳湯以泄滿,令黃從小便出。病情不同,治法亦異矣。竊思仲景利小便必用化氣之品,通大便必用承氣之味。故小便不利者,必加茯苓,甚者兼用猪苓,因二苓為化氣之品,而小便由於氣化矣。此小便不利,不用二苓者何?本論之「陽明病,汗出多而渴者,不可與猪苓湯。以汗多胃中燥,猪苓復利小便故也」。斯知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,不可用,則汗不出而渴者,津液先虛,更不可用明矣。故以推陳致新之茵陳,佐以屈曲下行之梔子。不用枳、朴以承氣,與芒硝之峻利,則大黃但可以潤胃燥,而大便之遽行可知。故必一宿而腹始減,黃從小便去而不由大腸。仲景立法神奇,匪伊所思耳。 |
仲景治療陽明病渴欲飲水有四種方法:原本從太陽病轉屬陽明病者,用五苓散微微發汗以散水氣。大煩燥渴、小便通利者,用白虎加人參湯清熱而生津。脈浮、發熱、小便不利者,用豬苓湯滋陰而利水。小便不利而腹滿者,用茵陳蒿湯以泄滿,使黃疸之邪通過小便排出。病情不同,治療方法亦不同。我認為仲景利小便必定要用化氣之藥,通大便必定會用承氣湯類方。所以治療小便不利,必定會加茯苓,嚴重者還同時用豬苓,因為二苓是化氣之藥,而小便是通過氣化而出。對於本證之小便不利,為什麼不用此二苓呢?因為《傷寒論》有「陽明病,汗出多而渴者,不可與豬苓湯。以汗多胃中燥,豬苓復利小便故也」之文。由此可知,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,不可用豬苓湯,則汗不出而渴者,津液先虛,更不可用豬苓湯,這是非常明確的。因此,用具有推陳致新作用之茵陳,輔以能屈伸下行之梔子。不用枳實、厚朴以承順胃氣,亦不用芒硝之峻利,這樣大黃就只能潤胃燥,而大便就可以排出了。因此,一定要經過一個夜晚後腹滿才會減輕,黃疸之邪氣通過小便而出,不經過大腸。仲景立法之神奇,真是匪夷所思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大承氣湯 大黃 芒硝 枳實 厚朴 |
||
|
小承氣湯 大黃 枳實 厚朴 |
||
|
治陽明實熱,地道不通,燥屎為患。其外症身熱、汗出、不惡寒、反惡熱、日晡潮熱、手足濈濈汗出,或不了了。其內症六七日不大便、初欲食反不能食、腹脹滿、繞臍痛、煩躁、詀語,發作有時、喘冒不得臥、腹中轉矢氣,或咽燥口乾、心下痛、自利純清水,或汗吐下後熱不觧,仍不大便,或下利、詀語,其脉實、或滑而數者,大承氣湯主之。如大便不甚堅燥者,小承氣湯微和之。如大便燥鞕而證未劇者,調胃承氣湯和之。若汗多、微發熱、惡寒未罷,腹未滿、熱不潮、屎未堅鞕、初鞕後溏,其脉弱、或微滿者,不可用。夫諸病皆因於氣,穢物之不去,由於氣之不順,故攻積之劑必用行氣之藥以主之。「亢則害,承乃制」,此「承氣」之所由。又病去而元氣不傷,此「承氣」之義也。夫方分大小,有二義焉:厚朴倍大黃,是氣藥為君,名「大承氣」。大黃倍厚朴,是氣藥為臣,名「小承氣」。味多、性猛、製大,其服欲令泄下也,因名曰「大」。味少、性緩、製小,其服欲微和胃氣也,故名曰「小」。二方煎法不同,更有妙義。大承氣用水一斗,先煮枳、朴,煮取五升,內大黃,煮取三升,內硝者,以藥之為性,生者銳而先行,熟者氣純而和緩。仲景欲使芒硝先化燥屎,大黃繼通地道,而後枳、朴除其痞滿。緩於製劑者,正以急於攻下也。若小承氣則三物同煎,不分次第,而服只四合。此求地道之通,故不用芒硝之峻,且遠於大黃之銳矣,故稱為「微和」之劑。 |
本方用於治療陽明實熱,腸道不通,燥屎為患。外證見身熱、汗出、不惡寒、反惡熱、日晡潮熱、手足濈濈汗出,或不了了。內證有六七日不大便,初欲食反不能食、腹脹滿、繞臍疼痛、煩躁、譫語、發作有時、喘冒不得臥、腹中轉失氣,或咽燥口乾、心下疼痛、自利純清水,或見汗吐下之後仍然發熱不退,仍然不大便,或下利、譫語,脈實、或滑而數者,用大承氣湯主治。對於大便不很乾燥堅硬者,用小承氣湯微和胃氣。如果大便乾燥堅硬而證候並不嚴重者,用調胃承氣湯調和胃氣。如果汗多、微微發熱、惡寒仍在,腹未滿、沒有潮熱、大便沒有堅硬、初硬後溏,脈弱,或微滿者,則不可用。各種病證都是因為氣機不順暢,穢物之所以不去,是由於氣機不順暢,所以攻積之劑必須以行氣藥為主。「亢則害,承乃制」,這是命名為「承氣」之由來。另外,邪氣去而元氣不受損傷,這是「承氣」之本義。承氣湯分為大小,有兩層含義:厚朴倍於大黃,是氣藥為君藥,稱為「大承氣」。大黃倍於厚朴,是氣藥為臣藥,稱為「小承氣」。味數多、藥性猛、藥劑大,服用後是為了令其泄瀉,因此稱為「大」。味數少、藥性緩、服用後是為了調和胃氣,所以稱為「小」。這二個方之煎煮方法不同,還有妙義。大承氣湯用一斗水,先煮枳實、厚朴,取五升,然後放入大黃,再煮取三升,最後加入芒硝,因為從藥性而言,藥物較生則氣銳利而先行,較熟則氣純和而和緩。仲景希望用芒硝先軟化燥屎,然後用大黃通暢腸道,最用後枳實、厚朴除去痞滿。煎煮分先後次序,正是為了急於攻下。至於小承氣湯,三味藥物一起煎煮,沒有分先後次序,每次只服用四合。這是只為了大便通暢,所以不用峻猛之芒硝,而且遠離銳利之大黃之,因此稱為「微和」之劑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調胃承氣湯 大黃 芒硝 甘草 |
||
|
此治太陽陽明併病之和劑也。因其人平素胃氣有餘,故太陽病三日,其經未盡,即欲再作太陽經,發汗而外熱未解。此外之不觧,由於裏之不通。故太陽之頭項強痛雖未除,而陽明之發熱、不惡寒已外見。此不得執太陽禁下之一說,坐視津液之枯燥也。少與此劑以調之,但得胃氣一和,必自汗而觧。是與「鍼足陽明」同義,而用法則有在經、在府之別矣。不用氣藥而亦名「承氣」者,調胃即所以承氣也。《經》曰:「平人,胃滿則腸虛,腸滿則胃虛,更虛更實,故氣得上下。」今氣之不承,由胃家之熱實。必用硝、黃以濡胃家之糟粕而氣得以下,同甘草以生胃家之津液而氣得以上。「推陳」之中,便寓「致新」之義,一攻一補,「調胃」之法備矣。胃調則諸氣皆順,故亦得以「承氣」名之。前輩見條中無「燥屎」字,便云未堅鞕者可用。不知此方專為燥屎而設,故芒硝分兩多於大承氣。因病不在氣分,故不用氣藥耳。古人用藥分兩有輕重,煎服有法度。粗工不審其立意,故有「三一承氣」之說,豈知此方全在服法之妙。少少服之,是不取其勢之銳,而欲其味之留中,以濡潤胃府而存津液也。所云「太陽病未罷者,不可下」,又與「若欲下之,宜調胃承氣湯」合觀之,治兩陽併病之義始明矣。白虎加人參,是於清火中益氣。調胃用甘草,是於攻實中慮虛。 |
此是治療太陽陽明併病之和劑。由於平素胃氣有餘,所以太陽病三日,邪氣行經未盡,就會再次出現太陽經證,發汗後外熱未解。這種外證之不解,是由於裏氣不通暢。因此,太陽證之頭項強痛雖然未解,但陽明證之發熱、不惡寒已經出現。此時不能拘泥於太陽病禁下之說,而坐視津液乾枯。少用此方調和胃氣,只要胃氣一和,必然會自汗出而解。這與「針足陽明」之義是相同的,但用法則有在經絡、在臟腑之區別。不用調氣之藥而仍稱「承氣」,是因為調胃即是承氣之意。《內經》說:「平人,胃滿則腸虛,腸滿則胃虛,更虛更實,故氣得上下。」如今氣機不能承順,是由於胃家之熱實。必須用芒硝、大黃以濡潤胃家之糟粕而氣得以下行,與甘草同用以生胃家之津液而氣得以上行。「推陳」之中就已含有「致新」之義,一攻一補,「調胃」之法就已完備。胃氣調順則諸氣皆順,因此亦可以稱為「承氣」。前輩見條文中沒有「燥屎」一詞,就說大便未堅硬者可以使用。不知道此方專為燥屎而設,所以芒硝之用量大於大承氣湯。由於病位不在氣分,所以不用調氣之藥。古人用藥分量有輕重,煎服有法度。粗工不能審察仲景立法本意,所以有「三一承氣湯」之說,他們哪裏知此方之妙全在服用方法上。少量服用,就不追求其威力之銳利,而期望其味停留在中焦,以潤澤胃腸而保存津液。《傷寒論》所說「太陽病未罷者,不可下」,再與「若欲下之,宜調胃承氣湯」結合起來看,治療兩陽併病之意義就明白了。白虎加人參湯,是在清火之中兼以益氣。調胃承氣湯用甘草,則是在攻實之中兼顧虛損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桃仁承氣湯 桃仁 大黃 芒硝 甘草 桂枝 |
||
|
治太陽病不觧,熱結膀胱,小腹急結、其人如狂,此畜血也。如表症已罷者,用此攻之。夫人身之經營於內外者,氣血耳。「太陽主氣所生病,陽明主血所生病。」邪之傷人也,先傷氣分,繼傷血分,氣血交併,其人如狂。是以太陽陽明併病所云「氣留而不行」者,氣先病也,「血壅而不濡」者,血後病也。若太陽病不觧,熱結膀胱,乃太陽隨經之陽熱瘀於裏,致氣留不行,是氣先病也。氣者血之用,氣行則血濡,氣結則血畜。氣壅不濡,是血亦病矣。小腹者膀胱所居也,外鄰衝脉,內鄰於肝。陽氣結而不化,則陰血畜而不行,故少腹急結。氣血交併,則魂魄不藏,故其人如狂。治病必求其本,氣留不行,故君大黃之走而不守者,以行其逆氣。甘草之甘平者,以調和其正氣。血結而不行,故用芒硝之醎以軟之,桂枝之辛以散之,桃仁之苦以泄之。氣行血濡,則小腹自舒,神氣自安矣。此又承氣之變劑也。此方冶女子月事不調,先期作痛,與經閉不行者最佳。 |
治療太陽病不解、熱結膀胱,小腹急結、其人如狂,這是蓄血證。如果表證已解,用此方攻之。人身負責營運內外者,就是氣血。「太陽主氣所生病,陽明主血所生病。」邪氣傷人,先傷氣分,隨後傷及血分,氣血交併,其人如狂。因此,太陽陽明併病所謂「氣滯而不行」者,是氣分先病,「血壅而不濡」者,是血分後病。如果太陽病不解,熱結膀胱,那是太陽隨經之熱邪瘀結於裏,導致氣機停滯不行,這是氣分先病。氣機是血液運行之源,氣行則血濡,氣結則血蓄。氣壅不濡,血亦會生病。小腹是膀胱所在之位置,外鄰衝脈,內鄰於肝。陽氣結聚而不化,則陰血蓄結而不能運行。因此小腹急結。氣血交併,則魂魄不藏,因此其人如狂。治病必求於本,氣滯不行,所以用走而不守之大黃為君藥,以調其逆行之氣。用甘平之甘草以調和正氣。血結而不行,所以用鹹味之芒硝軟化蓄血,辛味之桂枝以行散蓄血,苦味之桃仁以瀉血熱。氣行而血濡,則小腹自然舒暢,神氣自然安定。這又是承氣湯之一種變方。用此方治療女性月經不調、月經先期疼痛,以及閉經最為適宜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蜜煎方 猪胆汁 |
||
|
《經》曰:「外者外治,內者內治。」然外病必本於內,故薛立齋於外科悉以內治,故仲景於胃家實者,有蜜煎、胆導等法。蜂蜜釀百花之英,所以助太陰之開。胆汁聚苦寒之津,所以潤陽明之燥。雖用甘、用苦之不同,而「滑可去着」之理則一也,惟求地道之通,不傷脾胃之氣。此為小便自利,津液內竭者設,而老弱虛寒,無內熱症者,最宜之。 |
《內經》說:「外者外治,內者內治。」然而在外之疾病必然本源於裏,所以薛立齋對於外科病證全都以內治為主,所以仲景對於胃家實而有蜜煎導、膽汁導等法。蜂蜜釀造百花之花蕊,可以用來輔助太陰氣之開。豬膽汁聚集苦寒之津液,所以能潤陽明之燥。雖然用甘味、苦味是不同的,但「滑可去着」之原理是一樣的,只求通暢胃腸而不傷脾胃之氣。此方為小便自利而津液內竭之病證而設,尤其適宜於老弱虛寒而無內熱證之人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少陽方總論 |
||
|
六經各有提綱,則應用各有方法。如太陽之提綱主表,法當汗觧,而表有虛實之不同,故立桂枝、麻黃二法。陽明提綱主胃實,法當下觧,而實亦有微甚,故分大、小承氣。少陽提綱有口苦、咽乾、目眩之症,法當清火,而火有虛實。若邪在半表,則製小柴胡以觧虛火之遊行,大柴胡以觧相火之熱結,此治少陽寒熱往來之二法。若邪入心腹之半裏,則有半夏、瀉心、黃連、黃芩等劑。叔和搜採仲景舊論,錄其對症真方,擬防世急,於少陽、太陰二經,不錄一方,因不知少陽症,故不知少陽方耳。 |
六經病各有提綱條文,因此在運用上各有不同方法。比如太陽病之提綱主表,治法上應該發汗解表,但表證有虛實之分,因此立桂枝湯、麻黃湯二種方法。陽明病之提綱主胃實證,應該以攻下為法,但實證亦有輕重之分,所以分為大、小承氣湯。少陽病之提綱有口苦、咽乾、目眩等證,治法上應當清火,但火有虛實之分。如果邪氣在半表,則用小柴胡湯以解虛火之遊行,用大柴胡湯以解相火之熱結,這是治療少陽病寒熱往來之二種方法。如果邪氣進入心腹之半裏,則有半夏瀉心湯、瀉心湯、黃連湯、黃芩湯等方。王叔和搜採仲景舊論時,記錄了能應對應證候之方劑,為了臨床應急之需要,但在少陽、太陰兩經病中,卻沒有記錄一個方劑,因為他並不瞭解少陽病證,所以亦就不知道治療少陽病之方劑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小柴胡湯 柴胡 人參 黃芩 甘草 半夏 薑 棗 |
||
|
此為少陽樞機之劑,和觧表裏之總方也。少陽之氣遊行三焦而司一身腠理之開閤。血弱氣虛,腠理開發,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,邪正分爭,故往來寒熱。與傷寒頭疼、發熱而脉弦細,中風兩無關者,皆是虛火遊行於半表。故取柴胡之輕清微苦微寒者以觧表邪,即以人參之微甘微溫者預補其正氣,使裏氣和而外邪勿得入也。其口苦、咽乾、目眩、目赤、頭汗、心煩、舌胎等症,皆虛火遊行於半裏,故用黃芩之苦寒以清之,即用甘、棗之甘以緩之,亦以提防三陰之受邪也。太陽傷寒則嘔逆,中風則乾嘔。此欲嘔者,邪正相搏於半裏,故欲嘔而不逆。脇居一身之半,為少陽之樞,邪結於脇,則樞機不利,所以胸脇苦滿、默默不欲食也。引用姜、半之辛散,一以佐柴、芩而逐邪,一以行甘、棗之泥滯,可以止嘔者,即可以泄滿矣。夫邪在半表,勢已向裏,未有定居,故有或為之證,所以方有加減,藥無定品之可拘也。若胸中煩而不嘔者,去半夏、人參,恐其助煩也。若煩而嘔者,則人參可去,而半夏不得不用矣。加栝婁實者,取其苦寒降火而除煩也。若渴者,是元氣不足而津液不生,去半夏之辛溫,再加人參以益氣而生津液,更加栝婁根之苦寒者以升陰液而上滋也。若腹中痛者,雖相火為患,恐黃芩之苦轉屬於太陰,故易芍藥之酸以瀉木。若邪結於脇下而痞鞕者,去大棗之甘能助滿,加牡蠣之醎以軟堅也。若心下悸、小便不利者,是為小逆,恐黃芩之寒轉屬於少陰,故易茯苓之淡滲而利水。若內不渴而外微熱者,是裏氣未傷而表邪未觧,不可補中,故去人參,加桂枝之辛散,溫覆而取其微汗。若欬者,是相火迫肺,不可益氣,故去人參,所謂「肺熱還傷肺」者此也。凡發熱而欬者重在表,故小青龍於麻、桂、細辛中加乾姜、五味。此往來寒熱而欬者,重在裏,故并去姜、棗之和營衛者,而加乾姜之苦辛,以從治相火上逆之邪,五味之酸,以收肺金三之氣也。合而觀之,但顧邪氣之散而正氣無傷,此製小柴胡之意歟!是方也,與桂枝湯相倣,而柴胡之觧表遜於桂枝,黃芩之清裏重於芍藥,姜、棗、甘草微行辛甘發散之常,而人參甘溫,已示虛火可補之義。且「去滓再煎」之法,又與他劑不同。粗工恐其閉住邪氣,妄用柴、芩而屏絕人參,所以夾虛之症,不能奏功,反以速斃也。 |
這是少陽樞機之劑,和解表裏之總方。少陽之氣遊走於三焦而掌管全身腠理之開合。當血氣虛弱,腠理疏鬆時,邪氣因而進入並與正氣相爭,邪正分爭,故而寒熱往來。與傷寒之頭痛、發熱而脈弦細,以及中風無關,屬於虛火遊行於半表。因此選用輕清微苦微寒之柴胡以解表邪,同時用微甘微溫之人參預先補益正氣,使裏氣調和則外邪無法進入。口苦、咽乾、目眩、目赤、頭汗、心煩、舌上苔等證,都是虛火遊走於半裏,因此用苦寒之黃芩清熱,同時用味甘之甘草和大棗以緩黃芩之苦寒,亦是為了防備三陰受邪。太陽傷寒則嘔逆,太陽中風則乾嘔。而這裏出現欲嘔是邪氣與正氣相爭於半裏,所以欲嘔但不逆出。脅居於身體之側面,是少陽之樞機,邪氣結於脅部,則樞機不利,所以胸脅苦滿、默默不欲食。選用辛散之生薑和半夏,一方面輔助柴胡和黃芩驅邪,一方面行散甘草、紅棗之泥滯,可以止嘔者,即可以泄滿。邪氣雖然在半表,其勢已經趨向於裏,尚未有定居,因此有一些可能出現之證候,所以此方需要加減,而用藥則沒有固定之限制。如果胸中煩而不嘔,恐怕半夏、人參會助煩,故去之。如果煩躁並伴有嘔吐,可以去人參,但半夏則必須留用。加栝蔞實,是取其苦寒降火而除煩。如果口渴,是元氣不足而津液不生,則去辛溫之半夏而加人參益氣以生津液,再加苦寒之栝蔞根以升陰液而滋上。如果腹中痛,雖然是相火為患,但恐怕黃芩之苦會使病變轉屬太陰,因此用芍藥之酸以瀉木氣。若邪氣結於脅下而痞硬者,則去大棗以防甘味可以助滿,再加鹹味之牡蠣以軟堅。如果心下悸、小便不利者,這是輕微誤治所致,恐怕黃芩之寒會使病變轉屬少陰,因此用淡滲之茯苓以利水。如果內不渴而外有微熱者,表示裏氣未受傷而表邪未解,不可以補中,因此去人參而加辛散之桂枝,溫覆以取微汗。如果咳嗽,表示相火迫於肺部,不可以益氣,因此去人參,這就是所謂「肺熱還傷肺氣」。凡是發熱而咳者重在表證,因此小青龍湯用麻黃、桂枝、細辛,再加乾薑、五味子。這裏往來寒熱而咳者重在裏證,因此同時去調和營衛之甘草和大棗,再加苦辛之乾薑以治相火上逆之邪,加味酸之五味子以收斂肺氣。綜合來看,只考慮驅散邪氣而不傷正氣,這就是設立小柴胡湯之意吧!此方與桂枝湯相似,但柴胡解表之作用不如桂枝,黃芩清裏之作用比芍藥強,生薑、大棗、甘草則略微取其辛甘發散之用,而用甘溫之人參,已經表明虛火可以用補之意。而且用「去滓再煎」之法又與其他方劑不同。粗工擔心小柴胡湯可能會閉塞邪氣,妄用柴胡、黃芩而不用人參,所以對於夾虛證來說,不能取得療效,反而加速其死亡。 |
|
|
按:本方七味,柴胡主表邪不觧,甘草主裏氣不調,五物皆在進退之列。本方若去甘草,便名「大柴胡」,若去柴胡,便名「瀉心」、「黃芩」、「黃連」等湯矣。前輩皆推柴胡為主治,盧氏又以柴胡三生半冬配半夏為主治,皆未審本方加減之義耳。 |
按:本方七味藥中,柴胡主要針對表邪不解,甘草主要用於調和裏氣,其他五味藥都在可以加減之列。本方如果去甘草,就稱為「大柴胡湯」,如果去柴胡,就成了「瀉心湯」、「黃芩湯」、「黃連湯」等方。前輩都推柴胡為主治藥,而盧氏則主張以柴胡三生半冬與半夏搭配為主治藥,這都反映其未能審察本方藥物加減之意。 |
|
|
本方為脾家虛熱,四時瘧疾之聖藥,餘義詳《少陽病》觧製方大法。 |
本方是治療脾家虛熱,四時瘧疾之聖藥,其他方面之意義請參詳《少陽病》之製方大法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大柴胡湯 柴胡 黃芩 半夏 芍藥 枳實 薑棗 |
||
|
傷寒發熱,汗出不觧,十餘日結熱在裏,心下痞鞕、嘔吐、下利,復往來寒熱。或妄下後,柴胡症仍在,與小柴胡湯,嘔不止、心下急、鬱鬱微煩者,此皆少陽半表裏氣分之症。此方是治三焦無形之熱邪,非治胃府有形之實邪也。其心下急、煩、痞鞕,是病在胃口而不在胃中,結熱在裏,不是結實在胃。因不屬有形,故十餘日復能往來寒熱。若結實在胃,則蒸蒸而發熱,不復知有寒矣。因往來寒熱,故倍生姜,佐柴胡以觧表。結熱在裏,故去參、甘,加枳、芍以破結。條中並不言及大便鞕,而且有下利症,仲景不用大黃之意曉然。後人因有「下之」二字,妄加大黃以傷胃氣,非大謬乎?妄作傷寒書者,總不知憑脉辨症以用藥,專以併合仲景方為得意。如加甘草於大承氣中,而名「三一承氣」,加柴、芩、芍藥於承氣中,而名「六一順氣」,以為可以代三承氣、大柴胡、大陷胸等湯。竟不審仲景方分大小,藥分表裏,設方命劑,當因病人病機變遷輕重耳。豈聖賢之立方不精也,須爾輩更改乎?大小柴胡,俱是兩觧表裏之劑。大柴胡主降氣,小柴胡主調氣。調氣無定法,故小柴胡除柴胡、甘草外,皆可進退。降氣有定局,故大柴胡無加減法。後人每方俱有加減,豈知方者哉! |
傷寒發熱,汗出不解,十餘日後熱結在裏,心下痞硬、嘔吐、下利,又見往來寒熱。或因誤下後,柴胡證仍在,服小柴胡湯後,嘔不止,心下急痛,鬱鬱微煩者,這都是少陽半表半裏氣分之病證。此方用於治於三焦無形之熱邪,而不是治胃腸有形之實邪。心下急、心煩、痞硬之證,是病在胃口而不在胃中,結熱在裏而非胃中有實邪凝結。因為不屬於有形實邪,所以十餘日後仍有往來寒熱。如果是胃中有實邪凝結,則會蒸蒸發熱,不再有惡寒。由於往來寒熱,所以倍用生薑,佐以柴胡解表。由於結熱在裏,所以去人參和甘草,加枳實和芍藥以破結。條文中並未提到大便硬,而且有下利之證,仲景不用大黃之意思就顯而易見了。後人因為見條文有「下之」二字,就妄加大黃而損傷胃氣,,這難道不是極大之錯誤嗎?那些隨意注解《傷寒論》之人總是不明白要憑脈證而用藥,專門將仲景之方合併在一起而自鳴得意。比如在大承氣湯中加甘草,名為「三一承氣湯」,在大承氣湯中加柴胡、黃芩、芍藥,稱為「六一順氣湯」,以為可以取代三承氣湯、大柴胡湯、大陷胸湯等方劑。竟然不審察仲景之方分大小,用藥分表裏,設立方劑及其命名,應該根據病人病機變化之輕重。難道是聖賢立方不精,而需要你們來改變嗎?大、小柴胡都是兩解表裏之方。大柴胡湯主降氣,小柴胡湯主調氣。調氣無固定之法,所以小柴胡湯中除了柴胡和甘草外,其他藥物都可以加減。降氣有定局,所以大柴胡湯沒有加減法。後人將每個仲景方都設立加減法,這哪裏是懂得仲景方之人啊!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柴胡桂枝乾姜湯 柴胡 桂枝 乾姜 黃芩 甘草 牡蠣 栝婁根 |
||
|
傷寒五六日,發汗不觧,尚在太陽界。反下之,胸脇滿微結,是繫在少陽矣。此「微結」與「陽微結」不同。「陽微結」對「純陰結」言,是指結實在胃。此「微結」對「大結胸」言,是指胸脇痞鞕。小便不利者,因下後下焦津液不足也。頭為三陽之會,陽氣不得降,故但頭汗出。半表半裏之寒邪未觧,上下二焦之邪熱已甚,故往來寒熱、心煩耳。此方全從柴胡加減。心煩、不嘔、不渴,故去半夏之辛溫,加栝蔞根以生津。胸脇滿而微結,故減大棗之甘滿,加牡蠣之醎以軟之。小便不利而心下不悸,是無水可利,故不去黃芩,不加茯苓。雖渴,而太陽之餘邪不觧,故不用參而加桂。生姜之辛易乾姜之溫苦,所以散胸脇之滿結也。初服煩即微者,黃芩、瓜婁之效。繼服汗出周身,內外全愈者,姜桂之功。小柴胡加減之妙,若無定法,而實有定局矣。更其名曰「柴胡桂枝乾姜」,以柴胡症具,而太陽之表猶未觧,裏已微結,須此桂枝觧表,乾姜觧結,以佐柴胡之不及耳。 |
傷寒五六日,發汗不解,仍然在太陽病之範圍。反而進行攻下,胸脅滿而微結,這已經是屬於少陽病。這裏「微結」與「陽微結」不同。「陽微結」是相對於「純陰純」而言,是指胃中有實邪凝結。這裏所說「微結」是相對於「大結胸證」而言,是指胸脅痞硬。小便不利是因為攻後後下焦津液不足。頭為三陽之會,陽氣不得下降,所以但頭汗出。半表半裏之寒邪未解,上下二焦之邪熱已經嚴重,所以往來寒熱而心煩。此方完全根據小柴胡湯進行加減。心煩、不嘔、不渴,所以去辛溫之半夏,加栝蔞根以生津。胸脅滿而微結,所以減少因為味甘而容易導致脹滿之大棗,加味鹹之牡蠣以軟堅。小便不利而心下不悸,則無水邪需要滲利,所以不去黃芩,亦不加茯苓。雖然口渴,但太陽之餘邪未解,所以不用人參而加桂枝。將辛味之生薑換成苦溫之乾薑,可以散胸脅之滿結。初服藥時煩躁隨即變得輕微,這是黃芩和栝蔞根之功效。接著服藥而全身汗出,內外全愈,則是乾薑和桂枝之功效。小柴胡湯加減之法,看上去好像沒有固定之法,但實際上是有定局的。將其名更改為「柴胡桂枝乾薑湯」,是因為柴胡證都具備,而太陽之表證尚未解除,在裏已經微結,必須用桂枝解表,乾薑解結,以輔助柴胡之不足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柴胡桂枝湯 柴胡 桂枝 人參 甘草 半夏 黃芩 芍藥 大棗 生姜 |
||
|
柴胡二湯,皆調和表裏之劑。桂枝湯重觧表而微兼清裏,柴胡湯重和裏而微兼散表。此傷寒六七日,正寒熱當退之時,尚見發熱、惡寒諸表症,更兼心下支結諸裏症。表裏不觧,法當雙觧之。然惡寒微,則發熱亦微可知。支節煩疼,則一身骨節不痛可知。微嘔、心下亦微結,故謂之「支結」。表症雖不去而已輕,裏症雖已見而未甚,此太陽少陽併病之輕者,故取桂枝之半以觧太陽未盡之邪,取柴胡之半以觧少陽之微結。凡口不渴、身有微熱者,當去人參。此以六七日來邪雖不觧,而正氣已虛,故用人參以和之也。外症雖在,而病機已見於裏,故方以柴胡冠桂枝之前,為雙觧兩陽之輕劑。 |
小柴胡湯與桂枝湯都是調和表裏之方。桂枝湯重於解表而微微兼能清裏,小柴胡湯重於和裏而微微兼能散表。這是傷寒病六七日,正值惡寒、發熱即將消退之時,仍然見有發熱、惡寒等表證,同時伴有心下支結等裏證。表裏不解,治法上應當表裏雙解。然而,惡寒微,則可知發熱亦微。肢節煩痛,則可知全身骨節不痛。微嘔、心下亦微結,所以稱之為「支結」。表證雖然未除但已經變輕,裏證雖然已見但尚未嚴重,,這是太陽少陽併病之輕證,因此,取桂枝湯之一半以解尚未盡除之太陽邪氣,取小柴胡湯之一半以解少陽之微結。凡是口不渴、、身有微熱者,當去人參。這裏因為經過六七日,邪氣雖然未解,但正氣已經虛弱,所以用人參以調和。雖然外證仍在,但病機已經見於裏,所以方名以柴胡居於桂枝之前,使之成為雙解太陽少陽之輕劑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柴胡 人參 黃芩 半夏 薑棗 龍骨 牡蠣 桂枝 鉛丹 茯苓 大黃 |
||
|
傷寒八九日不觧,陽盛陰虛,下之應不為過,而變症蜂起者,是未講於調胃承氣之法而下之不得其術也。胸滿而煩、小便不利,三陽皆有是症。而驚是木邪犯心,詀語是熱邪入胃。一身盡重,是病在陽明而無氣以動也。不可轉側,是關少陽而樞機不利也。此為少陽陽明併病,故取小柴胡之半以轉少陽之樞,輔大黃之勇以開陽明之閤。滿者忌甘,故去甘草。小便不利,故加茯苓。驚者須重以鎮怯,鉛稟乾金之體,受癸水之氣,能清上焦無形之煩滿,中焦有形之熱結,煉而成丹,不特入心而安神,且以入肝而滋血矣。龍為東方之神,而骨具酉金之體,重能鎮驚,亦以金令行於左而平木。蠣為化生之物,其體堅不可破,其性守而不移,不特靜可以鎮驚,而寒可以除煩熱,且醎能潤下。佐茯苓以利水,又能軟堅。佐大黃以清胃也。半夏引陽入陰,能治目不瞑,亦安神之品,故少用為佐。人參能通血脉,桂枝能行營氣,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,在所必須,故雖胸滿、詀語而不去也。此於柴胡方加味而取「龍蠣」名之者,亦以血氣之屬,同類相求耳。 |
傷寒病八九日不解,陽盛而陰虛,進行攻下應該不為過分,但攻下後各種變證出現,這是因為沒有跟從調胃承氣湯之法而運用了不恰當之下法。胸滿而煩躁、小便不利,這是三陽病都會有之證候。而驚恐則是木邪犯心,譫語是熱邪入胃。一身都沉重,是病在陽明而無氣以運行。不能翻身,是關乎少陽之樞機不利。這是少陽陽明併病,因此取小柴胡湯之一半以運轉少陽之樞機,輔以勇猛之大黃以開陽明之閤。脹滿者忌用甘味,所以去甘草。小便不利,所以加茯苓。驚恐者必須重以鎮怯,鉛丹稟受乾金之體以及癸水之氣,能夠清除上焦無形之煩滿及中焦有形之熱結,煉製成丹,不只是能入心而安神,而且能入肝而滋養血液。龍屬東方之神,而其骨則具有酉金之性,質重能鎮驚,亦因為金令行於左以平木氣。牡蠣為化生之物,其外殼堅不可破,其性守而不走,不只是取其靜而可以鎮驚,其寒涼之性則可以驅除煩熱,而且味鹹還能潤下。輔以茯苓利水,又能軟堅。佐以大黃清胃。半夏引陽入陰,能治目不閉合,亦是安神之品,因此少用為輔助。人參能通利血脈,桂枝能推動營氣運行,一身都沉重而無法翻身者是必須要用的,所以即使胸滿、譫語而不去人參與桂枝。此方是在小柴胡湯基礎上加味而成,但取「龍骨牡蠣」為名者,亦是因為龍骨、牡蠣為血氣之屬,同類相求罷了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黃連湯 黃連 人參 甘草 桂枝 乾姜 半夏 棗子 |
||
|
傷寒表不發熱而胸中有熱,是其人未傷寒時素有畜熱也。熱在胸中必上形頭面,故寒邪不得上干。上焦實必中氣虛,故寒邪得從脇而入胃。《內經》云「中於脇則入少陽」,此類是已。凡邪在少陽,法當柴胡主治。此不往來寒熱,病不在半表,則柴胡不中與之。胸中為君主之宮城,故用半夏瀉心加減。胸中之熱不得降,故炎上而欲嘔。胃因邪氣之不散,故腹中痛也。用黃連瀉心胸之熱,姜、桂祛胃中之寒,甘、棗緩腹中之痛,半夏除嘔,人參補虛。雖無寒熱往來於外,而有寒熱相搏於中,所以寒熱並用,攻補兼施,仍不離少陽和觧之治法耳。此症在太陰、少陽之間,此方兼瀉心、理中之劑。 |
傷寒病,體表不發熱而胸中有熱,這是患者在未患傷寒病之前平素已有之蓄熱。熱在胸中必然會在頭面上反映出來,因此寒邪無法上犯。上焦有實邪,中氣必然虛損,因此寒邪可以從脅肋進入胃腑。《內經》說「中於脅則入少陽」,就是這類情況。凡是邪犯少陽,治法上當以柴胡湯為主。此證沒有往來寒熱,其病不在半表,則柴胡湯不適用於此。胸中為君主之宮城,因此用半夏瀉心湯加減。胸中之熱無法下降,所以上炎而欲嘔。邪氣結聚於胃中不散,所以腹中痛。用黃連瀉心胸之熱,用乾薑和桂枝驅除胃中之寒,用甘草和大棗緩解腹中之疼痛,用半夏來止嘔,用人參來補虛。儘管沒有在外可見之往來寒熱,但在裏則有寒熱相搏,因此寒熱並用,攻補兼施,仍然遵守少陽和解之治法。此證在於太陰和少陽之間,此方則兼有瀉心湯、理中湯之法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黃芩湯 黃芩 芍藥 甘草 大棗 |
||
|
太陽陽明合病,是寒邪初入陽明之經,胃家未實,移寒於脾,故自下利。此陰盛陽虛,與葛根湯辛甘發散以維陽也。太陽少陽合病,是熱邪陷入少陽之裏,胆火肆逆,移熱於脾,故自下利。此陽盛陰虛,與黃芩湯苦甘相淆以存陰也。凡太少合病,邪在半表者,法當從柴胡桂枝加減。此則熱淫於內,不須更顧表邪,故用黃芩以泄大腸之熱,配芍藥以補太陰之虛,用甘、棗以調中州之氣。雖非胃實,亦非胃虛,故不必人參以補中也。若嘔是上焦之邪未散,故仍加姜、夏。此柴胡桂枝湯去柴、桂、人參方也。凡兩陽之表病,用兩陽之表藥。兩陽之半表病,用兩陽之半表藥。此兩陽之裡病,用兩陽之裏藥。逐條細審,若合符節。然凡正氣稍虛,表雖在而預固其裏。邪氣正盛,雖下利而不須補中,此又當着眼處。《內經·熱病論》云:「太陽主氣,陽明主肉,少陽主胆。」「傷寒一日太陽,二日陽明,三日少陽。」冬不藏精,則精不化氣,故先氣病,次及肉之病而及胆,仍自外之內。此病本雖因於內,而病因為傷於寒,故一病兩名耳。胆汁最苦最寒,乃相火中之真味。火旺之水虧,胆汁上溢而口苦,故用芩、連之品以滋胆汁而清相火也。 |
太陽陽明合病,是寒邪初入陽明經脈,胃家尚未成實,寒氣轉移至脾,因此自下利。這是陰盛陽虛,與葛根湯則辛甘發散以顧護陽氣。太陽少陽合病,是熱邪陷入少陽之裏,膽火肆逆,熱邪轉移至脾,因此自下利。這是陽盛陰虛,與黃芩湯則苦甘相合以留存陰氣。凡是太陽少陽合病,邪氣在半表者,治法上應當從柴胡桂枝湯進行加減。這裏是熱邪內盛,不需要過多考慮表邪,因此用黃芩以清大腸之熱邪,配芍藥以補益太陰之虛,用甘草、大棗調理中焦之氣。雖然不是胃家實,亦不是胃家虛,因此不需要用人參補益中焦。如果出現嘔吐,是上焦邪氣未散,可以仍然加生薑和半夏。這是柴胡桂枝湯去柴胡、桂枝、人參之方。凡是兩陽之表病,則用兩陽之表藥。凡是兩陽之半表病,則用兩陽之半表藥。這是兩陽之裏病,所以用兩陽之裏藥。逐條加以仔細審察,是完全相符的。然而,凡是正氣稍虛,表證雖然在而應該預先固護裏氣。而邪氣正盛之時,雖然有下利亦不需要補益中焦,這又是需要留意之處。《內經·熱病論》說:「太陽主氣,陽明主肉,少陽主膽。」「傷寒一日太陽,二日陽明,三日少陽。」冬天不能藏精,則精不能化為氣,因此先有氣病,然後是肉病,接着是膽病,仍然都是從外到內之過程。此病原本雖然是源於內,但發病則因為外傷於寒,所以一種病而有兩種名稱罷了。膽汁最苦最寒,是相火中之真味。火旺所致之水虧,以致膽汁上溢而口苦,因此用黃芩和黃連這類藥來滋養膽汁並清泄相火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太陰方總論 |
||
|
太陰主內,為陰中至陰,最畏虛寒,用溫補以理中,此正法也。然太陰為開,故太陰亦能中風,則亦有可汗症。若見四肢煩疼之表而脉浮者,始可與桂枝湯發汗。若表熱裏寒,下利清穀,是為中寒,當用四逆以急救其裏,不可攻表,以汗出必脹滿也。又恐妄汗而腹脹滿,故更製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參湯以觧之。太陰本無下症,因太陽妄下而腹滿時痛者,是陽邪內陷,故有桂枝加芍藥湯之下法。若病不從太陽來,而腹滿時痛,是太陰本病。倘妄下之,必胸下結鞕而成寒實結胸,故更制三物白散以散之。此仲景為太陰悞汗悞下者立救逆法也,叔和不能分明六經之方治,而專以汗吐下之三法教人,重集諸「可與」、「不可與」等浮泛之辭,以混仲景切近的當之方法,是點金成鉄矣。 |
太陰主內,屬陰中之至陰,最畏虛寒,用溫補以調理中焦,這是常法。然而,太陰為開,因此太陰病亦有中風證,亦有可以發汗之證。如果見四肢煩疼之表證而脈浮者,才可以用桂枝湯發汗。如果是表熱而裏寒,下利清穀,這是中寒證,應該用四逆湯急治裏證,不可治表,因為汗出必然導致腹脹滿。又恐怕發汗導致腹脹滿,因此又創製了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加以治療。太陰病本身並不會有可下之證,因為太陽病誤下而腹滿時痛者,那是陽邪內陷所致,所以才有桂枝加芍藥湯之攻下法。如果病證並非由太陽病而來,則腹滿時痛,就是太陰本身之病證。如果誤用攻下,必然導致胸下結硬而形成寒實結胸,因此又創製三物白散以散之。這是仲景針對太陰誤汗誤下所創立救逆之法,王叔和無法明確區分六經病之方與治法,而專門以發汗、涌吐、攻下三法來教人,重新整理各種「可與」、「不可與」等浮泛之辭,混入仲景切近而實用治法之中,這反而是點金成鐵了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理中丸 人參 白朮 乾姜 甘草 |
||
|
太陰病,以吐利、腹滿痛為提綱,是遍及三焦矣。然吐雖屬上,而由於腹滿;利雖屬下,而由於腹滿,皆因中焦不治以致之也。其來由有三:有因表虛而風寒自外入者,有因下虛而寒濕自下上者,有因飲食生冷而寒邪由中發者。總不出於虛寒,法當溫補以扶胃脘之陽,一理中而滿痛、吐利諸症悉平矣。故用白朮培脾土之虛,人參益中宮之氣,乾姜散胃中之寒,甘草緩三焦之急也。且乾姜得白朮能除滿而止吐,人參得甘草能療痛而止利,或湯或丸,隨機應變,此理中確為之主劑歟!夫「理中者理中焦」,此仲景之明訓,且加減法中又詳其吐多、下多、腹痛滿等法。而叔和錄之於《大病差後》治真吐一症,是坐井觀天者乎! |
太陰病,以嘔吐、下利、腹滿疼痛為提綱證,這反映了病位涉及三焦。嘔吐雖然屬於上焦,而實質是由於腹滿;下利雖然屬於下焦,但實質是由於腹滿,都是因為中焦失調所導致。其來路有三種情況:一是因為表虛而風寒從外而入,二是因為下焦虛弱而寒濕由下上犯,三是因飲食生冷而寒邪從內而發。總是不離於虛寒,治法上應當溫補以輔助胃脘之陽,只要調理中焦則脹滿、疼痛、嘔吐、下利等證悉除。因此用白朮培補脾胃之虛,人參增益中宮之氣,乾薑溫散胃中之寒,甘草緩和三焦之氣急。而且乾薑得白朮能除滿而能止吐,人參得甘草能治疼痛而止下利,或用湯劑或用丸劑,根據病機而作相應變化,這個理中丸確實是主治之方啊!「理中者理中焦」,這是仲景之明訓,同時在加減法中詳細說明了嘔吐多、下利多、腹痛脹滿等治法。而王叔和則將此記錄在《大病差後》治療真吐一證,可謂是坐井觀天! |
|
|
按:太陰傷寒,手足自溫者,非病由太陽,必病關陽明。此陰中有陽,必無吐利交作之患,或暴煩下利,或發黃便鞕,則腹滿、腹痛,是脾家實而非虛熱,而非寒矣,又當於茵陳、調胃輩求之。 |
按:傷寒太陰病證而手足自溫者,如果不是來自太陽病,必然與陽明病有關。這是陰中有陽,必然不會有吐利交替發作之證候,或者暴煩下利,或發黃便硬,這樣,腹滿、腹痛就屬於脾家實而非虛熱,亦非寒邪,則應當考慮使用茵陳蒿湯、調胃承氣湯等方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四逆湯 乾姜 附子 甘草 |
||
|
「脉浮而遲」,「表熱裏寒」二句,是立方之大旨。脉浮為在表,遲為在臟。浮中見遲,是浮為表虛,遲為臟寒矣。腹滿、吐利、四肢厥逆,為太陰症。姜、附、甘草,本太陰藥。諸條不冠以「太陰」者,以此方為太陽併病立法也。按:四逆諸條,皆是太陽壞病轉屬太陰之症。太陽之虛陽留於表而不罷,太陰之陰寒與外來之寒邪相得而益深。故外症則惡寒發熱、或大汗出、身體痛、四肢疼、手足冷、或脉浮而遲、或脉微欲絕。內症則腹滿、腹脹、下利清穀、小便自利、或吐利交作。此陰邪猖厥,真陽不歸,故云「逆」也。本方是用四物以救逆之謂,非專治四肢厥冷而為名。蓋仲景凡治虛症,以補中為主。觀協熱下利、脉微弱者用人參,汗後身疼、脉沉遲者加人參,此脉微欲絕、下利清穀,且不煩、不欬,中氣大虛,元氣已虛,若但溫不補,何以救逆乎?觀茯苓四逆之治煩躁,且用人參,其冠以「茯苓」而不及參,則本方有參可知。夫人參通血脉者也,通脉四逆,豈得無參?是必因本方之脫落而仍之耳。薛新甫用三生飲加人參兩許而駕馭其邪,則仲景用生附,安得不用人參以固其元氣耶?叔和以太陰之吐利、四逆,混入厥陰,不知厥陰之厥利是木邪剋土為實熱,太陰之厥利,是脾土自病,屬虛寒,徑庭自異。若以姜、附治相火,豈不逆哉?按理中、四逆二方,在白朮、附子之別。白朮為中宮培土益氣之品,附子為坎宮扶陽生氣之劑。故理中只理中州脾胃之虛寒,四逆能佐理三焦陰陽之厥逆也。後人加附子於理中,名曰「附子理中湯」,不知理中不須附子,而附子之功不專在理中矣。蓋脾為後天,腎為先天,少陰之火所以生太陰之土。脾為五藏之母,少陰更太陰之母,與四逆之為劑,重於理中也。不知其義者,謂生附配乾姜,補中有發。附子得生姜而能發散,附子非乾姜則不熱,得甘草則性緩。是止知以藥性上論寒熱攻補,而不知於病機上分上下淺深也,所以不入仲景之門也哉! |
「脈浮而遲」,「表熱裏寒」二句,是本方立方之大旨。脈浮為病在表,脈遲為病在臟。脈浮而遲,浮為表虛,遲為臟寒。腹滿、吐利、四肢厥逆,屬於太陰病證。乾薑、附子、甘草,原本屬於太陰病之藥。各條文沒有冠以「太陰」,是因為此方是為太陽之併病而立法。按:四逆湯各條文,都是太陽病壞病後轉屬太陰之病證。太陽之虛陽停留於表而表證不罷,太陰之陰寒與外來之寒邪相互作用而使病情加劇。因此,外證見惡寒發熱、或大汗出、身體痛、四肢疼、手足冷、或脈浮而遲、或見脈微欲絕。內證則有腹滿、腹脹、下利清穀、小便自利,或吐利交作。這是陰邪猖獗,真陽不歸,所以稱之為「逆」。本方是用四味藥來救逆,而非專門以治療四肢厥冷而命名。因為仲景治療虛證,都是以補中為主。看看治療協熱下利、脈微弱者用人參,治療發汗後身疼痛、脈沉遲者加人參,這裏則是脈微欲絕、下利清穀,而且不煩、不咳,中氣大虛,元氣已虛,如果只是溫而不補,又用什麼來救逆呢?看看茯苓四逆湯治療煩躁,尚且用人參,方名冠以「茯苓」而不提及人參,可知四逆湯中應該有人參。人參是通血脈之藥,通脈以治四逆,豈能沒有人參呢?這必然是因為文獻記錄本方時有所脫落。薛新甫使用三生飲加人參一兩多以抵禦邪氣,那麼仲景用生附子,怎麼可能不用人參來固守元氣呢?王叔和將太陰病之吐利、四逆,混入厥陰病中,不知道厥陰病之厥利是木邪克土所致,屬於實熱,與太陰病治厥利是脾土自病,屬虛寒,二者完全不同。如果以乾薑、附子來治療相火,豈不是逆治嗎?按:理中湯和四逆湯之分別在於白朮、附子。白朮是中宮培土益氣之品,附子是坎宮扶陽生氣之藥。因此,理中湯只是調理中焦脾胃之虛寒,而四逆湯則能輔助調理三焦陰陽之厥逆。後人將附子加入理中湯中,稱為「附子理中湯」,是不知道理中湯中不需要附子,而附子之功效不專在調理中焦。因為脾為後天之本,腎為先天之本,所以少陰之火能生太陰之土。脾為五臟之母,少陰更是太陰之母,所以四逆湯之方比理中湯作用更強。不知此理之人,認為生附配乾薑,補中有發。附子得生薑則能發散,附子無乾薑則不熱,與甘草相配則性緩。這是只知在藥性上論寒熱攻補,而不知在病機上分上下淺深,所以不能進入仲景之門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 |
||
|
此太陰調胃承氣之方也。凡治病必分表裏,而表裏偏有互呈之證,如麻黃之喘,桂枝之自汗,大青龍之煩躁,小青龍之欬,皆病在表而夾裏症也。用杏仁以治喘,芍藥以止汗,石膏以治煩躁,五味、乾姜以治欬,是於表劑中兼治裏也。若下利、腹脹滿者,太陰裏症而兼身體疼痛之表症,又有先溫其裏,後觧其表之法。若下利清穀而兼脉浮表實者,又有只宜治裏,不可攻表之禁。是知仲景重內輕外之中,更有淺深之別也。夫汗為陽氣,而腰以上為陽,發汗只可散上焦營衛之寒,不能治下焦藏府之濕。若病在太陰,寒濕在腸胃而不在營衛,故陰不得有汗,妄發其汗,則胃脘之微陽隨而達於表,腸胃之寒濕入經絡而留於腹中,下利或1止而清穀不消,所以汗出必脹滿也。凡太陽汗後脹滿,是陽實於裏,將轉屬陽明。太陰汗後而腹滿,是寒實於裏而陽虛於內也。邪氣盛則實,故用厚朴、姜、夏散邪而除脹滿。正氣奪則虛,故用人參、甘草補中而益元氣。此亦理中之劑歟?若用之於太陽汗後,是抱薪救火,如此症而妄作太陽治之,如水益深矣。 |
此是太陰病之調胃承氣湯方。凡治病必須區分表裏,而表裏相兼又有不同之傾向,如麻黃湯證之喘息,桂枝湯證之自汗,大青龍湯證之煩躁,小青龍湯證之咳嗽,都是病位在表而夾裏證。用杏仁以治喘,用芍藥以止汗,用石膏以治煩躁,用五味子、乾薑以治咳嗽,是在治表方中兼治療裏證。如果下利、腹脹滿者,是太陰裏證而兼身體疼痛之表證,又有先溫其裏而後解其表之治法。如果下利清穀而兼脈浮之表實者,就又有只應該治裏,不可治表之禁忌。可見仲景重內輕外之治法中,更有淺深之分。汗為陽氣所化,而腰以上屬陽,發汗只能散上焦營衛之寒,不能治下焦臟腑之濕。如果病在太陰,寒濕在腸胃而不在營衛,因此陰病不能發汗,妄加發汗,則胃脘之微陽就會隨之而達於表,腸胃之寒濕則入於經絡而留於腹中,出現下利不止而完穀不化,所以汗出後必然腹脹滿。凡太陽汗出後腹脹滿,是陽實於裏,將轉屬至陽明。太陰汗出後腹脹滿,是寒實於裏而陽虛於內。邪氣盛則實,所以用厚朴、生薑、半夏以散邪而除腹脹滿。正氣奪則虛,所以用人參、甘草補中而益元氣。這不亦是理中之方嗎?如果將其用在太陽病發汗後,就是抱薪救火,如此之證候而當作太陽病來治療,就會使病情更加嚴重。 |
|
|
1 下利不止:根據前後文意,當是「下利不止」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三物白散 桔梗 貝母 巴豆 |
||
|
太陽表熱未除而反下之,熱邪與水氣相結成實熱結胸。太陰腹滿時痛而反下之,寒熱相結成寒實結胸。夫大、小陷胸用苦寒之品者,為有熱也。此無熱症者,則不得槩以陽症之法治之矣。三物小陷胸湯者,即「白散」也。以其結鞕而不甚痛,故亦以「小」名之。以三物皆白,欲以別於小陷胸之黃連,故以「白」名之。在太陽則或湯或丸,在太陰則或湯或散,隨病機之宜也。貝母善開心胸鬱結之氣,桔梗能提胸中陷下之氣。然微寒之品不足以勝結鞕之陰邪,非巴豆之辛熱斬關而入,何以使胸中之陰氣流行也?故用二分之貝、桔,必得一分之巴豆以佐之,則清陽升而濁陰降,結硬斯可得而除矣。和以白飲之甘,取其留戀於胃,不使速下,「散以散之」比「湯以蕩之」者尤為的當也。服之而病在膈上必吐,在膈下者必利,以本症原自吐利,因胸下結鞕而暫止耳。今因其勢而利導之,使還其出路,則結鞕自散也。然此劑非欲其吐,本欲其利,亦不欲其過利。故不利進熱粥一杯,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,此又「復方」之妙理歟!仲景每用粥為反佐者,以草木之性各有偏長,惟稼穡作甘為中和之味,人之精神血氣皆賴之以生。故桂枝湯以熱粥發汗,理中湯以熱粥溫中,此以熱粥導利,復以冷粥止利,神哉!東垣云:「淡粥為陰中之陽,所以利小便。」則利水之劑,未始不可用也。今人服大黃後用冷粥止利,尚是仲景遺意乎?此證叔和編在《太陽篇》中「水潠」病後,云「寒實結胸無熱症者,與三物小陷胸湯,白散亦可服」。按:本論小陷胸湯是黃連、栝婁、半夏三物,而貝母、桔梗、巴豆亦是三物。夫黃連、巴豆,寒熱天淵,豈有可服黃連之症,亦可服巴豆之理?且此外更無別方,則當云「三物小陷胸湯為散亦可服」。如云「白散亦可服」,是二方矣。而方後又以「身熱皮粟」一叚襍之,使人昏昏不辨。今移之太陰「胸下結鞕」之後,其症其方,若合符然。 |
太陽病表熱未除而反下之,熱邪與水氣相結形成實熱結胸。太陰病腹滿時痛而反下之,寒熱相結形成寒實結胸。大、小陷胸湯之所以用苦寒之藥,是因為有熱邪。這裏是無熱證,就不能一概用治陽證之法治療。三物小陷胸湯,就是「白散」。因為結硬而不很痛,所以亦以「小」來命名。而三物均為白色,為了與小陷胸湯之黃連作區別,所以用「白」來命名。在太陽病中或用湯劑或用丸劑,在太陰病中則或用湯劑或用散劑,這是根據病機而定。貝母善於疏通心胸鬱結之氣,桔梗能提升胸中下陷之氣。然而微寒之藥不足以戰勝結硬之陰邪,如果不用辛熱之巴豆斬關而入,怎麼能使胸中之陰氣流通呢?因此用二分貝母和桔梗,必須要用一分巴豆來輔助,則清陽上升而濁陰下降,結硬就可以被消除。用甘味之白飲調服,取其留戀於胃中而不迅速下行,「散以散之」比「湯以蕩之」更為合適。服藥後,若病位在膈上則必吐,病位在膈下者必利,因為本證原本就有吐利,只是因為胸下結硬而暫時沒有吐利。現在對其加以因勢利導,使邪氣有出路,則結硬自散。然而服用此方並非希望涌吐,而是希望病者能下利,同時亦不希望過度下利。因此,若沒有下利則進食一杯熱粥,而下利太過則進食一杯冷粥,這又是「復方」之妙理啊!仲景之所以常常用粥作為反佐,是因為穀物之甘而有中和之味,人之精神和血氣皆賴此而生。因此,桂枝湯用熱粥發汗,理中湯用熱粥溫中,而這裏以熱粥引導下利,又以冷粥止利,真是神奇啊!李東垣說:「淡粥為陰中之陽,所以能利小便。」那麼對於利水之方而言,未必不能用粥。如今人們在服用大黃後服冷粥來止瀉,難道是仲景所留下之意嗎?王叔和將本證編在《太陽篇》「水潠」之後,並說:「寒實結胸無熱證者,與三物小陷胸湯,白散亦可服。」按:《傷寒論》中小陷胸湯由黃連、栝蔞、半夏三味藥組成,而貝母、桔梗、巴豆亦是三味藥。黃連和巴豆寒熱之性有天淵之別,難道有可服黃連之證候,同時亦可以服巴豆之道理嗎?而且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方,那麼就應當說「三物小陷胸湯為散亦可服」。既然說「白散亦可服」,那就是二個方了。而方後注又將「身熱皮粟」一段文字混雜其中,使人迷糊無法辨識。現在將本證移於太陰病「胸下結硬」之後,那麼其證與其方,能就相符了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麻仁丸 杏仁 芍藥 枳殼 厚朴 大黃 麻仁 |
||
|
土為萬物之母者,以其得和平之氣也。濕土不能生草木,然稻、藕、菱、芡等物,亦有宜於水者。若燥土堅硬,無水以和之,即不毛之地矣。凡胃家之實,多因於陽明之熱結,而亦有因太陰之不開者,是「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」,故名為「脾約」也。承氣諸劑只能清胃,不能扶脾。如病在倉卒,胃陽實而脾陰不虛,用之則胃氣通而大便之開闔如故。若無惡熱、自汗、煩躁、脹滿、譫語、潮熱等症,飲食、小便如常,而大便常自堅硬,或數日不行,或出之不利,是謂之「孤陽獨行」。此太陰之病不開,而穢汙之不去,乃平素之蓄積使然也。慢而不治,則飲食不能為肌肉,必至消瘦而死。然府病為客,藏病為主,治客須急,治主須緩。病在太陰,不可盪滌以取效,必久服而始和。蓋陰無驟補之法,亦無驟攻之法。故取麻仁之甘平入脾,潤而多脂者為君。杏仁之降氣利竅,大黃之走而不守者為臣。芍藥之滋陰斂液,與枳、朴之消導除積者為佐。煉蜜為丸,少服而漸加焉,以和為度。此調脾承氣,推陳致新之和劑也。使脾胃「更虛更實」,而「受盛」、「傳道」之官,各得其職,津液相成,精血相生,神氣以清,內外安和,形體不敝矣。 |
土為萬物之母者,以其得和平之氣也。濕土不能生草木,然稻、藕、菱、芡等物,亦有宜於水者。若燥土堅硬,無水以和之,即不毛之地矣。凡胃家之實,多因於陽明之熱結,而亦有因太陰之不開者,是「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」,故名為「脾約」也。承氣諸劑只能清胃,不能扶脾。如病在倉卒,胃陽實而脾陰不虛,用之則胃氣通而大便之開闔如故。若無惡熱、自汗、煩躁、脹滿、譫語、潮熱等症,飲食、小便如常,而大便常自堅硬,或數日不行,或出之不利,是謂之「孤陽獨行」。此太陰之病不開,而穢汙之不去,乃平素之蓄積使然也。慢而不治,則飲食不能為肌肉,必至消瘦而死。然府病為客,藏病為主,治客須急,治主須緩。病在太陰,不可盪滌以取效,必久服而始和。蓋陰無驟補之法,亦無驟攻之法。故取麻仁之甘平入脾,潤而多脂者為君。杏仁之降氣利竅,大黃之走而不守者為臣。芍藥之滋陰斂液,與枳、朴之消導除積者為佐。煉蜜為丸,少服而漸加焉,以和為度。此調脾承氣,推陳致新之和劑也。使脾胃「更虛更實」,而「受盛」、「傳道」之官,各得其職,津液相成,精血相生,神氣以清,內外安和,形體不敝矣。 |
|
|
右太陰五方。按:諸經皆有溫散、溫補法,惟少陽不用溫。諸經皆有益陰、清火法,惟太陰忌寒涼。若熱病傳經有嗌乾等症,仍當清火。素有「脾約」大便不順,亦當滋陰。要知制方,全在活法,不可執也。
|
上述是太陰病五方。按:各經病都有溫散、溫補之法,只有少陽病不用溫補。各經病都有益陰、清火之法,只有太陰病忌用寒涼。如果熱病傳經而見嗌乾等證,仍需清火。如果素來「脾約」而大便不暢,亦需要滋陰。關鍵要知道制定方劑全在於靈活運用,不可固執不變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少陰方總論 |
||
|
仲景以病分六經,而製方分表裏寒熱虛實之六法,六經中各具六法而有偏重焉。太陽偏於表寒,陽明偏於裏熱,太陰偏於虛寒,厥陰偏於實熱,惟少陽與少陰司樞機之職,故無偏重。而少陽偏於陽,少陰偏於陰,製方亦因之而偏重矣。然少陰之陰中有陽,故其表症根於裏,熱證因於寒。治表症先顧其裏,熱症多從寒治者,蓋陰以陽為主,固腎中之元陽,正以存少陰之真陰也。其或陽盛陰虛,心煩不得臥,見於二三日中,可用芩、連者,無幾耳。腎本無實,實症必轉屬陽明,亦由少陰之虛。知其虛,得其機矣。 |
仲景將傷寒病分為六經,而製方則分表、裏、寒、熱、虛、實之六法,六經中各自具有此六法,但有所偏重。太陽病偏重表寒,陽明病偏重裏熱,太陰病偏重虛寒,厥陰病偏重實熱,只有少陽與少陰擔任樞機之職,因此沒有明顯偏重。但少陽偏重於陽,少陰偏重於陰,製方亦因此而有所偏重。然而,少陰為陰中有陽,所以其表證是根源於裏,熱證則由寒而引起。治療表證首先要考慮其裏,治療熱證則多從寒治療,這是因為陰以陽為主,固護腎中之元陽,正是為了保存少陰之真陰。其中或者會有陽盛陰虛,心煩不得臥見於得病二三日,而可以用黃芩、黃連等藥,這並不多見。腎病本身並無實證,實證必然會轉屬陽明,亦是由於少陰之虛弱所致。知道少陰病之虛,即能得其治療之機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麻黃附子細辛湯 |
||
|
麻黃附子甘草湯 |
||
|
少陰主裏,應無表症。病發於陰,應無發熱。今始受風寒即便發熱,似乎太陽而屬之少陰者,以頭不痛而但欲寐也。《內經》曰:「逆冬氣而少陰不藏,腎氣獨沉。」故少陰之發熱而脉沉者,必於表劑中加附子以預固其裏。蓋腎為坎象,二陰不藏,則一陽無蔽,陰邪因得以內侵,孤陽無附而外散耳。夫太陽為少陰之表,發熱無汗,太陽之表不得不開。沉為在裏,少陰之本不得不固。設用麻黃開腠理,細辛散浮熱,而無附子以固元氣,則少陰之津液越出,太陽之微陽外亡,去生遠矣。惟附子與麻黃並用,內外咸調,則風寒散而陽自歸,精得藏而陰不擾。此裏病及表,脉沉而當發汗者,與表病及裏,脉浮而可發汗者徑庭矣。若得之二三日,表熱尚未去,裏症亦未見,麻黃未可去,當以甘草之和中,易細辛之辛散。佐使之任不同,則麻黃之勢亦減,取微汗而痊,是又少陰發表之輕劑矣。二方皆少陰中風托裏觧外法。 |
少陰主裏,不應有表證。病發於陰,不應有發熱。如今剛受風寒便見發熱,似乎屬於太陽但卻歸屬於少陰病者,是因為頭不痛而但欲寐。《內經》說:「逆冬氣而少陰不藏,腎氣獨沉。」因此少陰病見發熱而脈沉者,必須在治表劑中加附子以預先固護裏氣。因為腎屬坎卦之象,二陰不藏,則一陽就無所遮掩,陰邪因此得以內侵,孤陽無所依附而外散。太陽為少陰之表,發熱無汗,則太陽之表氣不得不開。脈沉為病在裏,則少陰之本不得不固。假設用麻黃開泄腠理,細辛外散浮熱,而沒有附子來固守元氣,則少陰之津液外出,太陽之微陽隨之消亡,則有生命危險。只有附子與麻黃並用,內外調和,則風寒外散而陽氣自歸,精氣得藏而陰氣不受干擾。這是裏病及表,脈沉而需要發汗者,與表病及裏,脈沉而可發汗者大相徑庭。如果得病二三日,表熱仍在,裏證亦未見,麻黃不可去,應以甘草之和中,取代細辛之辛散。佐使之藥物不同,則麻黃發散之力亦會減弱,服藥後取微汗而愈,這又是少陰病發散表邪之輕劑。此二方都是治療少陰病中風,托裏解外之治法。 |
|
|
風本陽邪,雖在少陰中而即發,不拘於五六日之期。用細辛、麻黃者,所以治風,非以治寒也。用附子者,所以固本,非「熱因熱用」也。寒本陰邪,即在太陽,熱不遽發,故有「或未發」之辭。麻黃、桂枝,長於治風,而非治寒之主劑,故主治在發熱惡寒。若無熱惡寒者,雖有頭項強痛之表急,當㕥四逆、真武輩救其裏矣。蓋病發於陰,便已亡陽,不得以「汗多亡陽」一語為談柄也。少陰製麻附細辛方,猶太陽之麻黃湯,是急汗之峻劑。製麻附甘草湯,猶太陽之桂枝湯,是緩汗之和劑。蓋太陽為陽中之陽而主表,其汗易發,其邪易散,故初用麻黃、甘草而助以桂枝,次用桂枝、生姜而反佐以芍藥。少陰為陰中之陰而主裏,其汗最不易發,其邪最不易散,故用麻黃、附子而助以細辛,其次亦用麻黃、附子而緩㕥甘草。則「少陰中風,脉陽微陰浮者,為欲愈」,非必須陰出之陽而觧耶。然必細審其脉沉而無裏症者,可發汗,即知脉沉而症為在裏者,不可發汗矣。此等機關,必須看破。人皆謂麻黃治太陽之傷寒,而不知仲景用以治少陰之中風。且麻黃在太陽,只服八合,不必盡劑,妙在更發汗,則改用桂枝。在少陰「始得之」與「二三日」,皆可溫服一升,日三服。則《湯液本草》分麻黃為太陽經藥,猶「掘井得泉」,而曰「水專在是」矣。 |
風本為陽邪,雖然在少陰病中感而即發,並不受五六日之期所限。使用細辛、麻黃之目的是治風而非治寒。用附子是為了固本,而非「熱因熱用」。寒邪本屬於陰,即使是太陽病,發熱亦不會立即出現,因此有「或未發」之說。麻黃湯、桂枝湯擅長治療風邪,而不是治療寒邪之主方,因此主治在於發熱惡寒。如果是無熱惡寒,雖然有頭頸強痛之表證非常急迫,亦應當用四逆湯、真武湯等方以救其裏。因為病發於陰,便已亡陽,不能拘泥於「汗多亡陽」之說。少陰病有麻黃附子細辛湯,猶如太陽病有麻黃湯,是迅速發汗之峻劑。而有麻黃附子甘草湯,猶如太陽病有桂枝湯,是緩慢發汗之和劑。因為太陽為陽中之陽而主表,其汗易發,邪氣易於外散,因此最初用麻黃、甘草以助桂枝,其次用桂枝、生薑而用芍藥反佐。少陰為陰中之陰而主裏,其汗最不易發,邪氣最不易外散,因此用麻黃、附子而以細辛輔助;其次亦用麻黃、附子而以甘草緩之。則「少陰中風,脈陽微陰浮者,為欲愈」,就不一定要陰出於陽才能得解。然而必須仔細審察其脈沉而無裏證者,才可發汗,這樣就知道脈沉而有裏證者,便不可發汗。必須要看破此等機關。人們都認為麻黃是治太陽病之傷寒,而不知道仲景用來治療少陰病之中風。而且在太陽病中麻黃湯只需服八合,不必完全服盡,其巧妙之處在於如果需要再發汗,則改用桂枝湯。而治療少陰病之中風,不論「始得之」或得之「二三日」,都可以溫服一升,每日服三次。這樣來看,《湯液本草》將麻黃歸為太陽經藥,就好比「掘井得泉」,卻說「水專在是」一樣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附子湯 人參 白朮 附子 茯苓 芍藥 |
||
|
此大溫大補之方,乃正治傷寒之藥,為少陰固本禦邪之劑也。夫傷則宜補,寒則宜溫,而近世治傷寒者,皆以寒涼剋伐相為授受,其不講於「傷寒」二字之名實久矣。少陰為陰中之陰,又為陰水之藏,故傷寒之重者,多入少陰。所以少陰一經,最多死症。如「少陰病,身體痛,手足寒,骨節痛,口中和,惡寒,脉沉者」,是純陰無陽之症,方中用生附二枚,取其力之銳,且以重其任也。蓋少火之陽,鼓腎間動氣以禦外侵之陰翳,則守邪之神有權,而呼吸之門有鎖鑰,身體骨節之痛自除,手足自溫,惡寒自罷矣。以人參固生氣之原,令五臟六府之有本,十二經脉之有根,腎脉不獨沉矣。三陰以少陰為樞,設使扶陽而不益陰,陰虛而陽無所附,非治法之善也。故用白朮以培太陰之土,芍藥以滋厥陰之木,茯苓以利少陰之水。水利則精自藏,土安則水有所制,木潤則火有所生矣。扶陽以救寒,益陰以固本,此萬全之術。其畏而不敢用,束手待斃者,曷可勝計耶?此與麻黃附子湯,皆治少陰表症而大不同。彼因病從外來,表有熱而裏無熱,故當溫而兼散。此因病自內出,表裏俱寒而上虛,故大溫大補。然彼發熱而用附子,此不熱而用芍藥,是又陰陽互根之理歟!此與真武湯似同而實異。此倍朮、附去姜而用參,全是溫補以壯元陽。彼用姜而不用參,尚是溫散以逐水氣。補散之分歧,只在一味之旋轉歟! |
此是大溫大補之方,是正治傷寒之藥,為少陰病固本禦邪之方。受傷則應該補益,受寒則應該溫養,然而近代治療傷寒病者,相互授受都以寒涼藥剋伐陽氣為主,對於「傷寒」二字之真實意義已經很久沒有研究了。少陰為陰中之陰,又是陰水之臟,因此傷寒病之嚴重者,多數入於少陰。所以少陰病是最多死證。譬如「少陰病,身體痛,手足寒冷,關節痛,口中和,惡寒,脈沉者」,是純陰無陽之證,方中用兩枚生附子,取其銳利之力,而且令其擔當重任。因為少火之陽,可以鼓動腎間動氣以抵禦外侵之陰寒,這樣身體才有能力抵抗外邪,使呼吸正常,身體骨節之疼痛就會自除,手足自溫,惡寒自止。用人參鞏固生命之根源,使五臟六腑之氣有本,十二經脈之氣有根,腎脈不會獨沉。三陰病以少陰為樞,如果扶助陽氣而不補益陰氣,陰虛則陽無所依附,治法就不能盡善。所以用白朮培補太陰之土氣,芍藥滋養厥陰之木氣,茯苓滲利少陰之水。水利則精氣自然斂藏,土氣安則水氣有所制約,木氣得到滋潤則火氣有所生長。扶助陽氣以治寒證,補益陰氣以固守根本,這才是萬全之策。那些畏懼而不敢用,束手待斃之人,如何能數得過來呢?此方與麻黃附子湯都是治少陰表證,卻大不相同。後者之病從外而來,表有熱而裏無熱,所以需要溫補兼散邪。本證是病從內而出,表裏俱寒而上焦虛弱,所以需要大溫大補。雖然後者有發熱而用附子,本證不發熱而用芍藥,這又是陰陽互根之理啊!此方與真武湯看似相同但實際卻不同。本方倍用白朮、附子,去生薑而用人參,全是溫補以壯元陽。真武湯用生薑卻不用人參,仍然是溫散以逐水氣。二方補與散之不同,只在一味藥之變化而已!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真武湯 附子 生姜 白朮 茯苓 芍藥 |
||
|
真武,主北方水也。坎為水,而一陽居其中,柔中之剛,故名「真武」。取此名方者,所以治少陰水氣為患也。蓋水體本靜,其動而不息者,火之用耳。若坎宮之火用不宣,則腎家之水體失職,不潤下而逆行,故中宮四肢俱病。此腹痛下利、四肢沉重疼痛、小便不利者,由坎中陽虛,下焦有寒不能制水故也。法當壯元陽以消陰翳,培土泄水以消留垢。故君大熱之附子以奠陰中之陽,佐芍藥之酸苦以收炎上之氣,茯苓淡滲止潤下之體,白朮甘溫制水邪之溢,生姜辛溫散四肢之水。使少陰之樞機有主,則開闔得宜,小便得利,下利自止,腹中四肢之邪觧矣。若兼咳者,是水氣射肺所致,加五味之酸溫,佐芍藥以收腎中水氣,細辛之辛溫,佐生姜以散肺中水氣,而咳自除。若兼嘔者,是水氣在胃,因中焦不和,四肢亦不治,此病不涉少陰,由於太陰濕化不宣也。與治腎水射肺者不同法,不須附子以溫腎水,倍加生姜以散脾濕,此為和中之劑而非治腎之劑矣。若大便自利而下利者,是胃中無物,此腹痛因於胃寒,四肢因於脾濕,故去芍藥之陰寒,加乾姜以佐附子之辛熱。即茯苓之甘平者亦去之,此為溫中之劑而非利水之劑矣。要知真武加減與小柴胡不同。小柴胡為少陽半表之劑,只不去柴胡一味,便可名「柴胡湯」。真武以五物成方,為少陰治本之劑,去一味便不成「真武」。故去姜加參,即名「附子湯」,於此見制方有陰陽動靜之別也。
|
真武,主北方之水。坎為水,而一陽居於其中,柔中有剛,因此被命名為「真武」。以此作為方劑之命名,就是為了用來治療少陰之水氣病。因為水之體本身是靜態的,水之所以不斷地運行,是因為有火在發揮作用。如果坎中之火不能宣發,則腎中之水失於運化,不潤下則逆行,所以中宮與四肢都會發病。這裏所見腹痛下利、四肢沉重疼痛、小便不利等證,是由於坎中陽虛,下焦有寒而不能制水所致。治法上應該壯元陽以消陰翳,培土泄水以清除淤積。所以用大熱之附子以壯陰中之陽,佐以酸苦之芍藥收斂上炎之氣,茯苓淡滲以止水之潤下,白朮甘溫以制水邪之泛溢,生薑辛溫以散四肢之水。使得少陰之樞機恢復正常,則開合得當,小便得利,下利自止,腹中和四肢之邪氣得以消散。如果兼有咳嗽,是水氣上射於肺所致,加酸溫之五味子,輔以芍藥以收斂腎中之水氣,用辛溫之細辛,輔以生薑以散發肺中之水氣,則咳自除。如果兼有嘔吐,是水氣在胃中,因為中焦不和,四肢亦失和,此病與少陰無關,而是由於太陰之濕氣不能宣散所致。與治療腎水上射於肺不同,不需要附子以溫腎水,反而倍用生薑以散脾濕,因此這是和中之劑而不是治腎之方。如果大便自利而下利者,那是因為胃中無物,此時腹痛是因於胃寒,四肢沉重疼痛是因於脾濕,因此去陰寒之芍藥,加乾薑以輔助辛熱之附子。就算是甘平之茯苓亦應去除,因為這是溫中之劑而不是利水之方。關鍵要知道真武湯之加減法與小柴胡湯之加減法不同。小柴胡湯是治療少陽病半表之方,只要不去柴胡,就可以稱之為「柴胡湯」。真武湯由五味藥物組成,作為少陰病治本之方,去任何一味藥就不再是「真武湯」。因此去生薑加人參,即稱為「附子湯」,由此可見制方有陰陽動靜之不同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白通湯 葱白 乾姜 附子 |
||
|
白通加猪胆汁湯 |
||
|
白通者,通下焦之陰氣以達於上焦也。少陰病,自利而渴,小便色白者,是下焦之陽虛。而陰不生少火,不能蒸動其水氣而上輸於肺,故渴。不能生土,故自利耳。法當用姜、附以振元陽,而不得升驣之品,則利止而渴不能止,故佐葱白以通之。葱白稟西方之色味,入通於肺,則水出高源而渴自止矣。凡陰虛則小便難,下利而渴者,小便必不利,或出濇而難,是厥陰火旺,宜猪苓、白頭翁輩。此小便色白,屬少陰火虛,故曰「下焦虛」,又曰「虛故引水自」救。「自救」者,自病人之意,非醫家之正法也。若厥陰病欲飲水者,少少與之矣。 |
白通,能通下焦之陰氣以使其到達上焦之意。少陰病,下利而渴,小便色白者,屬於下焦陽虛。而陰氣不化生少火,不能蒸發水液而上輸於肺,所以口渴。不能生土氣,所以會自利。治法上應該用乾薑和附子來振奮元陽,但如果沒有升騰陽氣之藥,則下利雖止而口渴不能止,因此佐以蔥白來通達陽氣。蔥白稟受西方之色與味,能入通於肺,如此則水出高源而口渴自止。凡是陰虛則小便難,下利而渴者,小便必然不利,或者艱澀而難出,這屬於厥陰火旺,應該用豬苓湯、白頭翁湯等方。這裏是小便色白,屬於少陰火虛,因此稱之為「下焦虛」,又說「虛故引水自救」。所謂「自救」,是患者自己之想法,而不是醫者所定之治法。譬如厥陰病欲飲水者,可以少少與之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通脉四逆湯 甘草 乾姜 附子 葱 |
||
|
下利清穀,裏寒外熱,手足厥逆,脉微欲絕,此太陰壞症轉屬少陰之症,四逆湯所主也。而但欲寐,是繫在少陰。若反不惡寒,或咽痛、乾嘔,是為亡陽。其人面赤色,是為戴陽。此下焦虛極矣,恐四逆之劑不足以起下焦之元陽而續欲絕之脉。故倍加其味,作為大劑,更加葱以通之。葱稟東方之色,能行少陽生發之機,體空味辛,能入肺以行營衛之氣。姜、附、參、甘,得此以奏捷於經絡之間而脉自通矣。脉通則虛陽得歸其部,外熱自觧而裏寒自除,諸症無虞矣。按:本方以陰症似陽而設,症之異於四逆者,在不惡寒而面色赤,方之異於四逆者,若無葱,當與桂枝加桂、加芍同矣。何更加以「通脉」之名?夫人參所以通血脉,安有脉欲絕而不用者?舊本乃於方後云「面赤色者加葱,利止脉不出者加參」,豈非抄錄者之疏失於本方,而蛇足於加法乎?且減法所云「去」者,去本方之所有也。而此云「去」葱、芍、桂者,是後人之加減可知矣。 |
下利清穀,裏寒外熱,手足厥逆,脈微欲絕,這是太陰病壞病轉屬少陰之病證,為通脈四逆湯所主治。而但欲寐,則屬於少陰病。如果反不惡寒,或咽痛、乾嘔,則是亡陽。其人面色赤,則為戴陽。這是下焦已經虛極,恐怕四逆湯不足以啟動下焦之元陽而維持欲絕之脈。因此加倍其劑量,成為大劑,並加蔥白以通其陽氣。蔥白稟受東方之色,能行少陽生發之機,其體空而味辛,能入於肺以行營衛之氣。乾薑、附子、人參、甘草得蔥白則能在經絡之間快速發揮作用而使脈氣自通。脈氣通則虛陽得以回歸其位,外熱自解而裏寒自除,各證都會消失。按:本方是為陰證似陽而設立,與四逆湯證不同之處在於不惡寒而面色赤,與四逆湯方不同之處在於,如果不加蔥白,則與桂枝加桂湯、桂枝加芍藥湯相同。為何更以「通脈」命名此方呢?人參能通血脈,怎麼會有脈欲絕而不用呢?舊版卻於方後注說「面赤色者加蔥,利止脈不出者加參」,難道不是抄錄者之失當,而在加減法上有畫蛇添足之舉嗎?而且減法所說「去」之藥物,都是去除本方所應該有之藥物。而此處所說「去」蔥白、芍藥、桂枝,可知是後人之加減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茯苓四逆湯 茯苓 人參 甘草 乾姜 附子 |
||
|
乾姜附子湯 |
||
|
「發汗若下之,病仍不觧,煩躁者,茯苓四逆湯主之。」「下後復發汗,晝日煩躁不得眠,夜則安靜,不嘔不渴,無表症,脉微沉,身無大熱者,乾姜附子湯主之。」此二條皆太陽壞病轉屬少陰也。凡太陽病而妄汗、妄下者,其變症或仍在太陽,或轉屬陽明,或轉係少陽,或繫在太陰,皆是陽氣為患。若汗而復下,或下而復汗,陽氣喪亡,則轉屬少陰矣。此陽症變陰,陰症似陽,世醫多不能辨。用涼藥以治煩躁,鮮有不速其斃者。由不知太陽以少陰為裏,少陰為太陽之根源也。脉至少陰則沉微,邪入少陰則煩躁。煩躁雖六經俱有,而兼見於太陽、少陰者,太陽為真陰之標,少陰為真陰之本也。陰陽之標本,皆從煩躁見。煩躁之虛實,又從陰陽而分。如未經汗下而煩躁,屬太陽,是煩為陽盛,躁為陰虛矣。汗下後煩躁屬少陰,是煩為陽虛,躁為陰竭矣。陰陽不相附,故煩躁。其亡陽、亡陰,又當以汗之先後,表症之觧不觧為之詳辨。則陰陽之差多差少,不致溷淆,而用方始不誤矣。先汗後下,於法為順。而表仍不觧,是妄下亡陰,陰陽俱虛而煩躁也,故製茯苓四逆固陰以收陽。先下後汗,於法為逆,而表症反觧,內不嘔渴,似於陰陽自和,而實妄汗亡陽,所以虛陽擾於陽分,晝則煩躁也,故專用乾姜附子固陽以配陰。二方皆從四逆加減,而有救陽、救陰之異。茯苓感天地太和之氣化,不假根而成,能補先天無形之氣,安虛陽外脫之煩,故以為君。人參配茯苓補下焦之元氣,乾姜配生附回下焦之元陽,調以甘草之甘,比四逆為緩,固裏宜緩也。姜、附者,陽中之陽也,用生附而去甘草,則勢力更猛,比四逆為峻,回陽當急也。一去甘草,一加茯苓,而緩急自別。加減之妙,見用方之神乎! |
「發汗若下之,病仍不解,煩躁者,茯苓四逆湯主之。」「下後復發汗,晝日煩躁不得眠,夜而安靜,不嘔不渴,無表證,脈微沉,身無大熱者,乾薑附子湯主之。」此兩條都是太陽病壞病轉屬少陰。凡是太陽病而誤用發汗、攻下者,其變證有時仍停留在太陽,或轉屬陽明,或轉系少陽,或轉屬太陰,都屬於陽氣所病。如果發汗後再攻下,或者攻下後又發汗,陽氣消亡,則轉屬為少陰病。這是陽證變陰,陰證似陽,世醫多數不能辨識。用涼藥以治煩躁,很少不加速其死亡者。因為不知道太陽以少陰為裏,少陰是太陽陽氣之根源。病至少陰則脈沉微,邪入少陰則煩躁。雖然六經病中皆有煩躁,但如果同時兼見太陽和少陰病時,太陽是真陰之標,少陰是真陰之本。陰陽之標本皆可以從煩躁而見。而煩躁之虛實,又可以從陰陽而分。譬如沒有經過汗下而煩躁,屬於太陽之病,此時煩為陽盛而躁為陰虛。汗下後而煩躁則屬於少陰之病,此時煩為陽虛而躁為陰竭。陰陽不相應,所以煩躁。而對於亡陰、亡陽,又要根據發汗之先後,表證之解否來進行詳細辨別。這樣才能確保對於陰陽之虛實不至於混淆,從而用方才能正確。先發汗後攻下,在治法上是對的。而表證仍未解,是誤下後亡陰,陰陽俱虛而煩躁,所以製茯苓四逆湯鞏固陰氣以收斂陽氣。先攻下後發汗,在治法上是錯的,而表證反而得解,裏證不嘔不渴,似乎是陰陽自和,但實際上是誤汗而亡陽,所以虛陽擾於陽分,白天則煩躁,所以專門用乾薑附子湯鞏固陽氣以和陰氣。此兩方都是從四逆湯加減而來,但有救陽與救陰之不同。茯苓感受天地太和之氣所化,不依賴樹根而形成,能補先天無形之氣,安定由於虛陽外脫所致之煩躁,因此作為君藥。人參配茯苓補益下焦之元氣,乾薑配生附子回復下焦之元陽,再調以甘草之甘,比四逆湯之力為緩,因為鞏固裏氣宜用緩和之法。乾薑和附子都是陽中之陽,用生附子而去甘草,則作用更加強烈,比四逆湯之力為猛,因為回陽就應該迅速。從四逆湯中,一方去甘草,一方加茯苓,其緩急之用自然分明。方劑加減之妙,就可見用方之神啊!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吳茱萸湯 吳茱萸 人參 生姜 大棗 |
||
|
少陰吐利、手足厥冷、煩躁欲死者,此方主之。按:「少陰病吐利、煩躁、四逆者死」,此何復出治方?要知「欲死」是不死之機,「四逆」是兼脛臂言。「手足」只指指掌言,稍甚、微甚之別矣。岐伯曰:「四末陰陽之會,氣之大路也。四街者,氣之經絡也。絡絕則經通,四末觧則氣合從。」合在肘膝之間,即「四街」也,又謂之「四關」。夫四郊擾攘,而關中猶固,知少陰生氣猶存。然五藏更相生,不生即死。少陰之生氣注於肝,陰盛水寒,則肝氣不舒而木鬱,故煩躁。肝血不榮於四末,故厥冷。木欲出地而不得出,則中土不寧,故吐利耳。病本在腎而病機在肝,不得相生之機,故欲死。勢必溫補少陰之少火,以開厥陰之出路。生死關頭,非用氣味之雄猛者,不足以當絕處逢生之任也。吳茱萸辛苦大熱,稟東方之氣色,入通於肝,肝溫則木得遂其生矣。苦以溫腎,則水不寒。辛以散邪,則土不擾。佐人參固元氣而安神明,助姜、棗調營衛以補四末。此撥亂反正之劑,與麻黃、附子之拔幟先登,附子、真武之固守社稷者,鼎足而立也。若命門火衰,不能腐熟水穀,故食穀欲嘔。若干嘔、吐涎沫而頭痛,是脾腎虛寒,陰寒上乘陽位也。用此方鼓動先天之少火,而後天之土自生。培植下焦之真陽,而上焦之寒自散。開少陰之關而三陰得位者,此方是歟?
|
少陰吐利、手足厥冷、煩躁欲死者,用此方主治。按:「少陰病吐利、煩躁、四逆者死」,這裏為什麼又提出治療之方呢?關鍵要知道「欲死」則內含不死之機,「四逆」是包括上肢、下肢而言。「手足」只是指手指和掌心,程度上有微甚之別。岐伯說:「四肢末端是陰陽會合之處,是氣之大路。四街,是氣之經絡。絡脈絕則經脈自通,四末通則氣能相合。」氣合於肘膝之間,即「四街」,亦稱為「四關」。當四郊動亂而關中尚且穩固時,可知少陰之生氣仍然存在。然而,五臟之相生相克,不相生即死。少陰之生氣注入肝,陰盛水寒,則肝氣不舒而木氣鬱,所以煩躁。肝血不榮於四末,所以手足厥冷。木氣欲出於地而不能出,則中土不寧,所以嘔吐下利。病之本在於腎而病機則在於肝,不能得到相生之機,所以欲死。治法上必須溫補少陰之少火,以開啟厥陰之出路,生死關頭,不用氣味雄烈之藥物,不足以勝任絕處逢生之重任。吳茱萸味辛苦而氣大熱,稟受東方之氣色,能入通於肝,肝氣得溫則木氣能恢復其生發之性。苦能溫腎,則水不寒。辛以散邪,則土氣不被擾動。佐以人參固元氣而安神明,助以生薑、大棗調和營衛以補益四肢。這是撥亂反正之方,與麻黃湯、附子湯捷足先登而拔旗幟,附子湯和、真武湯能守護社稷,共同形成三足鼎立之局面。如果是命門火衰,無法腐熟水穀,則食穀欲嘔。如果乾嘔、吐涎沫而頭痛,是脾腎虛寒,陰寒上乘陽位所致。用此方可以鼓動先天之少火,則後天之土氣自然能得以相生。培補下焦之真陽,則上焦之寒氣自散。開啟少陰之關而使三陰各得其位,就是此方嗎?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黃連阿膠湯 黃連 阿膠 黃芩 芍藥 雞子黃 |
||
|
內膠烊盡少冷,內雞子黃攪令相得,溫服七合,日三服,此少陰之瀉心湯也。凡瀉心必藉芩、連,而導引有陰陽之別。病在三陽,胃中不和而心下痞鞕者,虛則加參、甘補之,實則加大黃下之。病在少陰而心中煩不得臥者,既不得用參、甘以助陽,亦不得用大黃以傷胃矣。用黃連以直折心火,佐芍藥以收斂神明,所以扶陰而益陽也。然以「但欲寐」之病情,而至於「不得臥」,以「微細」之病脉,而反見「心煩」,非得氣血之屬以交合心腎,甘平之味以滋陰和陽,不能使水升而火降。陰火不歸其部,則少陰之熱不除。雞子黃稟南方之火色,入通於心,可以補離宮之火。用生者攪和,取其流動之義也。黑驢皮稟北方之水色,且醎先入腎,可以補坎宮之精,內合於心而性急趨下,則阿井有水精凝聚之要也。與之相溶而成膠,用以配雞子之黃,合芩、連、芍藥,是降火歸原之劑矣。《經》曰「火位之下,陰精承之」,「陰平陽秘,精神乃治」,斯方之謂歟? |
加入阿膠烊化盡,稍涼後加入雞蛋黃攪拌均勻,溫服七合,每日服三次,這是治療少陰病之瀉心湯。凡是瀉心湯必定要借助黃連和黃芩,但導引之藥有陰陽之不同。對於三陽病,胃中不和而心下痞硬者,虛者加人參和甘草以補之,實則加大黃以下之。病在少陰而心中煩不得臥者,既不能用人參、甘草以助陽,亦不能用大黃以防傷及胃氣。用黃連以直接抑制心火,輔以芍藥收斂神明,因此能扶陰益陽。然而,從「但欲寐」之病情發展到「不得臥」,從「微細」之病脈,反而又出現心煩,如果不用氣血之品來使心腎交合,不用甘平之味來滋養陰陽,則無法使水升而火降。陰火不能歸其位,則少陰之熱無法消除。雞蛋黃稟受南方之火色,能入通於心,可以補益離宮之火。用生雞蛋黃攪拌均勻,取其流動之義。黑驢皮稟受北方之水色,而且味鹹能先入於腎,可以補益坎宮之精,內合於心而其性質急速下行,如此則阿井之水才能發揮水精凝聚之作用。用阿井之之與之相溶而製成阿膠,用以配合雞蛋黃,合上黃芩、黃連、芍藥,則本方是降火歸原之劑。《內經》說「火位之下,陰精承之」,「陰平陽秘,精神乃治」,就是指此方而言的嗎?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猪苓湯 猪苓 茯苓 澤瀉 滑石 阿膠 |
||
|
少陰病,得之二三日,心煩不得臥,是上焦實熱,宜黃連阿膠湯清之。少陰病,欲吐不吐,心煩但欲寐,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,是下焦虛寒,宜白通湯以溫之。此少陰初病而下利,似為虛寒,至六七日反見咳而嘔渴、心煩不得臥者,此豈上焦實熱乎?是因下多亡陰,精虛不能化氣,真陽不藏,致上焦之虛陽擾攘而致變症見也。下焦陰虛而不寒,非姜、附所宜。上焦虛而非實熱,非芩、連之任,故製此方。二苓不根不苗,成於太空元氣,用以交合心腎,通虛無氤氳之氣也。阿膠味厚,乃氣血之屬,是「精不足者,補之以味」也。澤瀉氣味輕清,能引水氣上升。滑石體質重墜,能引火氣下降。水升火降,得既濟之理矣。且猪苓、阿膠,黑色通腎,理少陰之本。茯苓、滑石,白色通肺,滋少陰之源。澤瀉、阿膠,醎先入腎,培少陰之體。二苓、滑石,淡滲膀胱,利少陰之用。五味皆甘淡,得土中沖和之氣,是「水位之下,土氣承之」也。五物皆潤下,皆滋陰益氣之品,是「君火之下,陰精承之」也。以此滋陰利水而升津,諸症自平矣。 |
少陰病,得之二三日,心煩不得臥,這是上焦實熱,宜用黃連阿膠湯清熱。少陰病,欲吐卻無法吐出,心煩但欲寐,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,屬於下焦虛寒,宜用白通湯溫之。這是少陰初得病時出現下利,看似虛寒,至六七日反而見咳而嘔吐、口渴、心煩不得臥,這難道是上焦實熱嗎?這是因為下利多而亡陰,精氣虛弱無法化氣,真陽不藏,導致上焦之虛陽擾攘而出現變證。下焦陰虛而不寒,不適宜用乾薑、附子。上焦虛而非實熱,不適宜用黃芩、黃連,因此創製此方。茯苓、豬苓無根無苗,形成於太空元氣,用以交合心腎,與虛無氤氳之氣相通。阿膠味厚,屬於氣血之品,即「精不足者,補之以味」。澤瀉氣味輕清,能引導水氣上升。滑石質地沉重,能引導火氣下降。水升火降,則能達成水火既濟之理。而且豬苓、阿膠,色黑能入腎,調理少陰之本。茯苓、滑石,色白能通肺,滋養少陰之源。澤瀉、阿膠,味鹹能先入腎,培養少陰之體。茯苓、豬苓、滑石,淡滲膀胱,能發揮少陰之用。五味藥都屬甘淡,稟受土中沖和之氣,合符「水位之下,土氣承之」之理。五種藥物都能潤澤下行,都能滋陰益氣,合符「君火之下,陰精承之」之義。用此滋陰利水而升提津液,各種證候自然消失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四逆散 柴胡 枳實 芍藥 甘草 |
||
|
少陰病四逆,泄利下重,其人或咳、或悸、或小便不利、或腹中痛者,此方主之。少陰為水火同處之藏,水火不和,則陰陽不相順接。四肢為陰陽之會,故厥冷四逆,有寒熱之分。胃陽不敷於四肢為寒厥,陽邪內擾於陰分為熱厥。然四肢不溫,故厥者必利。先審瀉利之寒熱,而四逆之寒熱判矣。下利清穀為寒,當用姜、附壯元陽之本。泄瀉下重為熱,故用白芍、枳實酸苦湧泄之品以清之。不用芩、連者,以病於陰而熱在下焦也。更用柴胡之苦平者以升散之,令陰火得以四達。佐甘草之甘涼以緩其下重。合而為散,散其實熱也。用白飲和服,中氣和而四肢之陰陽自接,三焦之熱自平矣。此症以泄利下重,知少陰之陽邪內擾於陰,四逆即非寒症矣。四逆皆少陰樞機無主,升降不利所致,只宜治下重,不須兼治諸症也。仲景因有四逆症,欲以別於四逆湯,故㕥「四逆散」名之。本方有咳者加五味、乾姜,悸者加桂枝,腹痛加附子,泄利下重加薤白,俱非泄利下重所宜。且五味、姜、桂加五分,於附子加一枚,薤白三升,何多寡不同若是?且以散只服方寸匕,恐不濟此症,此後人附會可知也。 |
少陰病四肢逆冷,泄瀉後重,其人或咳、或悸、或小便不利、或腹中痛者,用此方主治。少陰為水火同居之臟,水火不和,則陰陽之氣不能相互順接。四肢是陰陽相會之處,因此厥冷四逆,有寒熱之分。胃陽不能布散於四肢為寒厥,陽邪內擾於陰分則為熱厥。然而四肢不溫,因此厥逆者必然下利。首先要判斷下利是屬寒還是屬熱,則四逆之寒熱屬性就明確了。下利清穀為寒,應當用乾薑、附子以壯元陽之本。泄利後重為熱,因此用酸苦湧泄之白芍、枳實以清熱。不用黃芩、黃連,是因為病在陰分而熱在下焦。更用苦平之柴胡以升散其熱,使陰火得以四散。輔以甘涼之甘草以緩其後重。將藥物合而為散以散其實熱。使用白米湯調服,使中氣調和則四肢之陰陽氣得以順接,三焦之熱自然平熄。此證因為泄利後重,則可知少陰之陽邪內擾於陰,四逆就不是寒證。四逆都是由於少陰之樞機失調,升降不利所致,只需治療泄利後重,不需要同時治療其他證候。仲景因為有四逆證,為了與四逆湯區分,所以取名為「四逆散」。方後注有咳者加五味子、乾薑,心悸者加桂枝,腹痛者加附子,泄利後重者加薤白,這些加減藥都不是泄利後重所應該使用。況且五味子、乾薑、桂枝加五分,附子加一枚,薤白加三升,為什麼用量之多少有如此之不同呢?而且用散劑只服方寸匕,恐怕不能治療此證,可見這些加減法都是後人之穿鑿附會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猪膚湯 猪膚 白蜜 花粉 |
||
|
少陰病多下利,以下焦之虛也。陰虛則陽無所附,故下焦虛寒者,反見上焦之實熱。少陰脉循喉嚨,挾舌本,其支者,出絡心,注胸中。凡腎精不足,腎火不藏,必循經上走於陽分也。咽痛、胸滿、心煩者,因陰併於下而陽併於上,承 不上承於心,火不下交於腎,此未濟之象。猪為水畜而津液在膚,取其膚以治上焦虛浮之火,和白蜜、花粉之甘,瀉心潤肺而和脾。滋化原,培母氣,水升火降,上熱下行,虛陽得歸其部,不治利而利自止矣。三味皆食物,不藉於草,所謂「隨手拈來盡是道」矣。 |
少陰病多有下利,是由於下焦虛寒。陰虛則陽氣無所依附,因此下焦虛寒,反而會見上焦之實熱。少陰之脈循行喉嚨,挾舌本,其分支出而絡於心,注於胸中。凡腎精不足,腎火不藏,必然循經而上走陽分。咽痛、胸滿、心煩者,是因為陰氣併於下而陽氣併於上,水不上承於心,火不下交於腎,這是水火未濟之象。豬屬水畜而津液在於皮膚,用豬皮以治上焦虛浮之火,配合甘味之白蜜和花粉,能瀉心火潤肺而調和脾氣。滋養化源,培養母氣,水升火降,上熱下行,虛陽得以歸位,不需要專門治療下利而下利自止。這三味藥都屬於食物而不藉助於草木之藥,這就是所謂「隨手拈來盡是道」。 |
|
|
1 承不上承於心:根據前後文意,此處當為「水不上承於心」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厥陰方總論 |
||
|
太陰以理中丸為主,厥陰以烏梅丸為主。丸者,緩也。太陰之緩,所㕥和脾胃之氣。厥陰之緩,所㕥制相火之逆也。觀所主諸方,治手足厥冷、脉微欲絕而不用姜、附,下利、脉沉結而用黃柏,心動悸、脉代結而用生地、麥冬。總因肝有相火,當瀉無補,與腎中虛陽之發,當補當溫者不同耳。夫三陰皆有本經之熱:太陰之熱,脾家實而行胃脘之陽也。少陰之熱,腎陰虛而元陽發越也。厥陰之熱,肝胆熱而拂鬱之火內熱也。舉世悞於傳經熱邪之說,遇三陰熱症,漫無主張。見發熱脉沉者,斷為陽症;見陰脉而不治;中風下利者,妄呼為「漏底傷寒」。不明仲景之論,因不敢用仲景之方,非不學無術乎? |
太陰病以理中丸為主,厥陰病以烏梅丸為主。丸劑,有緩和之意。太陰病用緩和之法,是為了調和脾胃之氣。厥陰病用緩和之法,是為了制約相火之上逆。分析一下厥陰病所用各方,治療手足厥冷、脈微欲絕而不用乾薑和附子,治療下利、脈沉結用用黃柏,治療心動悸、脈代結而用生地、麥冬。總是由於肝中有相火,應當用瀉法而不能用補法,與腎中虛陽外越時應當用溫補之法不同。三陰病都有本經之熱:太陰經之熱是脾家實而行胃脘之陽,少陰經之熱是腎陰虛而元陽發越,厥陰經之熱是肝膽熱而有鬱結之火內熱。舉世都受傳經熱邪之說所誤,一旦遇到三陰經熱證時,常常無所適從。見發熱脈沉者就斷為陽證,見陰脈則斷為不治,見中風下利就妄稱之為「漏底傷寒」。由於不明仲景所論,因而不敢用仲景之方,難道不是不學無術嗎?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烏梅丸 烏梅 乾姜 桂枝 附子 蜀椒 黃連 黃柏 人參 當歸 細辛 |
||
|
六經惟厥陰最為難治,其本陰而標熱,其體風木,其用相火。㕥其具合晦朔之理,陰之初盡,即陽之初出,所㕥「一陽為紀,一陰為獨」,則厥陰病熱,是少陽之相火使然也。火旺則水虧,故消渴。氣有餘便是火,故氣上撞心,心中疼熱。木甚則剋土,故飢不欲食,是為「風化」。饑則胃中空虛,蚘聞食臭則出,故吐蚘。此厥陰之火症,非厥陰之傷寒也。《內經》曰:「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,或收或散,或逆或從,隨所利而行之,調其中氣,使之和平。」是厥陰之治法也。仲景之方多㕥辛甘、甘涼為君,獨此方用酸收之品者,以厥陰主肝而屬木。《洪範》云:「木曰曲直,曲直作酸。」《內經》曰:「木生酸,酸入肝。」「以酸瀉之,以酸收之。」君烏梅之大酸,是「伏其所主」也。佐黃連瀉心而除痞,黃柏滋腎㕥除渴,「先其所因」也。腎者,肝之母,椒、附以溫腎,則火有所歸而肝得所養,是固其本也。肝欲散,細辛、乾姜㕥散之。肝藏血,桂枝、當歸引血歸經也。寒熱並用,五味兼收,則氣味不和,故佐以人參調其中氣。㕥苦酒浸烏梅,同氣相求。蒸之米下,資其穀氣。加蜜為丸,少與而漸加之,緩以治其本也。仲景此方,本為厥陰諸症之法,叔和編於「吐蚘」條下,令人不知有厥陰之主方。觀其用藥,與諸症符合,豈只吐蚘一症耶?蚘為生冷之物,與濕熱之氣相成,故寒熱互用㕥治之。且胸中煩而吐蚘,則連、柏是「寒因熱用」。蚘得酸則靜,得辛則伏,得苦則下,殺虫之方,無更出其上者。久利則虛,調其寒熱,扶其正氣,酸㕥收之,其利自止。愚按:厥利發熱諸症,諸條不立方治,當知治法不出此方矣。 |
六經病中只有厥陰病是最難治療的,厥陰之本為陰而其標則為熱,厥陰之體屬風木,其用為相火。因為厥陰之氣具備陰極陽生之理,陰之初盡,即陽之初生,所以有「一陽為紀,一陰為獨」之說,因此厥陰病之發熱,就是少陽之相火所致。火旺則水虧,故消渴。氣有餘便是火,所以氣上撞心,心中疼熱。木甚則克土,所以飢不欲食,這就是「風化」之特點。饑則胃中空虛,蛔蟲聞到食物之氣味就出來,所以會吐蛔蟲。這是厥陰病之火證,並非厥陰之傷寒。《內經》說:「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,或收或散,或逆或從,隨所利而行之,調其中氣,使之和平。」這就是厥陰病之治法。仲景之方大多以辛甘、甘涼為君藥,唯獨此方以酸收之藥為君,因為厥陰主肝而屬木。《洪範》說:「木曰曲直,曲直作酸。」《內經》說:「木生酸,酸入肝。」「以酸瀉之,以酸收之。」以大酸之烏梅為君藥,就是「伏其所主」之意。輔以黃連,瀉心以除痞,佐以黃柏滋腎以除渴,這是「先其所因」之意。腎為肝之母,用蜀椒和附子以溫腎,令陽氣有所歸而肝得滋養,這是固其本。肝欲散,用細辛、乾薑以散之。肝藏血,用桂枝、當歸引血歸經。寒熱並用,五味兼收,則氣味不和,所以輔以人參調其中氣。用苦酒浸泡烏梅,是同氣相求。將烏梅蒸於白米之下,以穀氣為資助。加入蜜而製成丸劑,少量並逐漸增加劑量,是為了用緩和之法以治其本。仲景此方,本來是為了厥陰病各證設立治法,但被王叔和編在「吐蛔」條文之下,而使人不知道厥陰病有主治之方。觀察一下所用之藥,與厥陰病各證都相符,哪裏僅僅是治療吐蛔一證啊?蛔蟲屬於寒冷之物,與濕熱之氣相合而成,因此用寒熱相兼之藥治療。胸中煩而吐蛔,用黃連和黃柏是基於「寒因熱用」。蛔蟲得酸味則安靜,得辛味則伏藏,得苦味則下行,殺蟲之方,沒有比它更好的了。長期下利則致虛損,調和其寒熱,扶持其正氣,再用酸味來收斂,則下利自止。我以為:對於厥逆、下利、發熱等各證,各條文之下不立方治療者,就應該知道其治療方法不外乎此方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當歸四逆湯 桂枝 芍藥 當歸 細辛 通草 甘草 大棗 |
||
|
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姜湯 前方加吳茱萸 生姜 |
||
|
此厥陰傷寒發散表邪之劑也。厥陰居兩陰之交盡,名曰「陰之絕陽」。外傷於寒,則陰陽之氣不相順接,故手足厥冷,脉微欲絕。然相火居於厥陰之藏,藏氣實熱,則寒邪不能侵,只外傷於經,而內不傷藏。故先厥者,後必發熱。凡傷寒初起,內無寒症,而外寒極盛者,但當溫散其表,勿遽溫補其表。此方用桂枝湯㕥觧外,而㕥當歸為君者,因厥陰主肝為血室也。肝苦急,甘㕥緩之,故倍加大棗,猶小建中加飴糖法。肝欲散,當㕥辛散之。細辛,其辛能通三陰之氣血,外達於毫端,比麻黃更猛,可㕥散在表之嚴寒。不用生姜,不取其橫散也。通草即木通,能通九竅而通關節,用㕥開厥陰之闔而行氣於肝。夫陰寒如此,而仍用芍藥者,須防相火之為患也。是方桂枝得歸、芍,生血於營。細辛同通草,行氣於衛。甘草得棗,氣血㕥和。且緩中㕥調肝,則營氣得至手太陰,而脉自不絕。溫表㕥逐邪,則衛氣行四末而手足自溫。不須參、朮之補,不用姜、桂之燥,此厥陰之四逆,與太、少不同治,而仍不失「辛甘發散為陽」之理也。若其人內有久寒者,其相火亦不足。加吳子之辛熱,直達厥陰之藏。生姜之辛散,淫氣於筋。清酒㕥溫經絡,筋脉不沮通弛。則氣血如故,而四肢自溫,脉息自至矣。此又治厥陰內外兩傷於寒之劑也,冷結膀胱而少腹滿痛,手足厥冷者宜之。 |
這是治療傷寒厥陰病發散表邪之方。厥陰居於兩陰交盡之位,被稱為「陰之絕陽」。外傷於寒,則陰陽之氣無法順接,因此手足冷厥,脈微欲絕。然而相火居於厥陰之臟,臟氣有實熱,則寒邪無法侵襲,只能外犯於經絡,而在內不會傷及其臟。所以先厥冷者,後必發熱。凡傷寒病初起,內無寒證,而外寒極盛者,只應當溫散表邪,而不要急於溫補其表。此方用桂枝湯以解表,而之所以用藥當歸為君藥,是因為厥陰主肝,肝為血室。肝氣不欲急,因而用甘味緩之,所以倍用大棗,猶如小建中湯加飴糖之法。肝氣欲散,當用辛味宣散。細辛之辛味能通達三陰之氣血,外能達於毫毛,比麻黃更強烈,可以宣散在表之嚴寒。不用生薑,是為了避免其橫散之特性。通草即木通,能通利九竅和關節,用以開啟厥陰之闔而使氣行於肝。如此之陰寒證,而仍然使用芍藥,是必須要防止相火為患。此方中,桂枝與當歸和芍藥同用,能使營氣化而為血。細辛與通草同用,能使衛氣通行。甘草與大棗同用,則能使氣血調和。而且緩中以調肝氣,則營氣就能到達手太陰肺經,則脈氣自然流暢。通過溫散表邪,則衛氣就能流通四肢末端而手足自然溫和。不需要人參、白朮之補益,不用生薑、桂枝之溫燥,這是針對厥陰病四逆之治療,與治療太陰病、少陰病之法不同,而仍然不失「辛甘發散為陽」之理。如果患者內有久寒,其相火亦不足。加辛熱之吳茱萸,可以直達厥陰之臟。加辛散之生薑,可以使厥陰之氣外達於筋脈。清酒用來溫通經絡,可以使失於流通之筋脈通暢。這樣,氣血恢復正常,而四肢自然溫和,脈氣自然通暢。此方又是治療厥陰病內外兩傷於寒之方,對於寒冷凝結膀胱而出現少腹滿痛,手足冷厥亦能使用。
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小建中湯 桂枝 芍藥 甘草 生姜 大棗 飴糖 |
||
|
厥陰為闔,外傷於寒,肝氣不舒,熱鬱於下,致傷中氣,故製此方以主之。凡六經外感未觧者,皆用桂枝湯觧外。如太陽誤下而陽邪下陷於太陰者,桂枝湯倍加芍藥㕥瀉木邪之干脾也。此肝火上逼於心脾,於桂枝加芍藥湯中更加飴糖,取酸苦以平肝藏之火,辛甘㕥調脾家之急,又資其穀氣以和中也。此方安內攘外,瀉中兼補,故名曰「建」。外症未除,尚資姜、桂㕥散表,不全主中,故稱曰「小」。所謂「中」者有二:一曰心中,一曰腹中。如傷寒二三日,心中悸而煩者,是厥陰之氣逆,上衝於心也,比「心中疼熱」者稍輕,而有虛實之別。疼而熱者為實,當用苦寒㕥瀉心火。悸而煩者為虛,當用甘溫以保心氣,是建腹中之宮城也。傷寒陽脉濇,陰脉弦,腹中急痛者,是厥陰之逆氣上侵脾胃也,比「饑不欲食,食則吐蚘」者為更重,而有形氣之別。食即吐蚘為有形,當用酸苦㕥安蚘。腹中急痛為無形,當用辛寒㕥止痛,是建腹中之都會也。世不明厥陰之為病,便不知仲景所㕥製建中之理。不知胆藏肝內,則不明仲景先裏後表之法。蓋寒雖外來,而熱從中發。必先開厥陰之闔,始得轉少陰1之樞。先平厥陰陰脉之弦,始得通少陽陽脉之濇。此「腹中痛者,先與小建中湯。不差者,繼用小柴胡湯」之理也。凡腹痛而用芍藥者,因相火為患。若因於虛寒者,大非所宜,故有建中、理中之別。或問:腹痛既與小建中溫之,更用小柴胡涼之,先熱後寒,仲景亦姑試之乎?曰:不差者,但未愈,非更甚也。先之㕥建中,是觧肌而發表,止痛在芍藥。繼之㕥柴胡,是補中㕥逐邪,止痛在人參。按:柴胡加減法,腹中痛者,去黃芩加芍藥,其功倍於建中。可知陽脉仍濇,故用人參㕥助桂枝;陰脉仍弦,故用柴胡㕥助芍藥。若一服建中而即差,則不必人參之補,亦不須柴胡之散矣。 |
厥陰為闔,外受寒邪,肝氣不舒,熱鬱於下,引致中氣受傷,因此創製此方主治。凡是六經病外感未解者,都可以用桂枝湯解表。例如太陽病誤下而陽邪陷於太陰者,用桂枝湯倍用芍藥以瀉干犯脾胃之木邪。本證是肝火上逼於心脾,所以在桂枝加芍藥湯中又加入飴糖,取其酸苦以平肝臟之火,取其辛甘以調和脾家之急,並資其穀氣以和中。此方能安內攘外,瀉中兼補,因此稱為「建」。外證未除,仍需用生薑、桂枝以散表邪,不完全主治中焦,所以稱為「小」。所謂「中」,有兩種意思:一是心中,一是腹中。譬如傷寒病二三日,心中悸而煩者,是厥陰之氣逆,上衝於心,比「心中疼熱」稍輕,但有虛實之別。疼痛而熱者為實證,應使用苦寒以瀉心火。悸而煩躁者為虛證,應使用甘溫以保心氣,這是建立腹中之宮城。傷寒病陽脈澀,陰脈弦,腹中急痛者,是厥陰之逆氣上侵脾胃,比「饑不欲食,食則吐蛔」更嚴重,但有形氣之別。食則吐蛔為有形,應使用酸苦以安撫蛔蟲。腹中急痛為無形,應使用辛寒以止痛,這是建立腹中之都會。世人不明白厥陰所發之病,就不知道仲景創製小建中湯之原理。不知道膽臟於肝內,就無法理解仲景先裏後表之治法。因為寒邪雖然是從外來,但熱邪是從內而生。必須先開啟厥陰之闔,然後才能轉動少陽之樞機。先平厥陰病陰脈之弦,然後才能使少陽病陽脈之澀得以暢通。這就是「腹中痛者,先與小建中湯。不差者,繼用小柴胡湯」之理。凡是腹痛而用芍藥者,是因為相火為患。如果腹痛是因於虛寒,就一定不能用芍藥,所以才有建中湯和理中丸之區別。有人問:腹痛既用小建中湯之溫補,為何還要用小柴胡湯之清涼,先熱後寒,仲景亦是姑且試用嗎?答曰:不瘥者,只是病未康復,而非更加嚴重。先用小建中湯,是解肌以發表,止痛在於芍藥。然後用小柴胡湯,是補中以驅邪,止痛在於人參。按:小柴胡湯加減法中,腹中痛者,去黃芩加芍藥,其功效倍於小建中湯。因為陽脈仍然澀,所以用人參來輔助桂枝。因為陰脈仍然弦,所以用小柴胡湯來輔助芍藥。如果服一次小建中湯後立即痊癒,就不需要人參之補益,亦不需要小柴胡湯之散邪了。 |
|
|
1 少陰:據前後文理,當為「少陽」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茯苓甘草湯 桂枝 生姜 茯苓 甘草 |
||
|
此厥陰傷寒發散內邪之汗劑。凡傷寒厥而心下悸者,宜先治水,後治其厥,不爾,水漬入胃,必作利也。此方本欲利水,反取表藥為裏症用,故雖重用姜、桂,而㕥裏藥名方耳。厥陰傷寒,先熱者後必厥,先熱時必消渴。今厥而心下悸,是下利之源,斯時不熱、不渴可知矣。因消渴時飲水多,心下之水氣不能入心為汗,畜而不消,故四肢逆冷而心下悸也。肺為水母,肺氣不化,則水氣不行。茯苓為化氣之品,故能清水之源。然得猪苓、澤瀉,則行西方收除之令,下輸膀胱而為溺。桂枝、生姜,則從辛入肺,使水氣通於肺,以行營衛陰陽,則外走肌表而為汗矣。佐甘草以緩之,汗出周身,而厥自止;水精四布,而悸自安。㕥之治水者,即所以治厥也。凡厥陰之渴在未汗時,太陽之渴在發汗後。如傷寒心悸,汗出而渴者,是水氣不行,而津液又不足,須小發汗㕥散水氣,故用五苓。傷寒心悸,無汗而不渴者,津液未虧,故可用此方大發其汗。五苓因小發汗,故少佐桂枝,不用生姜用白朮者,恐漬水入脾也。此用姜、桂與茯苓等分,而不用芍藥、大棗,是大發其汗。佐甘草者,一㕥協辛發汗,且恐水漬入胃也。厥陰厥而不利,與見厥復利者,因熱少而不能消水,水漬入胃,故仲景言其症而未及治法。與本方汗之則利自止,是「下者舉之」之義也。本方為汗家峻劑,與麻黃湯義異,而奏捷則同。因水氣在心下而不在皮毛,故不用麻黃。悸而不喘,故不用杏仁。且外不熱而內不渴,故不用小青龍。仲景化水發汗之劑,不同如此。 |
這是治療傷寒厥陰病發散內邪發汗之方。凡傷寒病厥而心下悸者,應先治水,然後再治療厥證,否則水邪浸入胃中,必然引起下利。此方本意是利水,反而用發表藥來治療裏證,所以雖然重用生薑和桂枝,而以治裏之藥命名此方。傷寒厥陰病,先發熱者其後必然厥逆,先發熱時必然會消渴。如今厥而心下悸,就是下利之源頭,可知此時尚沒有發熱和口渴。因為消渴時飲水較多,心下之水氣無法入心化為汗液,蓄積不消,所以四肢逆冷而心下悸。肺為水之母,肺氣不能化水,則水氣不能流通。茯苓為化氣之藥,所以能使水之源頭清澈。然而與豬苓和澤瀉同用,則能起到西方肅殺之功,使水氣下輸膀胱而成尿液。桂枝和生薑則因其味辛而入肺,使水氣通於肺而調節營衛之陰陽,則能外走肌膚而化為汗。佐以甘草之緩和,使汗從周身而出,則厥證自然停止;水精四布,而心悸自然平定。用此方治水,即是治療厥證。凡是厥陰病之口渴發生在未發汗之前,而太陽病之口渴則發生在發汗之後。例如傷寒病心悸,汗出而口渴者,說明水氣無法正常運行,而津液又不足,必須輕微發汗以散水氣,因此用五苓散。而傷寒病心悸,無汗而不口渴者,說明津液尚未損耗,因此可以用此方大發汗。五苓散由於輕微發汗,因此少配桂枝,不用生薑而用白朮,是擔心水氣會浸入脾。此方用等份之生薑、桂枝和茯苓,而不用芍藥和大棗,是為了大發汗。輔以甘草,一方面協助辛味藥發汗,另一方面是擔心水氣浸入胃。厥陰病見厥證而不下利,與出現厥證又見下利,是因為陽氣不足以運化水液,水氣浸入胃,所以仲景只言其證而未涉及治法。用本方發汗而下利自止,這是「下者舉之」之意。本方為發汗之峻劑,與麻黃湯作用機制不同,但取效同樣快捷。因為水氣在心下而不在皮毛,所以不用麻黃。因為心下悸而不喘,所以不用杏仁。而且外無發熱而內不口渴,所以不用小青龍湯。仲景化水與發汗之方,有如此之不同。 |
|
|
按:傷寒汗出而渴,是傷寒、溫病分歧處,大宜着眼。要知不惡寒反惡熱者,即是溫病。有水氣而心下悸,尚是傷寒。若無水氣,則五苓燥熱,即溫病發火之藥矣。 |
按:傷寒病汗出而渴,是區分傷寒病和溫病之不同處,對此要特別留意。關鍵要知道不惡寒而反惡熱者,就是溫病。有水氣而心下悸,仍然屬於傷寒病。如果沒有水氣而用五苓散,則其燥熱之性就是助長溫病陽邪化火之藥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炙甘草湯 炙甘草 人參 阿膠 麻仁 桂枝 麥冬 生姜 大棗 清酒 生地1 |
||
|
厥陰傷寒,則相火內鬰。肝氣不舒,血室乾涸,㕥致營氣不調,脉道濇滯而見代結之象。如程郊倩所云:「此結者不能前而代替,非陰盛也。」凡厥陰病,則氣上沖心,故心動悸。此悸動因於脉代結。而手足不厥,非水氣為患矣。不得甘寒多液之品㕥滋陰而和陽,則肝火不息而心血不生。心不安其位,則悸動不止。脉不復其常,則代結何㕥調?故用生地為君,麥冬為臣,炙甘草為佐,大劑㕥峻補真陰,開來學滋陰之一路也。反㕥甘草名方者,藉其載藥入心,補離中之虛㕥安神明耳。然大寒之劑,無㕥奉「發陳」、「蕃秀」之機,必須人參、桂枝,佐麥冬㕥通脉,姜、棗佐甘草㕥和營,膠、麻佐地黃以補血。甘草不使速下,清酒引之上行,且生地、麥冬,得酒力而更優也。 |
傷寒之厥陰病,則相火內鬱。肝氣不舒,血室乾涸,以致營氣不調,脈道澀滯而見脈代結之象。正如程郊倩所說:「這種脈結是指脈氣不能前行而代替,不是陰盛所致。」凡是厥陰病,則氣上衝心,所以心動悸。這種心悸動是由於脈代結所致。而手足並無厥冷,則不是水氣為患。如果不用甘寒多液之藥以滋陰而和陽,則肝火不得平息而心血亦無法生成。心不能安其位,則心悸動不止。脈氣不能恢復正常,則代結之象如何能得調和?因此用生地為君藥,麥冬為臣藥,炙甘草為佐藥,大劑量以峻補真陰,開啟了後學滋陰之流派。反而以甘草來命名此方,是通過甘草載藥入心,滋補離中之虛以安神明。然而,大寒之劑卻沒有陽氣「發陳」、「蕃秀」之機,必須用人參、桂枝輔助麥冬以通脈,生薑、大棗輔佐甘草以和營氣,阿膠、火麻仁輔佐生地黃以補血。甘草不使藥性迅速下行,清酒則引導藥性上行,而且生地和麥冬在清酒作用下效果更加優良。 |
|
|
1《傷寒論》炙甘草湯原本有生地,故補「生地」二字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燒裩散 |
||
|
男女交媾而病傳焉,奇病也。其授者始因傷寒,而實種於慾火;其受者因於慾火,而實發於陰虛,此「陰陽易」之病所由來也。無惡寒發熱之表,無胃實、自利之症。此因兩精相搏而當時即發,與「冬不藏精,春必病溫」者不同。夫「邪之所湊,其氣必虛」,「陰虛者,陽必湊之」,故少氣而熱上冲胸。氣少不得運,故頭重不舉,身體皆重。邪中於陰,故陰中拘攣。冲任脉傷,故少腹裏急。精神散亂,故目中生花。動搖筋骨,故膝脛拘急。病由於腎,毒侵水道,故小便不利。諒非金石所能愈,仍須陰陽感召之理以致之。裩襠者,男女陰陽之衛。衛乎外者,自能清乎內。感於無形者,治之㕥有形。取其隱內,燒而服之,形氣相感,小便即利。陰頭微腫,濁陰走下竅而清陽出上竅,慾火平而諸症自息矣。男服女,女服男,然更宜六味地黃湯合生脉散治之。 |
男女交合而將病邪傳予對方,屬於奇病。傳授者最初病於傷寒,而實際上是由於慾火;感受者是因為慾火,而實際上是源於陰虛,這就是「陰陽易」之病之由來。沒有惡寒發熱之表證,亦沒有胃實、下利之證。這是因為男女之精氣相搏而當時即刻所發之病,與「冬不藏精,春必病溫」是不同的。「邪之所湊,其氣必虛」,「陰虛者,陽必湊之」,所以少氣而熱上衝胸。氣少無力運行,所以頭重不舉,全身沉重。邪氣侵襲於陰部,所以下陰拘攣。衝任脈受傷,所以少腹裏急。精神散亂,所以視物昏花。動搖了筋骨,所以膝蓋與下肢拘急。病源於腎,毒侵水道,所以小便不利。想來並非金石之品所能治,仍然需要依靠陰陽相感之理來治療。內褲是男女保護外陰之物。在外能保護其外陰之物,自然能清除在內之邪。生於無形之病,則以有形之物來治療。取其隱藏於內之物,燒灰後服用,使形氣相互感應,小便即通利。陰頭微腫,則濁陰走下竅而清陽出上竅,慾火平息則諸證自然消退。男病者服女子之內褲,女病者服男子之內褲,但更應該服用六味地黃湯合生脈散來治療。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六經方餘論 |
||
|
既論制方之大法,又分六經之方㕥論之,亦云詳矣。而定方不同之故,更不可不辨也。夫風寒暑濕之傷人,六經各有所受,而發見之脉不同。或脉同而症異,或脉症皆同而主症不同者,此經氣之有別也。蓋六經分界,如九州之風土,人物雖相似,而衣冠、飲食、言語、性情之不同,因風土而各殊。則人身表裏之寒熱虛實,亦皆因經氣而異矣。如太陽一經,寒熱互呈,虛實遞見,治之者,當於表中顧裏,故發表諸方往往兼用裏藥。陽明之經主實熱,治者當於實中防虛,故制攻下諸方,而又叮嚀其不可輕用。少陽之經氣主虛熱,故立方涼觧,每用人參。太陰之經氣主虛寒,故立方溫補,不離姜、附。少陰之經氣多虛寒,故雖見表熱而用附子,亦間有虛熱,故亦有滋陰之劑。厥陰之經氣主實熱,故雖手足厥冷,脉微欲絕,而不用姜、附。然此為無形之實熱,與陽明有形之實熱徑庭矣。仲景製方,因乎經氣,《內經》「審其陰陽,㕥別剛柔。陽病治陰,陰病治陽。定其氣血,各守其鄉」之理也。所㕥表裏攻補陰陽之品,或同或異者,亦因其經氣血之多少而為之定劑耳。請再㕥表裏論之:三陽主表而有裏,三陰主裏而無表,何也?太陽為五藏之主,㕥胸中為裏,猶天子之明堂也;㕥少陰為裏,猶君王之宮禁也。陽明為六府之主,㕥腹中為裏,猶中州之都會,萬物所歸也;㕥太陰為裏,猶政事之府,百職所由分也。少陽為十一藏所決之主,故胸腹皆為其裏而無定位;㕥厥陰為裏,猶運籌於帷幄也。治三陽者,既顧心腹之裏,又顧三陰之裏,所㕥陽經之方倍於陰經。而陽有多少,病有難易,所㕥陽明之方不及太陽,少陽之方更少於陽明也。三陰非無表症也,而謂其無表,猶女子之庭戶即丈夫之堂構,女子出外之引導即丈夫之威儀。故少陰之一身盡熱,無非太陽漸外之陽。太陰之四肢煩疼,原是胃脘之所發。厥陰之厥而發熱,疇非三焦胆甲之氣也。第不頭痛項強,胃家不實,不口苦目眩,定其為陰經耳。三陰之表自三陽來,所㕥三陰表劑,仍用麻黃、桂枝為出路。然女子亦有婢妾,所㕥太陰之芍藥,少陰之附子,厥陰之當歸,得互列於表劑之間,並行而不悖。此《內經》「陰陽表裏雌雄相輸應」之義也。嗟呼!「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生」者,始可與讀仲景之書也夫! |
已經討論了制方大法,又分六經論述了不同之方,可以說是非常詳盡了。然而,製定不同方劑之原因,更是不能不加以辨析。風寒暑濕之傷人,六經各有所受,而所觀察到之脈證不盡相同。有時脈象相同而證候不同,有時脈象和證候都相同,但主證不同,這是由於經氣是有差異的。因為六經所分之界限,猶如九州之風土人情,雖然人物看起來相似,但其衣冠、飲食、言語、性情各不相同,這都因為風土人情各不相同。同樣,人體表裏之寒熱虛實,亦都會因經氣而有所差異。比如太陽經,寒熱互見,虛實交替,治療應該以表為主而兼顧於裏,因此發表各方之中往往兼用治裏之藥。陽明經主實熱,治療時應當在治實證時兼防止其虛,因此制定各攻下之方,而又叮嚀慎重使用。少陽之經氣主虛熱,因此立方時以涼解為主,常常用人參。太陰之經氣主虛寒,因此製方時以溫補為主,離不開乾薑和附子。少陰之經氣多虛寒,所以雖然見有表熱而用附子,間中亦有虛熱,因此亦有滋陰之方。厥陰之經氣主實熱,所以雖然手足厥冷,脈微欲絕,而不用乾薑和附子。然而,這是無形之實熱,與陽明有形之實熱完全不同。仲景製方,基於經氣之不同,這就是《內經》「審其陰陽,以別剛柔。陽病治陰,陰病治陽。定其氣血,各守其鄉」之理。因此,針對表裏攻補陰陽之藥,或者相同或者不同,亦是因為各經氣血之多少而確定用藥。請讓我再從表裏進行分析:三陽主表而有裏,三陰主裏而無表,這是為什麼?太陽為五臟之主,以胸中為裏,就像天子之明堂;以少陰為裏,猶如君王之禁宮。陽明為六腑之主,以腹中為裏,猶如中州之都會,萬物皆歸於此;以太陰為裏,如政務之府,百官由此而各行其職。少陽為十一臟所決之主,因此胸腹皆為其裏而無固定位置;以厥陰為裏,猶如在帷幄中運籌。治療三陽病,既要顧及心腹之裏,又要顧及三陰之裏,所以治陽經之方是治療陰經之方之兩倍。而陽氣有多少,所治之病有難有易,所以陽明經之方不及太陽經,少陽經之方更少於陽明經。三陰病並非沒有表證,而說三陰病無表證,就猶如女子之庭戶即為丈夫之房舍,女子外出之引導即為丈夫之威儀。所以少陰病之一身盡熱,無非就是太陽漸出之陽氣。太陰病之四肢煩疼,原本就是胃脘所發之陽氣。厥陰病之厥而發熱,無非是三焦與膽之氣。只是因為不頭痛項強,胃家不實,不口苦目眩,而將其定為三陰之病。三陰病之表證來自於三陽之氣,所以三陰病治表之劑仍然用麻黃、桂枝使邪氣有出路。然而女子亦有婢妾,所以太陰病之芍藥,少陰病之附子,厥陰病之當歸,都可以在治表之劑中使用,與治表藥並行而悖。這就是《內經》「陰陽表裏雌雄相輸應」之義。唉!「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生」者,才可以與之討論如何讀仲景之書啊!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麻黃升麻湯 麻黃 升麻 黃芩 知母 石膏 芍藥 天冬 乾姜 桂枝 當歸 茯苓 白朮 玉竹 甘草 |
||
|
六經方中,有不出於仲景者,合於仲景,則亦仲景而已矣。若此湯,其大謬者也。傷寒六七日,大下後,寸脉沉而遲。夫寸為陽,主上焦,沉而遲是無陽矣。沉為在裏,則不當發汗。遲為藏寒,則不當清火。且下部脉不至,手足厥冷,泄利不止,是下焦之元陽已脫。又咽喉不利,吐膿血,是上焦之虛陽無依而將亡,故擾亂也。如用參、附㕥回陽而陽不可回,故曰「難治」,則仲景不立方治也,明矣。此用麻黃、升麻、桂枝㕥散之,彙集知母、天冬、黃芩、芍藥、石膏等大寒之品以清之,㕥治陽實之法治亡陽之症,是速其陽之斃也。安可望其汗出而愈哉?用乾姜一味之溫,苓、朮、甘、歸之補,取玉竹㕥代人參,是猶攻金城高壘而用老弱之師也。且用藥至十四味,猶廣羅原野,冀獲一兔,與防風通聖等方,同為庸臣僥倖之符也。謂「東垣用藥多多益善」者,是不論脉病之合否,而殆為妄談歟! |
六經病方中,有些方並非出自仲景,但符合仲景之法,亦可算是仲景之方而已。至於此方,是完全錯誤的。傷寒病六七日,大下後,寸脈沉而遲。寸脈屬陽而主上焦,沉而遲為無陽。脈沉為病在裏,則不應該發汗。脈遲為臟寒,則不應該清火。而且下部脈不至,手足厥冷,泄利不止,說明下焦之元陽已脫。又有咽喉不利而吐膿血,反映上焦之虛陽無所依附而將消亡,所以虛陽擾亂。如果用人參、附子以回陽而陽氣無法回復,所以說「難治」,則仲景就不會立方以治之,這已經很清楚了。此方用麻黃、升麻、桂枝以發散,匯集知母、天冬、黃芩、芍藥、石膏等大寒之品以清熱,用治療陽實之法來治療亡陽之證,這是加速陽氣之消亡。怎麼能期望通過汗出就能痊愈呢?使用一味溫性之乾薑,以及茯苓、白朮、甘草、當歸之補,以玉竹代替人參,就好比用了老弱之兵來攻打金城高牆。而且用藥多達十四味,就好像在原野上廣泛佈防,而希望捕獲一隻兔子,這與防風通聖散等方一樣,都是庸醫僥倖之法。說「東垣用藥多多益善」者,是不會談論所用之方藥是否與所治之病證相合,都是毫無依據之言論罷了! |
|
原文 |
翻譯 |
|
|
牡蠣澤瀉散 牡蠣 澤瀉 蜀漆 海藻 瓜婁根 商陸根 葶藶子 大黃 |
||
|
叔和獨㕥「傷寒」立論,故稱傷寒為「大病」,既云「大病」,則「差後」當用調補法矣,如云「勞復」是因勞而復,當補中益氣,何得用蜀漆㕥吐之有?「宿食」當消食利氣,何㕥加大黃?若「腰已下有水氣」,當溫腎利水,何得用商陸、葶藶等峻利之劑?豈仲景法乎?且此等症候,仲景方中自有治法。如「勞復」可用桂枝人參、新加湯,「宿食」可用梔子厚朴湯,「腰以下水氣」可用猪苓、五苓,與桂枝去桂加苓朮等湯,「虛嬴少氣」,用桂枝人參湯治陽虛,炙甘草湯治陰虛。由此觀之,仲景未嘗無法,末常缺方,何須補續耶?後人不分此等方法是叔和插入,故曰「仲景只知治外感,不知治內傷」。又曰:「但取仲景法,不取仲景方」。夫仲景之方不足取,則仲景之法亦非法矣。仲景每用參苓白朮甘草㕥治外感,而反謂其不能治內傷,豈非㕥其治?「勞復」、「食復」反用吐下法?仲景道知後世必有無知妄作,亂其篇章,壞其成法者,亦必有好學深思,心知其意為之發明者,故其《自序》曰:「若能尋余所集,思過半矣。」叔和不能集仲景之法,於所集中而反搜採於所集之外,故「各承家技」者,仍得混雜於其間。嗟呼!仲景因粗工之妄治而設此種活方,層層活法,游刃有餘。仲景之方逍遙自得,只於所集中取之無盡,用之不竭。若更外取他方,此仲景所云「崇餙其末忽其本」也。因叔和創夾雜之源,後人競立,論㕥為貴,至陶尚文則濫極矣。孟子曰:「能言拒楊墨者,聖人之徒也。」楊墨之道,不熄孔子之道,不著諸家異端之邪說。不明岐伯,仲景之聖教不行,故余不得不辨。 |
王叔和以「傷寒」立論,因此稱傷寒病為「大病」。既然稱之為「大病」,則「差後」病應該用調補之法,譬如「勞復」病是因勞累而復發,應當補中益氣,為什麼會用蜀漆以吐之呢?「宿食」病應該消食利氣,為甚麼會加大黃呢?如果「腰以下有水氣」,應該溫腎而利水,為什麼要用商陸、葶藶子等峻下之藥呢?這難道是仲景之法嗎?而且對於這些證候,仲景之方已經有相應之治法。例如,對於「勞復」病可以用桂枝人參湯、桂枝新加湯,對於「宿食」病可以用梔子厚朴湯,對於「腰以下水氣」可以用豬苓湯、五苓散,或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等方,對於「虛羸少氣」可以用桂枝人參湯治陽虛,炙甘草湯治陰虛。由此可見,仲景並不缺乏治法,亦未曾缺少方藥,有什麼需要補充呢?後人不能分辨此等方法都是叔和後來添加的,所以說「仲景只知道治療外感病,不知道治療內傷病」。又說:「只取仲景之治法,不取仲景之方。」如果仲景之方不足以取,則仲景之法亦就不是法了。仲景每每用人參、茯苓、白朮、甘草治療外感病,而有人卻說這些藥不能治療內傷病,這難道不可以用嗎?而對於「勞復」病、「食復」病反而可以用涌吐、攻下之法?仲景知道後世必定有些無知之人對其篇章妄加改動,亦知後世必定有好學深思之人,能得其之心法而為之發揚光大,所以在《自序》中說:「若能尋余所集,思過半矣。」王叔和無法收集仲景之法,反而在其收集之中混雜了外來之法,所以那些「各承家技」者仍然得以混雜其中。唉!仲景因為那些粗工之誤治而設立這些活方,一層一層之活法,用起來游刃有餘。仲景之方逍遙自得,只在應該收集到的內容中就已經取之不盡,用之不竭。如果在此之外再去尋求其他方劑,這正如仲景所說「崇飾其末忽其本」。因為叔和開創了夾雜其它內容之做法,後人爭相立論,並以此為貴,至於陶節庵就已氾濫至極了。孟子說:「能夠在言論上反駁楊朱、墨翟之人,就是聖人之門徒。」楊朱與墨翟之學說尚未熄滅孔子之道,不將異端邪說放入其中。如果不明岐伯之言,則仲景之聖教亦不能推行開來,因此我不得不對此加以辨論。 |
|
|
《傷寒附翼》卷之下終 |
《傷寒附翼》卷下結束 |



